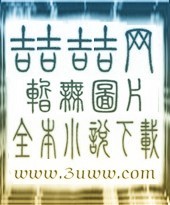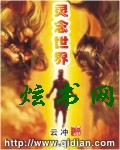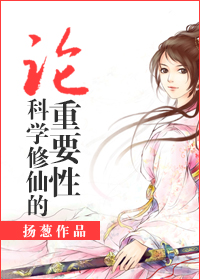世界是平的-第1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为什么这么说呢?资本、技术和信息的民主化不仅将所有保护其他体系的墙摧毁得一干二净,这三个民主化也是世界上新型力量的源泉,我将其称之为“电子族”。
全球化体系核心:“电子族”与
“金色紧身衣”之间的相互影响力
“电子族”是由那些遍及全球、坐在计算机屏幕前炒股票、证券和现汇者们组成的。他们中也有通过鼠标器咔嚓咔嚓地将互助基金、养老基金及正在形成的市场基金在世界范围内调来调去的人,还包括那些坐在家中通过因特网开展电子商务的人,当然也包括大的跨国公司的合伙者,这些人的工厂现在遍及全世界,经常用最快的效率最低的成本更换他们的产品。“电子族”成员日益庞大要归功于技术、资本和信息的民主化——今天,它们已经开始代替政府机能成为资本的主要源泉,对公司和国家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在当今全球化体系时期,一个国家如果想繁荣兴旺,不仅必须穿上“金色紧身衣”,而且还必须与“电子族”沟通关系。“电子族”对“金色紧身衣”情有独钟,因为“金色紧身衣”包含了“电子族”希望一个国家应有的各种自由及自由市场的规则,它对那些穿上了“金色紧身衣”并一直保持着的国家的回报,是外资投资不断增长,对那些没有穿上“金色紧身衣”国家的惩罚就是——“电子族”不是有意绕开这些国家,就是从这些国家将资金抽走。
对“电子族”来说,穆迪氏投资服务公司、拉佛菲尔浦斯(Duff&Phelps)信用等级公司、标准普尔(Standard&Poor)都是侦探,这些信誉评估机构在世界各地四处寻觅,经常去各国嗅嗅闻闻,一旦它们发现某国将“金色紧身衣”搁置一边,就大声发出警报(虽然穆迪氏投资服务公司有时也有走麦城或被兴奋剂所迷惑,如在东南亚的所作所为那样,直到出事后才发出警报)。
“电子族”民族与国家及“金色紧身衣”之间的相互影响力是当今全球化体系的核心。我首次认识到这点是1995年2月,克林顿总统发表就职演说前夕对加拿大的访问。当时,我负责对白宫的采访,在为采访总统的加拿大之行作准备时,我一直盯着《金融时报》及其他一些报刊上的文章,看看加拿大方面事前对来自“希望之人”的首次访问说些什么。我非常有趣地发现,他们根本没有涉及总统之行。相反,他们却大谈特谈由穆迪斯投资服务公司所进行的调查。当时的加拿大议会正就国家的债务进行辩论。穆迪氏投资服务公司的一个工作组正好到渥太华,对加拿大财政部长和议员们提出警告。穆迪氏投资服务公司小组告诫他们说,如果他们不将预算赤字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降低到国际正常水平和期望的那种程度,穆迪氏投资服务公司将把加拿大的金融信用率从3…A降级,果真如此,加拿大和每个加拿大公司向国外借款时就不得支付高额利率。为强调此点,加拿大财政部发表声明称:“与我们的经济总产值相比,加拿大的外债总额十分巨大,这意味着加拿大过分脆弱,有可能成为全球金融市场危机的引爆点。我们的经济主权正蒙受着实质性损失。”针对那些对此点理解不深的加拿大人,财政部长保罗·马丁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我们在用我们的眼珠子作抵押。”不,加拿大人对“希望之人”丝毫不感兴趣,“穆迪氏投资服务公司的人”和“电子族”才是他们所关注的重点。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六章“金色紧身衣”(5)
这些“电子族”来自何方?他们如何能产生出这样一种令人生畏的力量,以至于像个“超级大国”一样可恐吓另外一个国家,或能让某个单一民族的国家富裕起来?
第一章 新体系(1)
福里斯特·冈普的妈妈想谈些什么来着?生命就如同一盒巧克力,你绝对不明白里面装的是什么。对我来说,一个酷爱旅游的外国记者,生活就如同旅馆房间服务——你绝对不会了解门外边发生的事。
“这活儿只有日本人才能做得出来”
以1994年12月31日晚上的事为例,那天《纽约时报》委任我为外事专栏的作家,我的专栏发稿是从东京开始的。当我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越洋飞行到达大仑饭店后,就叫了一次房间服务,提出一个简单的要求:“请尽快给我送4个橘子来。”我喜欢橘子,需要摆在那里慢慢吃。打电话时,我认为这是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要求了,接电话的人也似乎明白了我的意思。大约20分钟后,有人敲门,一位穿着笔挺服装的房间服务员站在门口,他前面的手推车上盖着一块上过浆的白色餐布,下面是4个盛着刚榨出来的鲜橘汁的玻璃杯,每个玻璃杯下面是装满冰的银碗。
“不是,不是。”我对服务员说,“我要橘子,橘子——不是橘汁。”然后我装着咬一口橘子的模样给他看。
“是的,是的。”服务员边说边点头,“橘子,橘子。”
我返回房间继续工作。20分钟后,再次传来敲门声,还是那位服务员,还是那辆用亚麻布盖着的用于房间服务的手推车,所不同的是车上有4个碟子,每个碟子里盛着剥了皮的橘子,橘子瓣摆成小方块,宛如一盘寿司,这活儿只有日本人才能做得出来。
“不是,不是。”我再次摇着头说,“我要的是整个整个的橘子,”我用手比划成圆圈形,“我要橘子放在我的房间慢慢吃,我不能一次将4个掰成瓣的橘子一下吃掉,掰了的橘子也不能放在冰箱里,我要的是整个的橘子。”
我再次用夸张的手法模仿吃橘子的样子。
“是的,是的,”服务员一边说一边点头,“橘子,橘子,你要完整的橘子。”
20分钟过去了,敲门声再次响起,同一位服务员,同一个手推车,他带来了4个完整的橘子,分别摆在4个小碟子上,一把叉子,一把餐刀,叠好的餐布整齐地放在一边。
“对啦!”我签了字。“那才是我所需要的。”
当他离开房间后,我看了看账单,4个橘子是22美元。我如何才能向我的老板报账呢?
但我的橘子经历并非到此结束。两个星期后我到了河内,独自在市中心旅馆用了晚餐。当时正是越南橘子丰收的时节。小贩们在街头巷尾成堆地叫卖刚摘下来的新鲜的、招人喜欢的橘子。每顿早餐我都要吃几个。当服务员过来问我要什么甜点时,我只说要一个橘子。
他出去了,数分钟后返回。
“对不起,”他说,“我们没有橘子。”
“那怎么可能呢?”我有些发怒地问道,“每天早餐时你们都会摆一大桌子,现在你却说厨房后面某个地方没有一个橘子?”
“对不起,”他摇着头说,“你说的或许是西瓜吧。”
“行呀,”我说,“就给我上西瓜吧。”
5分钟后服务员带着一个掰成三瓣的橘子回来了。
“我发现橘子了,没有西瓜。”
现在我明白了,作为一位预言家,我应该把当时看到的一切都记录下来,因为我从盘子和房间外边的事里发现的问题太多了,虽然那并不是我作为《纽约时报》记者按编辑部要求在全球飞来飞去时的发现。
从“在欧洲”专栏到“国际”专栏
作为一名《纽约时报》国际事务专栏作家,如果有人想找份最好的工作,我觉得这就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作,不知是否正确?如果对,那么我已经得到这份工作了。其理由是,拥有这样崇高工作的人,可以带着自己的观点去环游世界。我可以在任何时候到任何地方去,就我的所见所闻发表看法。但问题是,当我着手动笔写作本书时,我面临的问题是:什么观点?透视什么?展望什么?组织系统——超级故事——通过我对世界的观察,如何帮助读者弄懂这些现象,优先考虑它们,评论它们、了解它们?
第一章 新体系(2)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的前任干此事比较容易些,他们处处可以遇到一个现成的超级故事和国际体系。我是《纽约时报》历史上第五任国际事务专栏作家,“国际”实际上是该报最早的专栏,1937年由安妮·奥黑尔·麦考密克女士创办,最初称之为“在欧洲”;因为在那些日子里,对多数美国人来说,“在欧洲”就是国际事务,《纽约时报》的第一个海外专栏定格在欧洲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纽约时报》1954年为麦考密克女士发布的讣告说,她开始发表国际专稿时“是以代顿的工程师麦考密克先生妻子的身份,当时她为了伴随丈夫经常买票去欧洲。”(从那时开始,《纽约时报》上的讣告被认为更政治化了。)她报道的国际体系是欧洲凡尔赛列强平衡的崩溃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
正如美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堀起、成为跨越世界的超级大国、在全球范围内担当起与苏联进行斗争的重任一样,《纽约时报》的“在欧洲”专栏也从1954年起改成“国际”专栏。几乎一夜之间,整个世界成了美国任意驰骋的战场,所有的世界事务,哪怕是天涯海角,都成了与苏联争夺的对象。在西方资本主义与东方共产主义之间,在华盛顿与莫斯科和北京之间对于影响霸权之间的竞争,成了三位国际专栏作家组织他们超级故事的主要观点。
从“冷战后世界”到“全球化”
到1995年春,我着手国际专栏写作时,冷战已经结束,柏林墙也倒塌,苏联成了历史。我曾有幸在莫斯科目睹过这一切。1991年12月16日这天,国务卿詹姆斯·贝克正在莫斯科访问,鲍里斯·叶利钦正在蚕食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权力。当天贝克按预订日程与戈尔巴乔夫见面,他们的会谈是在克里姆林宫金壁辉煌的圣·凯瑟琳厅举行的。开始之前,通常会很和谐地安排一次新闻发布会。贝克先生和他的随从在长长的克里姆林宫尽头的两扇大木门后等待,戈尔巴乔夫与他的随员在另一头的大门后面,双方只等统一信号出现,大门同时打开,两人同时迈进房间,来到大厅正中央,在闪光灯下握手。为了会谈,贝克按时来到指定地点,门慢慢打开,走出来的却是鲍里斯·叶利钦,而非戈尔巴乔夫,猜猜谁将来吃晚餐!“欢迎来到俄罗斯大地,这些都是俄式建筑,”叶利钦对贝克如是说。贝克当天晚些时候会见了戈尔巴乔夫,很明显,权力已经发生转换。我们负责报道此事的国务院记者在克里姆林宫呆了整整一天,大家静候在那儿,外边大雪纷纷,太阳下山时我终于走了出来,克里姆林宫银装素裹,我们迈着沉重的步伐走过克里姆林宫斯巴斯克大门,靴子在刚下的雪地里踏出条条新痕,我注意到克里姆林宫顶端旗杆上锤子与镰刀的红旗仍高高飘扬,像聚光灯一样在那儿飘了70年。我自言自语:“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看见它在那儿飘扬了。”不幸被我言中,数星期后,随着冷战体系及这个超级故事的结束,它也消失了。
但是数年后当我从事专栏写作时,我仍然弄不明白,冷战体系作为国际关系中占支配地位的组织框架消失后,用什么来填补其真空呢?我开始专栏写作时没有任何偏见——脑子一片空白。数年后,像所有其他人一样,我将自己归入了“冷战后世界”。我们知道,某种新的包含不同类型的国际关系的框架正在形成之中,它是什么我们还不能下定义,所以我们就不予评论。它不是冷战,因此我们且将其称之为冷战后世界。
我在国外旅行得越多,就越明显感到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不是仅有些污秽、前后矛盾、模模糊糊、处于后冷战时代的世界,相反,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新的世界体系里,这个体系有它自己独特的逻辑、规则、压力和动机,应该有它自己的名称:“全球化”。全球化不只是经济上的一种时尚,也不是一种流行趋势,它是一种国际体系——是随着柏林墙倒塌后取代冷战体系的国际化体系。我们需要尽可能多地了解它。如果它对犯罪行为能起到一种限制作用,也一定能限制外交界里的老生常谈。鉴于此,“冷战后世界”就应该宣布结束,我们现在处在一个新的全球化国际体系里。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一章 新体系(3)
比较:“冷战体系”和“全球化体系”
当我讲到“冷战体系”和“全球化体系”时,我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的意思是,作为一个国际体系,冷战有它自己的权力结构:美国与前苏联之间的平衡。冷战有它自己的规则:在外交事务上,没有一个超级大国可以侵犯另一个的势力范围;在经济上,少数发达国家集中培育各自的民族工业,发展中国家主要依靠出口促进增长,共产主义国家发展的是自给自足的经济,西方国家的经济是管制下的贸易。冷战有它自己的理论: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冲突以及缓和、不结盟和新思维。冷战有它自己的人口流动趋势:从东方到西方的人口流动因铁幕而完全中止,但从南向北的流动却稳固地增加。冷战对国际事务有自己的观点:世界被划分为共产主义集团、西方集团、中立集团,每个国家都属于某集团中的一员。冷战有自己明确的技术定义:占主导地位的是核武器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但对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人来说,刀耕火种仍然是主要的生产方式。冷战有它自己明确的计算方法:核武器的投掷量。最后,冷战也让人明显地担忧:核毁灭。如果将所有这些因素通盘考虑,冷战实际上对世界的每个国家的国内政治和国外政策都产生了影响。冷战体系不会影响世界上每件事,但的确影响了许多事。
今天的全球化体系类似一个国际化体系,与此相比,冷战体系具有独特及最明显的特征——分裂。世界四分五裂,各阵营的成员都是临时挑选的,你所面临的威胁或挑战都取决于你被分割在什么阵营。简而言之,冷战体系用一个词就可体现——柏林墙。对那个世界描述的最恰当的是杰克·尼科尔森在电影《几个好人》中扮演的角色,尼科尔森在里面担任美国驻古巴关塔那摩军事基地的海军陆战队上校。影片中有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