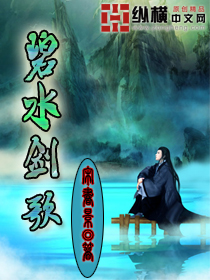碧海剑歌-第2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叶听涛道:“或许都是天意……锡去没相信过这些。”他望着马车中棺木隐约的影子,眉间突然掠过一阵挡也挡不住的苦涩。马车启动,载着白茉的灵柩慢慢地驶过陆吾镇的青石板街道,缓缓地移动着。
“好在他终于也得到了结果,好过老死于这里无人送葬。”楚玉声转过头去,凝望着叶听涛,“你想要的结果是什么?”
叶听涛不答,他的手依然与手中的剑紧紧相握在一起,剑鞘却总是冰凉如雪。他深深地叹息了一声,不再去掩藏其中的过往。楚玉声的眼神中有了些诧异。
“接下去,你打算怎么办?”她问。
“我想,是鸽开这里了吧。”叶听涛目送着马车消失在长街尽处,喟然道。
(第一卷完)
第一卷·飞泉夜雨潇湘吟 潇湘卷外传 渡边雪
那年冬天,一个子披着貂皮斗蓬,冒着鹅毛大雪来到流云渡。斗蓬太大,遮着她半张脸和全身,只看见一缕乱发从额头垂落下来。这年的行客多半都是这副狼狈相,只因为雪下个不停,已有一些人困守在渡口,巴柏等船来接应。
门帘掀起扑进来一阵雪,阿吉打了个喷嚏,愤愤地爬起来,招呼那子登名住店。“一间房。”她只说了一句,也没有脱下斗蓬,露出的半张脸皮肤惨白惨白的。阿吉没敢多说,把她领了进去。
我回过头,继续磕我的瓜子。在流云客栈呆了几年,也习惯了各种各样的奇人异士,来人都是客,安守本份就好。大雪已下了十几天,派出去购买各种物事的伙计尚未回来,所幸客人也不甚多,还可支持得下去。
店田的炉火噼噼啪啪的,门帘外风雪有声。角落里有个样子潦倒的书生,抱了一壶酒吟吟哦哦。天字地字号房里各有几个带刀佩剑的人,但都吩咐将饭食送进房里,风雪阻塞了道路,也让那些可能发生的争斗偃旗息鼓。这最好。
下午是客栈里最清闲的时候,我常常在心里反复地计算着枕头下积攒着的银子已有多少,与我的计划还差多少。去年年终掌柜的多分了些利钱,使我在流云客栈要呆的日子又缩短了两个月。我每天努力地干活,即使是在生意清淡的冬天,也不早早缩回房去。
阿吉与我相处了三年。他是某一个暴雨之被掌柜的从渡口捡回来的,醒了以后也成了客栈的杂役。他从阑说他家里的事,也好像没有什么奔头,仿佛只是为了报答掌柜的而干活,但同样也很卖力。
那个子要了人字一号房,阿吉回来说。脸颇有些兴奋,仿佛又看见了什么值得饭后唠嗑的事。他朝我凑过来:“阿通,咱们在客栈干活,见过的姑娘也有一大打了,可像这姑娘这么漂亮的,保管你没见过。”
我笑了笑:“是吗?也不就是两眼一鼻子?标致些的百个里头总得有一个吧。”
阿吉不依不饶:“可这姑娘是真漂亮,那斗蓬一脱,就跟水仙儿似的,斗蓬里还夹了把琴。”
“呦,也是个走江湖卖艺的?我说住人字房呢,都是可怜人。”我用手拢了拢瓜子壳。
“要说是卖艺的也有蹊跷,她那把琴哪,一看就是有了年头的了,上头还镶着些乌七八糟的符文,说不准是哪朝遗物呢。”
“也许吧。”我有些心不在焉。阿吉见我不接话,也就悻悻地住了嘴,抄了一把瓜子,坐在我旁边磕起来。
“我说阿通,你怎么对人比对条狗还不感兴趣哪?我看你也老大不小了,媳不娶,姑娘不爱,打算当和尚哪?”
“嘿!”我微微冷笑了一声,本想回敬他一句无家无根,但话到嘴边又作罢:“你就急急自己吧,咱哥儿俩还不是一样。”
阿吉嘿嘿笑了笑,一片瓜子壳从嘴唇里蹦出来。角落里的书生拍拍桌子,示意再上一壶酒。阿吉瞧着他没动窝,我站起来又给他拿了一壶。走到柜前的时候,我不由得瞥了一眼住客名牌上的人字一号房,匆匆看得了“玄音”二字。也像是个艺的名字。
书生喝得大醉,接过了酒,又问我要笔墨,看来想将客栈的墙壁糟蹋一番。我含含糊糊地应了几声,推作去取,转身往里堂走去。索抱些柴伙来,炉田的火也快灭了。路过杂役房,我习惯地看了看枕头,一切如旧。我的积蓄还好好地在那里。十两三钱,够买些家什,但还不很多。
降雪的天气木柴容易潮湿,昨该是阿吉劈柴,他常忘了给柴堆罩上层油布。我怀着这样一点担心来到后院,一片厚厚的积雪一时有些耀目,无法看清里面的物事。我走进雪里,雪马上就没到脚踝,湿冷包裹着鞋袜,脚趾隐隐发疼。后院里静悄悄的,猪圈里的猪已经移到了杂物房里,只有几匹客人的马低着头互相挨挨擦擦。我想起竹林山。
那个小地方往常四季如,是没有雪的。那一年下了,虽不很大,但足以在所有瓦屋的顶上薄薄覆上一层银白。阿娘阑及给我们缝靴子,大家穿着布鞋,如临大敌,里面包上两三双袜子,在路上走多了脚还是冻得失去知觉。只有青娘很高兴,总在飘雪的时候拉着我往外跑。我怕她着凉,又怕阿娘责怪,所以一被她拉出门就开始想用什么借口把她骗回去。好在青娘很听话,从不任。
流云渡的雪是不像竹林山那样轻柔的,一下就是天地俱白,不穿靴子绝不可以出门。我的脚在雪地里踩出一个个深深的坑,又有雪迅速地填进去。这个时候,我听见“吱呀”一声,一扇客房朝着后院的窗被推开了。一张脸在后面露出来。
玄音。我不知怎的立刻确定那是玄音,阿吉口中得见所未见的子。也许是因为她的不再被斗蓬遮住的脸白如水仙,也许是因为她的一缕头发依然垂在额角,也许只是因为她很。清洁的五,双眼如知秋的一片落叶,凝视了一眼天空中飘舞的雪。我一时怔愣,傻在当地。
她并没有看见我,视线被雪牢牢牵住,有风拂动她淡绿的裙衫和黑发。我有些隐秘的庆幸,她用一根棍子支起窗户,正好挡住了我。可是她还是看见了我的脚印,一个个无可挽回地留在那里。等我惊觉这一点,她已经转身回走,任凭小小的雪片翻跃窗棂,浸润房内的空气。
店田因为炉火旺盛而温暖干燥,阿吉和我把烂醉的书生架回人字二号房。经过玄音房间的时候,我和阿吉都不由自主放轻了脚步,怕惊扰到她。阿吉嘲弄地向我撇撇嘴,我不予理睬。书生已欠下一两银子的酒钱,我和阿吉扫视他的房间,发现他只剩下些书可以拇抵充了。每年总会有一些这样的人,仕途受阻、抱负落空、为人陷害、情场失意,他们有各式各样的理由来到这个不大不小的渡口寻醉一场。好些的清醒后自行离去,不然便只能扫地出门。
掌柜的偶尔给他们几钱碎银子,多半不给。开始我还为这些人担心,后来慢慢也就不放在心上了。大家不过各司其职,扮演着上天要我们扮演的一些角。演得好演得不好,如何开始如何收场,冥冥之中都自有定数。
书生扑在上,嘴里喃喃地说些什么,不一会儿酣睡去了。
这天客栈即将关门的时候,出去买物事的伙计终于归来,带回了些米粮鸡鸭,赶车的手上都冻起了疮子。我们很高兴,决定给所有的客人加菜一道。闻说掌柜的回乡看望老母亲,尚困在苏州无法回来,阿吉地笑。
冰封雪结的流云渡来往的人很少,如此守着静静的客栈,难免让人思忆起家乡的亲人,没过两天,小厮阿财趁着元宵节近,掌柜的又不在,与我央求了一阵,回家探亲去了。客栈里只剩下我、阿吉、一个小厮、一个厨子,以及房中的几个客人。除了我之外,其他人多是无亲可探,每逢佳节,也只有彼此聚在一起算是个伴。
玄音姑娘也依然悄无声息地呆在这里。她每天让人送饭到房里,从不在店堂中露面。那些带刀剑的江湖中人曾瞥眼之间注意过她,但目光都只停留在她的房门外。她整天在房里,无人说话,也不弹琴。有几次我到后院劈柴,见她的窗子关着,纷扬的雪无声地贴在窗纸上。我不由得有些怅惘。阿吉曾向她献殷勤,煮了汤圆端去放在她的房门外,一个晚上动也没动一下。阿吉于是放弃对她的留意,仍旧开始全心照顾大田的生意。阿吉便是这般无甚耐心的人,自认识以来,似乎只有留在流云客栈这件事,在他来说还算长久。我也有些炕透他。直到元宵节过后的第二天,这一切似乎有了些微的改变。
来人是一个佩带长剑的男子,一身湖蓝绸衫,衣摆在风雪里猎猎翻卷。我正站在门口望着满天大雪暗暗叹气,这个男子穿越风雪朝我走了过来。
“客住店?”我看见他的长剑,心中突地跳了一下。剑鞘上红宝石的光芒在雪白之中格外扎眼。
“嗯。”男子看了看我,我赶紧替他掀开门帘,他一弯腰,走了进去。
这类人在流云渡也并不是少见的,以我的经验,要看这些人中的一个在他们一群人中地位如何,大抵要看他的佩剑。名剑配英雄,从他们的谈话里,我时常听到一把剑因主人的传奇而成名,又使一个手持它的人因之具有尊贵身份的事情。甚至于有一段时间,我和阿吉商量着要动用各自的积蓄去铸造一把剑。但是没过多久我就首先放弃了。我不是那些上天入地的剑客,我得干活赚钱。赚钱是不需要剑的。
阿吉见到这个男子的剑也不小地吃了一惊,急忙开始奉承拍马:“客您一路辛苦了,打尖还是住店呀?”
“住店。”男子的声音淡淡的。
“有来,咱这儿天字一号上房还空着,正好给您大人住了,客您来得也巧了,您打哪儿来呀?”阿吉跑前跑后,十分热络。我无意与他争抢,只上前问道:“客尊姓大名?”
“叶听涛。”男子回答,随着阿吉向内堂走,我也跟随其后,准备去登记名牌上写上他的名字。心想这回又是我赌赢了,我赌天字一号会住个三个字名字的人。阿吉仍旧喋喋不休,并开始问到叶听涛的剑上:“客您的剑一看就不是凡物啊,也只有您这样的人物才配使它。”
我不皱了皱眉,果然,在阿吉抚摸叶听涛那把佩剑的时候,叶听涛右手一振,阿吉仿佛被一股气浪推翻在地:“哎呦!”阿吉痛叫。叶听涛冷冷看了他一眼,自往天字房去了。我扶起阿吉,数落道:“你也就是手痒痒,什没好碰非碰那玩意儿,武林中人都拿它当命似的。”
阿吉摸摸脑袋,看看叶听涛已走远,狠狠地“呸!”了一声。
叶听涛走进内廊之前,我注意到他扫了一眼登记名牌,在“玄音”二字上停留了一下。我心中一凛。风声时而拍打窗户和门帘,像鬼在桥。以前青娘听到这种声音总是很害怕,深更半也会来桥,要和我睡在一起。我不得不许多时间把她哄回去,哄到她睡着。青娘的脸孔在我胸中荡漾开来。
就在这个时候,走廊里传来一声的唤声:“小二。”
我吓了一跳,一时不能认出这是谁的声音,但旋即明白是玄音。我和阿吉都愣了一下,我起身:“哎!姑娘有何吩咐?”
玄音没有回答,我听见轻轻的脚步声,她回了房。“叫你过去呢!”阿吉贼忒兮兮地拱了我一下,我不由得着慌,不及细想,赶紧朝内廊走去。
“进门。”玄音坐在房里,用一块白绣帕轻轻擦拭琴弦,动作缓缓的。
我蹑足进门,站在门槛前面,往前走了两步,便不敢再走了。玄音一挥左袖,我感到一阵风拂过面颊,身后的门关上了。我心里呯呯直跳。
“方才来的是何人?”玄音问道。她的声音就像屋外的冰雪,我的脖子里凉凉的。
“一位客……叫叶听涛。”我答。
玄音的眼神轻微地一动,低头瞧着琴弦:“作何打扮?”
“蓝衫子,跟过路侠客差不多的模样,佩剑上还镶着宝石,想来挺名贵的。”我快速地说,毕恭毕敬。
“嗯……”玄音沉吟,没再说话,眉头微微蹙着。她仿佛是忘记了我还站在这儿。我有些不知所措,又担心她是否还记得那天窗后之事,窗外风雪依然,我胡思乱想一阵,忽然冲口而出:“姑娘房中可需要火炉?”
玄音一怔:“不必。”
“暖暖手也好啊,姑娘的一双手是弹琴的,不像我们这些粗坯子,冻烂了也不打紧。”
“……”
“……呃,姑娘别见怪,我们这些粗人不会说话,您……”
“……好吧。”
“哎!”我很高兴,急忙跑回大堂,在柜下掏出一个黄铜暖手炉。那是掌柜的交代给贵客用的,轻易不拿出来。我用袖子把它擦擦干净,揣在怀里。阿吉坐在堂角的一条长椅上斜眼望着我,笑了笑。
傍晚的时候,雪势小了一些,有两三个客人出门查看,问了问我们附近的道路,便决定趁天没黑赶去附近的村落,看看有无商队的马车可搭。那几个客人结帐的时候,我和阿吉都得了些碎银子,阿吉顺手收进腰带里,我则趁牵马的当儿把它藏到枕头下的小布袋中,又把里面的银子都倒出来,摊在铺上数了一遍。十两六钱银子。
客人们消失在积雪覆盖的小路尽头。我回店堂去勾名牌上他们的名字,发现整家客栈只剩下了我、阿吉、一个厨子、潦倒书生,还有叶听涛和玄音。那个书生最近已喝不起酒,整天闷在房里。叶听涛常常来店堂吃饭,但并不怎么理会我和阿吉,吃完了以后,就在那里坐着。阿吉和我因而不能放肆地说话,只能干磕瓜子,彼此看着。叶听涛在等着什么人出来与他相会,我渐渐看了出来。
我和阿吉私下议论,都说叶听涛和玄音是相识的,但他们又不见面,仿佛在隔着几间屋子对峙,彼此之间只有屋外风雪呼啸的声音。我心里暗暗纳闷,又不敢去探听些什么。不惹武林人士,是掌柜的定下的规矩。有一天晚上,在我和阿吉熄了烛火上,我还未入睡的时候,寂寂的里传来“铮”的一声琴声。传遍了整家客栈,然而又很轻,我犹豫了一下,打算将之当作幻觉。
又是“铮”的一响,声音如一声试探和叩门,一条丝线穿越而来,在耳畔鸣动。我轻轻坐起身,一下子睡意全无。
黑暗中我望着人字一号房的方向,虽然什么都炕见,但我还是立刻想象出玄音坐在桌前,轻轻拨动琴弦的样子。她在弹琴,她终于开始弹琴了,可是难道她在深更半卖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