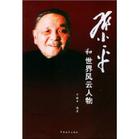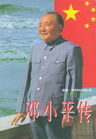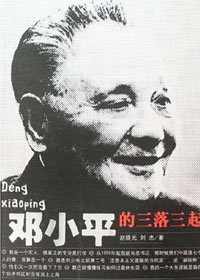邓小平的三落三起-第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8月28日上午,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美驻华大使赫尔利,蒋介石代表张治中陪同下,也乘坐一架美国飞机离开延安,但目的地是当时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所在地重庆。中共最高领导人此行是应蒋介石邀请,准备与国民党最高领导人,在和平、民主、团结基础上,合理解决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商讨团结救国大计”。
也就是在这一天,刘、邓在涉县赤岸村司令部旧址内会议室里,讨论发起上党战役的准备情况。他们对离开延安前毛泽东的那番寓意深刻的话记忆犹新:“你们回到前方,放手打就是了,不要担心我在重庆的安全问题。你们打得越好,我越安全,谈得越好,别的法子是没有的。”他们心中清楚,我党这种积极谈判和备战自卫的姿态,是在全面分析国内外时局以后,针对蒋介石坚持独裁、卖国和内战的反动方针做出的。根据阎锡山一部进犯上党解放区的情况,经反复讨论,会议最后确定集中万人“进行上党战役,坚决消灭该敌”。
我是一个军人,我真正的专业是打仗(2)
部署既定,刘、邓等离开赤岸村,会同李达一道奔赴平汉前线。次日,蒋介石授意何应钦印发蒋在1933年“围剿”红军编订的《剿匪手本》。就在当日下午,蒋介石同毛泽东进行第一次商谈,还表示一切问题愿听从中共方面意见,重提所谓中国无内战说法,提出了谈判三个原则。当日晚,还邀请毛泽东仍宿在自己的山洞官邸林园。
9月10日,刘、邓指挥所部发起上党战役,经攻城、围城打援两个阶段,坚决收复阎锡山部抢占的上党地区。蒋介石在重庆一边部署人同中共代表团谈判,一边密示所部:“目前与奸党谈判,乃系窥测其要求与目的,以拖延时间,缓和国际视线,俾国军抓紧时机,……待国军控制所有战略据点、交通线,如彼不能在军令政令统一原则下屈服,则以土匪清剿之。”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昭然若揭。
上党战役的隆隆炮声刚刚停止,平汉战役(也称邯郸战役)的硝烟又起。1945年10月16日至11月2日,刘伯承和邓小平周密组织、亲临指挥的平汉战役,争取高树勋率新八军起义进而达到围歼其他之敌,共毙伤敌3000余人,俘敌战区副长官马法五等高级军官以下万余人,并缴获大量武器、弹药等装备。这是刘、邓运用军政兼施、攻心为上谋略取得的一次很有影响的战役胜利。此役是继上党战役后我军给国民党军队的又一次沉重打击,引起国民党内部很大的震动,它对阻止国民党军队沿平汉路北进,掩护我军调整部署及争取国内和平的斗争,起了巨大的作用。
《孙子兵法·谋攻》说:凡用兵之法,“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又说“上兵伐谋”。
1945年10月,国共双方共同签订的《会谈纪要》(又称《双十协定》)墨迹未干,国民党就增兵80万,分四路进攻华北。首要目标是抢占平津、进军东北。马法五、高树勋等所部共万余人,是四路中的主力。
10月16日,刘、邓下达了组织平汉(邯郸)战役作战的基本命令,决定集中3个纵队和太行军区等部队共6万人,并动员10万以上民兵参战,围歼马法五、高树勋等部。24日,我各参战兵团按作战预案已大部赶到预定地区,形成了对敌包围的态势,随后,及时调整部署待机总攻。对刘、邓这一部署,毛泽东复电认为“部署甚当”。28日,后续部队全部到达,总攻时机已成熟。
在准备更大规模的军事打击的同时,政治方面争取高树勋的特殊战斗,也在秘密战场上悄然进行着。高树勋当时担任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1942年至1944年期间,高树勋就同我们党有联系,关系比较久。1945年9月,当高树勋率部开赴平汉路前,刘伯承和邓小平就布置4个月前派到高部任冀察战区总部参议的中共地下党员王定南,抓紧做好争取高树勋的工作。为此,刘伯承还亲笔写信给高树勋。
当高树勋部北上国民党军沿平汉路开进后,即派人与刘伯承、邓小平取得联系,表示了不愿打内战的意向。刘、邓抓住这一时机,设法召见王定南。邓小平告诉王:情况变化很快,高树勋新八军和河北民军已离开新乡,到达磁县马头镇。党中央和毛主席指示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拦阻国民党这3个军北进,这是我们当前严重的战略任务。刘伯承接着也讲了话。随后,邓小平明确向王定南交代任务:你现在就回去对高树勋将军讲,根据目前形势需要,他要就地起义,配合我们完成阻止国民党北上的战略任务。刘伯承则进一步要王定南促使高树勋痛下决心:这正是高树勋将军走向革命的大好时机,要他当机立断!同时,刘、邓把有关情况及时上报中央军委。这时,邯郸以西的峰峰矿区晋冀鲁豫野战军指挥所,成为刘、邓挥师痛歼敌军和秘密策反敌军的指挥中枢。
临阵策反,必须以坚强的军事实力为后盾,造成兵临城下,使其插翅难飞之势,并对反戈一击者必需的要求予以满足。此种策略需攻心为上才能奏效。高树勋长期以来受国民党中央系和孙连仲排挤,心怀不满,久有离心倾向,不愿在新内战中充当先锋,暗中已与我党建立联络,此时被包围,表现得更为动摇,战斗不积极。我军在待机总攻时对新八军实施佯攻,又打又拉,促其进一步动摇。尽管如此,高树勋对马上举义还是缺乏思想准备。正像邓小平后来所说:“高树勋倾向起义,但在犹豫当中。那时国民党要吃掉西北军,有这个矛盾。”所以,当王定南返回马头镇向其转告刘、邓的话时,他心存顾虑,长吁短叹地说:“多年来和我同甘共苦的妻子,以及本军其他家属,目前还在徐州,我们在这里马上起义,国民党岂不要迫害他们?”王定南直言相告:当前正是关键时刻,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至于家眷确是一个实际问题,为此,我可以马上去请示刘司令员、邓政委设法解决。在此前后,高部所有汽车、马车都是头向南,准备南撤。
。。
我是一个军人,我真正的专业是打仗(3)
10月28日凌晨,王定南再次赶到峰峰,向刘、邓汇报高树勋谈话结果。邓小平强调:他现在起义,作用重大,时机很重要啊!刘伯承也重申: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至于高夫人和其他军官家属安全问题,我们可以请示中央设法解决。说完,刘、邓即签发了请党中央设法护送高部家眷脱离险境的电报。当王定南把这些情况面告高树勋时,他非常感激,当即表示:我立即起义,走革命的道路。当日晚,刘、邓又委派野战军参谋长李达前往马头镇高部驻地,代表刘、邓与高接洽起义具体问题。李达曾与高树勋在西北军为伍,前者是1931年宁都起义时由西北军参加工农红军。仅这件小事就足见刘、邓对高树勋起义的重视。李达向高转达了刘、邓对他起义的欢迎之意,激励他发扬西北军冯玉祥、赵博生、董振堂等人的光荣传统,坚决投入人民的阵营,与此同时,刘、邓命令所部对包围之敌发起总攻,指挥北集团狠打第四十军,以南集团钳制第三十军、佯攻新八军。战至30日,迫使敌军再次收缩阵地。
10月30日,高树勋率新八军及河北民军等约1万人阵前起义,使敌兵力骤减,防御部署出现缺口,军心动摇。刘、邓根据各方面(包括高树勋方面)提供的情报判断:敌军内部恐慌,无心恋战,必以全力向南突围。故“围师必阙”,网开一面,将主力隐蔽地南移至漳河以北敌退路两侧。31日黎明前,当敌主力脱离防御阵地时刘、邓才突然把即将溃退之敌包围在南北旗杆樟等地,尔后,以“擒贼先擒王”的计策,于11月1日直捣敌军首脑长官部。2日,残敌大部被歼,仅少数漏网,战役宣告结束。
刘、邓指挥的平汉战役,是在比组织上党战役还困难的条件下发起的。关于这一点,邓小平在后来的回忆中讲得很清楚:“打了上党战役,虽然弹药有点补充,装备有点改善,但还是一个游击队的集合体。在疲惫不堪的情况下,又打平汉战役。队伍没有到齐,敌人进攻。”而“马法五的第四十军、三十军都是强的。高树勋的新八军也有战斗力呀!锡联在马头镇拼了一次,一拼就是几百人伤亡。”在如此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取得那样大的战果,高树勋率部起义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刘、邓对高树勋的义举非常重视。
10月31日,即高树勋正式宣布起义的第二天,刘伯承、薄一波并代表邓小平乘车到马头镇会晤高树勋等。几天后,刘、邓派人告诉高树勋,党中央已责成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张爱萍派人将高夫人等新八军起义军官家属,从徐州接送到解放区。高树勋感激地说:共产党办事真是言必信,行必果,实在了不起啊!
起义以后,高树勋部根据党中央指示,改编为民主建国军,高任总司令。刘、邓为整编这支起义部队又做了很多工作,包括调派干部,筹集资金等等。1946年2月,在送别被俘的马法五返回新乡之时,刘伯承、邓小平还与高树勋等亲切会晤,合影留念。在邓小平、薄一波等领导人亲切关怀下,高树勋本人于1945年11月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新中国建立后,曾出任河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副省长、国防委员会委员,并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全国委员。1955年被授予一级解放勋章。1972年1月在北京逝世。不过,邓小平以坦诚的态度回忆说:“我一直遗憾的是,后来我们对高树勋处理不公道。”有的老同志记得,解放以后,邓小平一直想给高树勋的职位安排得高一些。这是后话。
明朝开国功臣刘伯温在其所著的兵书《百战奇略·离战》中云:“凡与敌战,可密候邻国君臣交接有隙,乃遣谋者以间之。彼若猜贰,我以精兵乘之,必得所欲。法曰:亲而离之。”刘伯承、邓小平等运用此计技高一筹。他们在平汉战役胜利后总结了四条对顽敌作战初步经验,首要一条就是:“必须以政治、军事同时进攻,此打彼拉,打打拉拉,故拉了新八军,接着消灭了第三十、四十军,打退了第三十二军并十六军,在政治与军事上给了双重打击”。在总结战术经验时又充分肯定:由于奠定了战役胜利基础,“加上高树勋毅然反对内战,率新八军起义,更促成了战役的迅速结束和获得彻底胜利。”刘、邓运用军政兼施、恩威并重的方法,上兵伐谋,首创了全国解放战争中,利用国民党内部矛盾,策动其高级将领率部阵前起义,以促成战役迅速结束和获得彻底胜利的成功范例。
我是一个军人,我真正的专业是打仗(4)
“在解放战争第一年,我们完成了中央军委规定的歼敌指标。就二野所在地区来说,完成了分配给自己的份额,也许还超过一点。由于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战略反攻的时间提前了,比预定的不止提前一年两年。”邓小平曾这样总结第二野战军第一年的战绩。
上党、平汉战役结束以后,晋冀鲁豫解放区迎来了全面内战爆发前的相对沉寂时期。1945年11月中旬,邓小平与刘伯承率领部队返涉县赤岸村开了庆功大会,随后,决定将成立不久的晋冀鲁豫中央局、军区迁移到涉县以东、邯郸以西的武安县下柏树、龙泉、伯延一带。时间是12月底。
这时,高树勋部起义后由马头镇北上武安县伯延镇,刘伯承、邓小平在伯延期间,帮助高树勋部整训部队。当时,刘、邓住处离高树勋住地不远,当时高部被改编成立民主建国军誓师大会的会场,如今是一所小学的操场。
在武安县时,邓小平一家五口人团聚在一起。自从1939年9月结婚以来,由于南征北战全家人难得团聚一次。1946年3月2日,刘、邓率领晋冀鲁豫领导机关又由武安东移至邯郸。这是在平汉线上的一座较大城市。
1946年1月,国共停战协定签订以后,国共两党和美国三方代表组成“三人小组”及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军调部派出执行小组分赴各地执行任务。于是,邓小平同刘伯承一起,又开始同美、蒋代表人员进行艰难的“和谈”斗争。
从保存下来的历史照片看,1946年6月前,邓小平会见了军事调处执行组成员。地点可能是在邯郸市。照片上,邓小平站立在前排,美蒋代表并肩而立。照片上的人都没有表现出高兴神情。邓小平面容平静,目视前方,头脑中清醒地意识到时局的复杂性。
果然,1946年6月底,以国民党军大规模围攻中原解放区为标志,全面内战爆发了!6月28日,邓小平同刘伯承来到邯郸以南15公里的马头镇车站,出席第三、第六纵队全体指战员参加的誓师出征大会。刘、邓登上用小火车皮搭成的讲台,先后作打好自卫反击战的动员报告。他气愤地告诉指战员:“蒋介石不遵守政治协商会议和停战协定,并已公开撕毁停战协定向解放区全面进攻了。”
邓小平的目光扫视着全场,言简意赅地说:“蒋介石认为他们的准备已经很充分,可以在三个月至六个月全部消灭人民解放军。”他“虽有美国援助,但他发动反人民内战,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他的军队士气不振,经济困难,是他无法克服的。我们虽无外援,但人心所向,士气高涨,经济亦有保障,我们一定能够打败蒋介石。”
他语气坚定,满怀信心地向大家提出号召:“要迅速作好一切准备,粉碎蒋介石的进攻”。“我们要有足够的信心,打好自卫反击战这一仗”。
邓小平在大会上是这样信心百倍地号召大家去迎接新的战斗,但对实际困难也是心中有数的。他后来在闲谈中曾说:
“我们这个部队,在外边名声很大,都叫什么刘邓大军,其实我们就这么点家底,兵力不足5万,外加几门山炮、迫击炮、弹药也很缺。尽管我们很困难,还要支援延安,因为陕北比我们更困难。……我们部队的这一批战士,大部分都是翻身解放的农民子弟,素质很好,陇海战役伤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