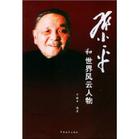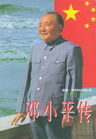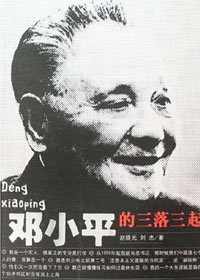邓小平的三落三起-第2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时,工厂领导罗朋恰巧有事外出,大家围在邓小平身边一时束手无措。还是卓琳有经验。她用手摸摸邓小平的头,看看他的眼睛,告诉监管人,“给他冲点白糖水喝就会好一些。”在电工班和卓琳一起干活关系很好的青年女工程红杏忙跑回家中,端来冲得很浓的白糖水。喝过白糖水,邓小平渐渐地清醒起来,脸色也略为好些。随后,陶端缙驾驶拖拉机把邓小平送回了将军楼。笔者1995年5月到该厂,还看到这辆拖拉机放在那里。
工人们还看到,邓小平身上,保留着劳动人民勤俭节约的好传统。1970年的农历五月初五,是邓小平夫妇到江西后的第一个端午节。这一天,和卓琳在一个电工组的青年女工程红杏,拿着在街上买的糯米和粽叶来到将军楼,帮助卓琳包粽子。
这时,邓小平从菜地里忙走了进来,微笑着和程红杏打招呼。程红杏想起来,自己刚才看见邓小平正在菜地里种着菜,感到很惊奇:这样大的干部,自己还会种菜呀!
过了一会儿,正在做饭的邓小平继母正准备把一碗变了味的菜汤倒掉,程红杏也凑过去,用鼻子闻了闻,也觉得变了味,说不要吃了。没想到,邓小平闻后笑着说:“煮开后,还能吃。”这件小事使程红杏很受触动,一直铭记在心。不久,“老头真节约,连一碗馊了的菜汤都不肯倒掉”的佳话,就在工人们中间传开了。
。 想看书来
我是刘少奇之后第二号“副统帅”(5)
有一次,邓小平用的面盆底部漏了个小眼,就用小棉球堵起来用,后来小眼变大了,邓小平就拿到车间去,请工人给焊一下。工人们把脸盆焊好后,又点了点漆,陶端缙亲自给送来。看到陶端缙来送修好的脸盆,邓小平忙招呼他在客厅的大沙发上坐下,两人聊了起来。
话题转到了工资上。陶端缙说:“我们虽然工龄不短了,但工资十分低,孩子又多,生活十分困难。”
实际上,当时有关部门已停发邓小平夫妇的工资,只发给生活费。但邓小平不为所动,好像没有发生停发工资的事一样。对眼前这位老工人的叙述,他却格外关注。他心情沉重地说:“这个事我知道,你们这一类工人都有家,有好几个孩子,工资很低,我都知道的。”
陶端缙看得出来,邓家生活也不宽裕,他们不仅自己种菜、养鸡,连碗变味的菜汤也舍不得扔,脸盆坏了还修理了再用。于是,他问:
“你每个月吃多少米,够不够吃?”
“够了,我每月吃粮26斤,多吃一点蔬菜。什么蔬菜我都喜欢多吃一点。”“你生活上还需要什么?”
邓小平坦率地说:“我喜欢喝点米酒,有时自己也做点。”看到对方对自己会酿酒感到奇怪,他笑了笑又接着说:“其实,做米酒很简单,也很容易做。先煮糯米饭,加点酒药,放点白糖,再用罐子装起来密封好,过几天就可以吃了。我现在喝的米酒都是我自己做的。”
陶端缙告诉邓小平:“那好哇,酒药、糯米,我那里都很容易搞到,你要的时候,告诉我一声就行。”邓小平笑着说:“行呀,可以,可以。”……
1977年7月,邓小平夫妇当年劳动过的工厂收到邓家从北京发来的一封热情洋溢的来信。这封信,表达了邓小平一家对工人们的深情厚谊:“我们在你们厂的三年劳动、学习中,与广大工人和干部结下了深厚友谊,工人和干部对我们的关心和帮助,使我们感动难忘。”
邓小平曾这样对别人讲:我这里生活是很单调的。娃娃们不在身边,真有点想他们。在子女心目中,邓小平是慈父。
邓小平夫妇在将军楼中住下后不久,就提出能否让在陕西插队的小女儿邓榕先来南昌和家人见面,因为她不知道三位老人南来江西,结果杳无音信。后来又提出让大女儿邓林前来,答复是子女可以前来,但江西省革委会不出证明联系,很明显,这是一种不赞成。卓琳难过,邓小平坐在沙发上面无表情,默默无语。
有一次,邓小平和监管人交谈时,不无惆怅地说:“我这里生活是很单调的,想写信给中央,能否让两个小孩靠近我们。现在看来不行就算了,娃娃们不在身边,真有点想他们。”
看着对方年轻的脸庞,邓小平深深吸了一大口烟,面带苦涩地微笑说:“你年纪还轻,还没到年龄,到了我们这么大岁数了会有这种感觉的。”思念之情,溢于言表。
1970年春节前夕,小女儿由陕西来到南昌,这真是喜从天降!小女儿聪明活泼,性格开朗,喜爱唱歌。来那天,一走近将军楼,老远就跑着叫爹爹、妈妈,当她一下子扑到邓小平怀抱里时,一向不善于感情流露的邓小平双眼迸放着慈爱、喜悦的光芒,父女久别重逢的这番情景感人至深。
1971年冬天,邓小平夫妇为二女儿举办了十分简朴的婚礼。那一天,将军楼内外笑声不断,呈现出从未有过的喜庆气氛。看着子女们在困境中得到锻炼,如此豁达、乐观,而且长大成人了,邓小平脸上绽开了笑容。
二女儿怀孕临产时,她准备在父母身边生养,并希望婆婆同往。婆婆心想,我一个乡下老太婆,亲家毕竟是当过“大官”的,去那能合适吗?经再三动员,才前往南昌市。
没想到,刚一见到邓小平时,拘束感就消失了不少。邓小平很和气地对她说:“我们是革命家庭,没有什么规矩,你随便些,想吃什么就请随便做好了。”
孩子生下来了,是个女孩儿。有一天,邓小平坐在将军楼门前,怀抱着小外孙女合影。小家伙的眼睛怎么也不看前方。邓小平一边用手逗着,一边嘴里叨念着。无奈,小外孙女就是不往前看,“咔嚓”一声,照相机里留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邓小平穿着棉衣,头戴圆帽,怀抱小外孙女,看到隔代孩子的出生,他心里涌起难得的快慰。
。。
我是刘少奇之后第二号“副统帅”(6)
邓质方,小儿子,读中学时,小儿子就爱好搞无线电,头脑很聪明。“文化大革命”初期,到山西插队。1970年,他也前来南昌探望年迈的父母。小儿子的到来,使邓小平夫妇心里感到十分喜悦。当天晚上,父子俩畅谈到深夜。从社会讲到家庭,从学习讲到生活,带来了许多外界新闻,邓小平听了感到很是忧虑。他已经看到,“文化大革命”发展越来越偏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正确轨道,连“伟大舵手”毛泽东本人也难以驾驭了。
最令邓小平惦念的是大儿子。他们知道,这个出生在太行山区,由老战友刘伯承起名“朴方”的儿子,从小学业就很好,“文化大革命”前是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文化大革命”初期因受“第二号走资派”问题的株连,受迫害致残。更使两位老人牵肠挂肚的是:邓朴方住院治疗期间,身边却没有任何家人护理。后来从亲属来信中得知,邓朴方已被撵出医院,送到了北京郊外的清河救济院。当时,他身体已十分衰弱,胸以下肢体瘫痪,时常发高烧。儿子的不幸遭遇,令两位老人十分悲痛,他们的心几乎都被揉碎了。
恰巧这时中办和江西省革委会在商量怎样护理邓朴方的问题。邓小平及时致信党中央,表明要把大儿子接来自己照顾的愿望,获准后,邓朴方得以前来南昌。妹妹跳跃着扑到父母怀中,不同的是,邓朴方是坐着手摇车来到父母跟前的。
晚上,邓小平夫妇帮助儿子洗澡。邓小平手拿热毛巾一遍又一遍地擦抚儿子的肌肤,还仔细地询问着病情。儿子双手扬着,一边比划一边告诉父母:“从胸口往下,都不是我的了,我成了半截啦。”听到这些话,两位老人难过得半晌说不出话来。
夏天的南昌非常炎热邓朴方每天都需要洗澡、翻身。这些沉重的护理工作,便由邓小平主动承担下来。他先把洗澡水烧好,再组织全家人帮忙,把很胖的邓朴方抬进洗澡间。在热腾腾的蒸汽中,他一丝不苟地给儿子擦胸搓背,还得耐心地听从儿子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的指挥。
邓朴方平稳地坐着,面对父母及家人平静地讲述着自己欲见亲人的痛苦往事:“一天清晨,我起床后吃力地挪动着瘫痪的身躯,坐进手摇车时,没跟任何人讲,就一个人悄悄地摇出了救济院。我不知道你们在什么地方住,还想到中南海去找你们。我用力地摇着手摇车,和太阳比赛,沿着柏油马路,直向北京城。凭着双手力量,我摇了几十里路,终于来到中南海西门。坐在车里,我在西门外的马路旁,静静地向中南海里望着,一望就是几个小时。我想,也许能望见父母,或者望见那些从小就熟悉的伯伯、叔叔们,总之,我是多么想见到亲人啊!”
邓朴方的话,深深地打动着邓小平夫妇的心。为了不使邓朴方在家中寂寞,邓小平经常考虑怎样给他找点事做,丰富他的生活内容,在精神上给他以安慰。
有一次,邓小平在车间里主动问陶端缙:“厂里有没有修理电机方面的事情可干?”回答说没有。邓小平又问:“有没有无线电技术的或者收音机修理方面的事情可干?”陶端缙想遍了厂里的种种工作,确实没有这方面的事可做。邓小平告诉陶端缙:儿子邓朴方在家里闲着,能给他找点这方面的活儿干就好了。他得知厂里确实没有这方面的活儿,仍抱着一线希望,第三次询问陶端缙:“你家里有没有收音机呀?让孩子修理一下也好,这也使他不至于整天躺在床上闷得慌。”看到对方因生活拮据,没有收音机,当然也无法拿来修理时,邓小平理解地点了点头,便不再提这件事了。为儿子的一点小事开口求人,对于邓小平来说是不多的。
把我从江西“牛棚”接回来(1)
“文化大革命”是“左”了,被坏人钻了空子。林彪这个人不能说没本事,就是伪君子,利用毛主席抬高自己。林彪垮台了,我们党的日子会好点,就是还有那么几个书生在胡闹。
—— 1982年11月邓小平在井冈山参观时的谈话
一九七三年周恩来总理病重,把我从江西“牛棚”接回来,开始时我代替周总理管一部分国务院的工作,一九七五年我主持中央常务工作。
——1987年10月13日邓小平会见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卡达尔时的谈话
在一些执行“左”倾路线很卖气力的人眼中,与邓小平很难交谈。有这样一次别开生面的思想汇报。
邓小平夫妇来江西一个月后,监管人奉命要邓小平写出劳动和学习心得,实际上是想了解其“思想动向”,看其“认识错误”的态度。结果,邓小平十分不快,只说了一句“我准备给毛主席、党中央写信”的话,就转身走开了。后来,监管人改变态度征求邓小平对其工作的意见时,邓小平平心静气地介绍了自己的情况。
这次“思想汇报”倒成了邓小平对监管人的思想教育。以后,上级又再三催促:他们来劳动一年多了,让他们总结总结嘛,你给他们宣传宣传。于是,监管人用纸写下了两段毛主席语录,放在邓小平的饭桌上。
邓小平当然理解此举的含义,但他并未理会,还是平静地吃饭。不几天,上级催促紧了,监管人又继续送来类似的两条语录放在桌子上,邓小平仍旧熟视无睹,没有愠怒,没有惊异,和往常一样,大口地吃着饭。
还有一次是十多分钟的尴尬会面。1970年5月,江西省执行林彪意图颇为卖力的一号人物×××来到将军楼,他自命不凡,开口就问:“你来江西劳动七八个月,觉得怎么样,有什么体会?”
对方傲慢无礼的态度,使邓小平心中充满不悦,他不动声色地回答:“我昨天给中央办公厅汪东兴写了一封信,请他转交给毛主席,我的全部情况都在信里讲得很清楚了。”
不卑不亢,不软不硬,一句话就顶了回来。这位人物暗自掂量了一下,知道自己远不是邓小平的对手。于是,他改换话题,讲起自己1967年以来主持江西工作的情况,介绍江西省三年来的“大好形势”,以及对今后“全国山河一片红”的乐观态度。他喋喋不休地讲着,看邓小平也不反对也不附和,没有表态,只是端坐在沙发上,两眼直视前方。心中很不是滋味,又转换话题聊家常:“你还有什么困难,有什么要求吗?我可以帮助解决,你尽管讲好了。”
邓小平依旧是神态安然,语气如常:“我的意见在昨天的信里已经通过中办主任汪东兴向毛主席汇报了。”说完,只管凝思养神,不再理这位不速之客。
这个人物明白,再坐下去是自讨没趣,不如尽早离开。于是,他很尴尬地说:“我们走吧。”从上楼到下楼,总共不过十来分钟。
这次会面,邓小平虽然没说什么话,但在他心中留下深深的记忆。1972年11月他在听取江西省某县汇报时说:“两年前有人给我讲过江西形势如何大好,我看完全是吹牛的。”
此后,这个人物又到将军楼来过两次,不过,他接受了第一次的教训,来时态度不再傲慢,谈话内容也只限谈家常而不谈政治了。
古语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林彪一伙的倒行逆施既严重破坏了我们党、国家、人民的事业,也加速了自己灭亡。邓小平第二次“起”的机遇出现了。1971年9月13日,林彪篡党夺权阴谋败露,仓皇叛逃以后,拖拉机修造厂也于11月初向全厂职工传达了中央通知和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证材料。邓小平夫妇以普通职工身份听了传达。文件传达了两个半小时,邓小平表情平静,镇定自若,始终没离开座位,也没和别人交谈。根据工厂安排,他听了一会儿工人们的分组讨论,就带着文件回到将军楼。
邓小平子女们急于知道父母所听的文件内容,因监管人在场,卓琳便把女儿拉到厨房,用手指在她手心写下“林彪死了”四个字。待全家聚在一起听卓琳讲述文件内容时,邓小平也显得很兴奋,但是他只说了八个字:“林彪不死,天理不容!”一句话,道出了邓小平对林彪集团祸国殃民罪行的深恶痛绝。这天晚上,邓小平全家十分高兴地坐在一起打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