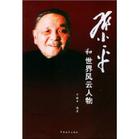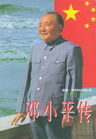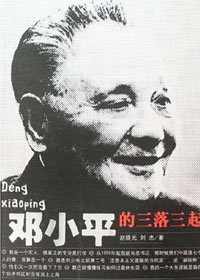邓小平的三落三起-第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邓小平是18岁那年,在异国他乡的法国投身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滚滚洪流中来的。他很少讲自己的革命经历,更很少讲自己的童年。
作为中国人民伟大的儿子,邓小平深情地爱着他的祖国和人民,对于生养自己的故乡他也很怀恋,但是,自从1920年夏由家里的山溪走出来,经过嘉陵江,长江,飘洋过海到法国,他就再也没有回到生他养他的家乡。1949年末,他和刘伯承率几十万大军进到西南,离家乡很近了,但他还是没有回去,倒是在重庆住下来,一忙就是数年,直到奉调进京,担负更重要的职务,行前,也未去故乡探望一下。80年代,他作为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又陪同外宾来到故乡附近,但还是没有回去,只是在成都住了下来。还有60年代……
什么原因呢?据他的女儿讲:父亲自己不回老家,也不许我们回去。他说我们一回去,就会兴师动众,骚扰地方。其实,还有他实在是太忙了。50年代初,大西南百废待兴,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任总书记,这是他一生中最繁忙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十年他开展工作步履维艰,70年代以后他为徘徊不前的中国指方向、绘蓝图。说起来也是巧合,我们共和国有10位元帅,四川籍元帅有朱德、刘伯承、陈毅、聂荣臻4位,他们离开家乡后,竟都没有再“衣锦还乡”,倒不是他们淡漠乡情,和邓小平一样,他们心中装的是天下事、国家事、民族事,家事自然难以顾及了。尽管如此,他们无时无刻不眷恋着生养自己的故乡,关切着家乡的变化,每当有家乡人前来,都要在百忙中抽出时间会见,询问情况。毕竟是父老乡亲们对自己有着养育之恩啊。邓小平家乡现健在的惟一的一个表弟淡文全曾经十分感慨地说:“小平同志的胸襟宽阔,他关心的不是家人,而是整个家乡、整个国家的建设发展。”有一年,淡文全到北京,小平忙于国事,无暇顾及,只叫国务院接待办的同志接待一下。淡文全在国务院接待室住了十来天,便重返广安。
从现在的《邓氏家谱》中看,记载是从邓鹤轩开始,邓家原籍是江西省吉安府庐陵县,洪武十三年,以兵部员外郎入四川,迁家广安。据家谱记载,邓家在历史上曾经是一朝三驸马,一门二十侯,唐宋元明,均有伟人出现。到邓绍昌这一代,已是三代单传。不过,农历龙年得子,加上望子成龙的愿望,邓绍昌给自己的长子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邓先圣,5年后起学名为邓希贤,18年后,为适应白色恐怖下秘密工作的需要,在武汉,又更名为邓小平,而且被尊称了整整70年。
邓小平的故乡四川省广安县位于重庆以北150公里,以前不通火车,靠船做交通工具。县城主要街道长不过1华里,宽不过5米。邓小平出生、居住地在县城北公里的协兴乡牌坊村。他的父亲邓绍昌,母亲是广安县望溪乡人,姓淡。
据邓小平旧居管理人员介绍:“邓家老院子”一共是16间,邓小平曾祖父、祖父、父亲,三代人历经数十年修成了一个三合院,和别的农舍差不多,这房子也是白灰抹的墙,木头搭的门,青瓦盖的顶,一排正房略高一点,两边的偏房各有数间,左中右面的中间是一个平坎。
我在法国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2)
1950年,邓小平把住在这些房子里的家人全都接到重庆居住,两年后土改时,邓小平写来信讲,家里人不回来了,房子就分给贫下中农住。当时分给4户人,后来又变成了8户。1987年把屋子腾出来供大家参观。
1904年8月22日(农历七月十二日),邓小平出生在广安县协兴乡牌坊村。5岁进私塾发蒙,后转入新式小学。高小毕业后,考入广安县中学。1919年秋考入重庆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受五四运动的影响,这时他有了朴素的“工业救国”的爱国思想,他同全校同学一起参加抵制日货、声讨卖国贼的活动。1920年夏,赴法国勤工俭学。
这段文字可以扼要地概括少年邓小平的活动情况。邓小平的女儿认为:父亲的少年时代,则可以说过得十分平常。现在在一些亲戚中和乡亲们中有一些关于父亲少年时代的带有传奇味道的传说,多不可靠。值得说明的是,邓小平的出国留洋,是他的父亲给选择的,并且极力主张,其母亲倒是恋恋不舍。父亲的选择当时并非是让儿子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连邓小平当时自己头脑中想的,也只是想外出学点本事,而没想到一去就再没有回来。职业革命家的道路是邓小平自己选定的,一经选定就再也没有动摇过。但是,选择这条道路也并非是轻而易举。
邓小平曾经告诉自己的女儿,在当年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中,“我是那一批八十几个人里面最小的,连发言权都没有。”
1920年8月27日,刚刚过完16岁生日的邓小平,和从重庆留法预科学校毕业的其他82名川东子弟,告别家乡离开重庆,9月11日,在上海登上法国邮轮“盎特莱蓬”号,开始了前往异国他乡的远航。历时39天,终于在10月19日到达法国南部城市马赛。
首次出国远航的印象肯定相当深刻。比他们晚两个月赴法的周恩来曾这样抒发当时的感受:“出国去,走东海、南海、红海、地中海,一处处的浪卷涛涌,奔腾浩瀚,送你到那自由故乡的法兰西海岸。”
邓小平虽然没有那样诗情画意地抒发当时的感受,但是,50多年后,他多次谈自己当时乘坐的就是“几万吨轮”。
法国城市特别是巴黎的繁华、气派,异国他乡的风土人情,和旧中国的贫穷落后、腐化不堪,在这些青年学生的心理上形成了鲜明的反差。邓小平也是带着这种美好印象开始了勤工俭学的生活。
1920年10月21日,邓小平和其他中国留学生入巴耶中学学习。但是,5个月后因费用无法自己负担,不得不离开中学,“俭学”不成,只好“勤工”,但是,邓小平决然没有想到,此次离开校门,就再也没有迈进法国学校的大门。“俭学”的希望破灭了。
勤工俭学这个出国留洋的初衷,在现实面前被抛得越来越远,邓小平等首先不得不打工,以维持自己的生活。他也未能想到,这种打工一干就是4年多。
第一个做工之处是法国南部重工业城市克鲁梭的施奈德工厂。“工种”是轧钢车间的轧钢工,进厂注册日期是1921年4月2日,编号是07396。76年以后,来华访问的法国总统希拉克将邓小平在法国勤工俭学时使用过的工作证件亲手交给###同志,并说:“我仔细地找过施奈德工厂的档案。”###同志接过镶在镜框内已发黄的工作证件时,非常高兴。他回赠希拉克一首他亲笔书录的唐诗:“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可以想象,轧钢工的劳动强度极大,而且十分危险,工时又很长,这对于不满17周岁,身材矮小的邓小平来说,是多么不堪重负呵!然而,做的是苦工,挣得的工资却十分低廉。显然,温饱还是解决不了。后来,邓小平在谈起这20多天的轧钢工生活时说:在克鲁梭拉红铁,做一个月的苦工,赚的钱连饭都吃不饱,还倒赔了一百多法郎。
我们从邓小平入厂前的一个月(1921年3月3日,这是迄今为止搜集到的邓小平最早的照片)的留影看到:他虽然穿西服、扎领带,仍然是一个身材不高,脸上挂着学生气的青年。
我在法国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3)
第二个工作之处是在巴黎运河边上的一家专门制作扇子和纸花的香布朗工厂。“工种”是“扎花工”,就是用薄纱和绸子做花,然后把花扎在一根铁丝上。邓小平经过了5个多月的“失业”,于1921年10月22日来到这家小工厂做工。扎花所得仍旧很少,一般的女工每天可挣两个以上的法郎,熟练工每天才挣得10多个法郎。况且这还不是固定工作,两个星期以后即11月4日,邓小平和同学们被工厂解雇,他们又被送回到失业大军的行列中,而且一呆就是3个月。
第三个工作之处是在蒙达尼附近夏莱特的哈金森橡胶工厂。“工种”是“制鞋工”,加工防雨用的套鞋。每星期工作54个小时,每天是10个小时。实行计件工资。邓小平每天可以做20多双鞋,大约可挣十五六个法郎,每月所得除生活费用外,可以剩余200多个法郎。这一段,他的做工生活比较稳定。这从当时和他在一起的人回忆中可略见一斑。“晚饭后至睡觉时间有二小时至三小时可以利用。此时木棚里很热闹,看书的人很少,甚至没有,大家闲谈、开玩笑、相骂,幸而没有相打的。有个四川小孩子,矮矮的,胖胖的,只有十八岁,每日这个时间总是跳跳蹦蹦,走到这一角同人说笑话,又走到那一角找人开玩笑。”这个“小孩子”就是当时的邓小平。
不过,这种稳定生活从邓小平1922年2月14日入厂至10月17日第一次主动要求离开,时间是6个月。要求离开的原因是前往塞纳夏狄戎中学继续求学。可惜,因为钱不够,无法完成学业。所以,不得不于1923年2月2日重新回到哈金森工厂做工。这次做工时间仅仅为1个月零几天,他第二次主动要求离开哈金森工厂,记载他情况的工卡上注明离开的原因是“拒绝工作”。其实,工厂并不知道他离开的真正原因。因为此时,邓小平已成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一年后易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一员,成为一个具有一定政治觉悟和选择共产主义为自己理想的革命青年。
邓小平曾回忆说:在法国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而且都是杂工。在这里,他初次接触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亲自体验了劳动工人阶级遭受压迫、剥削的悲惨境遇。在此期间,他出国时所抱的“勤工俭学”的梦幻最终破灭了。不过,正像他几年后在莫斯科的追述:
“最初两年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虽略有感觉,然以生活浪漫之故,不能有个深刻的觉悟。”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我在军队那么多年没有负过伤(1)
1974年4月,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发言,系统阐述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
我在军队那么多年没有负过伤,地下工作没有被捕过
我们在上海做秘密工作,非常的艰苦,那是在吊起脑袋干革命。我们没照过相,连电影院也没去过。我在军队那么多年没有负过伤,地下工作没有被捕过,这种情况是很少有的。但危险经过好几次,最大的危险有两次。
——邓小平的回忆
邓小平和他的战友们回国了。出国时,少年邓小平从海路坐轮船前往法国,历时一个多月,一路上欣赏着大海,回国时,年轻的邓小平是从陆地走的,火车、汽车、骆驼、马匹,从1926年底到1927年2月,备尝了旅途艰辛,用邓小平的话说:这一路上,足足一个多月,连脸都没洗过一次。光骑骆驼走沙漠就整整走了8天8夜。
这时正是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高潮时期。邓小平受中国共产党的派遣回国,到西安冯玉祥国民军联军担任中山军事学校政治处处长,兼政治教官,并任该校中共组织的书记。关于这所中山军事学校情况,邓小平有这样一段回忆:
“这个学校是当时担任国民革命军驻陕总司令于右任办的,于当时属于国民党左派,这个学校的主要职务都是由党派人担任的。校长史可轩是党员(后牺牲),副校长是由苏联回国的李林同志(我们在法国就熟识,李后在中央苏区牺牲),我同时担任校党的书记。”
邓小平和他的战友们是如何活动的呢?他的自述告诉我们:“学校经过短期筹备,很快办起来,学生不少是党团员,除了军事训练外,主要是政治教育,健全和发展党团等项工作。政治教育主要讲革命,公开讲马列主义,在西安,是一个红色的学校。这个学校在1928年成为陕西渭华暴动的基础。”
从2月到西安到6月离开,短短4个月时间,邓小平等中###员们做了大量工作。紧张的工作,不宽裕的生活,并没有使邓小平悲观,精神上反倒更乐观,他还记得当年敲史可轩的“竹杠”让他请客,吃牛肉泡馍。可见,那时大家的关系是很密切的。
笔者曾于1991年在西安附近见到史可轩同志的坟墓,墓碑上的字是邓小平建议当时的党中央主要领导人给题写的,足见他不忘牺牲同志,重视友情。
“那个时候我是中央的秘书,是政治秘书。八七会议的时候,我们住在武昌,……会议是号召搞全国起义,全国到处起来,从八一就开始了。”这是邓小平后来回忆他初到武汉时的情况。
1927年是中国现代革命史上一个重要的年份。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政变,汪精卫在武汉背叛革命。参加了汪精卫在郑州召开的###会议的冯玉祥,开始清除自己军队中的共产党员。邓小平经与其他共产党员研究,在冯玉祥以“集训”为名,集中共产党人于开封,最后“礼送出境”之前,由西安前往武汉,在6月底7月初到达。到中共中央机关工作,被分配担任中央秘书,不久,汪精卫主持的武汉政府也公开###,严重的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为适应秘密工作环境,他从此改名为邓小平。
刚到中央机关工作,就发生了一件令邓小平记忆犹新的事情:有一次党中央主要负责人陈独秀主持召开会议,讨论河南问题。会议相当简单,没开多久,陈独秀说了句“耕者有其田”就宣布散会了,表现得相当武断。由于会议很短,讨论问题很少,邓小平又不熟悉情况,而偏偏被责成根据会议记录起草一个给河南省委的文件。结果,他只好写了三百多字,还被有的同志认为太简单了,告诉下一次再写长点。
随后,他又以中央秘书身份参加了令他终身难忘的八七会议。这次中共中央紧急会议,纠正和清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