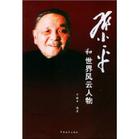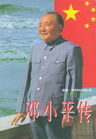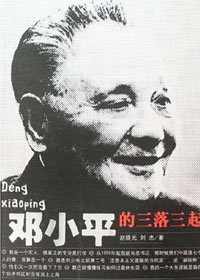邓小平的三落三起-第1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大别山这场斗争,主要是我们政策对头,包括军事政策。”
部队初进大别山,地形不熟,语言不通,缺乏山地作战经验,并且无后勤供给。当地匪特造谣惑众,说什么:“刘伯承一个眼睛,现在两个都瞎了,不能指挥我们,要失败”;“刘、邓要回四川,我们来送,将来怎么回北方”;“刘、邓在冀鲁豫未来,用电台指挥”等等。上述情况使部分指战员对创建大别山根据地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产生了怀疑,出现了信心不足的右倾情绪和违法乱纪的现象。9月27日至29日,刘、邓在光山县砖桥乡文氏祠连续3天召开旅以上干部会议,史称“王大湾会议”。又被风趣地称为“安卵子会议”。
邓小平在会上分析了全国形势后说:“党中央对我们这次行动的意义作了充分的估计。现在,我们不但保存和进一步巩固了原有解放区的基本地域,而且把战争引向蒋管区,迫使蒋介石把战线由黄河移到长江。同志们可以看到,中央这步棋下得多么英明,多么有远见。”他话题一转:“可是,我们有些人只看到自己的艰苦,而看不到全战场的新变化……”随后,刘伯承作了长篇讲话,他号召干部要“挺起腰杆站队”。至今,有位当年给会议送水、洗衣服的老人还清楚地记得当时会议情况,开会时,首长们都蹲坐在地上,邓小平讲话时挥着手,很激动。会议开得很好。
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我这一生,这一个时候最紧张(7)
关于“王大湾会议”的地点问题,有人在当地党史部门听到这样说法,实际上,光山县并没有王大湾这个地名,文氏祠所在地方并非叫王大湾。当时言称王大湾开会,是为使会议在极端保密情况下顺利召开所采取的一种方式。这次会议使大家明确了坚持大别山斗争和全国战局的密切关系。坚定了克服困难的决心。从而成为坚持大别山艰苦斗争的一个转折。后来,邓小平讲:“特别在困难的时候,尤应鼓励部队坚决作战,把敌人士气压下去,才能巩固自己的士气。大别山九月就有这个经验。”很快,主力部队在大别山南麓就取得了高山铺等战斗的胜利。
不久,在主力逐步北移过程,部队中又出现了急于求战的急躁情绪。“总想打个歼灭战”。邓小平回忆:“我们开了个会,我讲的话,提出要避战。因为那时打不得败仗,一败就不可收拾”。在他看来,大别山斗争的胜利不决定于消灭好多敌人,而决定于能否实现党中央、毛泽东战略决策:付出代价站稳脚,站得住就是胜利。“一切为了站稳脚跟”。这样,刘邓大军前抵长江,扩大了解放区,面对武汉等敌重兵盘踞的大城市,威胁国民党统治,“这是个真正的胜利,前进一千里的意义就在这里”。
一位老同志在当年日记中这样记下了邓小平:“8月30日。邓政委报告:我们已经到了大别山;9月12日、13日。黄家湾,首长们住下后,出外散散步,他们一边走,又好似一边在想,部队到一个新地方,地形不熟,敌情不明,担心吃亏。邓政委老看着那几匹骡子,是否又要叫我们减少呢?10月21日。由洗马畈起身,爬三角尖,马不好骑,刘司令员用竹竿做手杖,一步一步向上走,邓政委不用手杖,抓着小树直向前冲。……刘、邓很喜欢向这些老和尚问东问西;11月10日。开会,邓政委先作报告,后刘司令员作报告;11月27日。今日特别高兴的和值得记载的是刘伯承、邓小平与李先念会师了;12月10日李达参谋长找我说:今天按前天分的走。保密。我同邓政委、李副司令员向南,刘司令员向北,怎么走,刘司令员知道;12月11日。到苏家河西北之崔家坂。从此心照不宣,按名单有计划地分开。”
留在大别山指挥其他几个纵队(1)
1939年8月,邓小平、卓琳在延安结婚,成为革命伴侣。这是回到太行山的邓小平和卓琳。
我一个,先念一个,李达一个,留在大别山指挥其他几个纵队
就是我一个,先念一个,李达一个,带着几百人不到一千人的前方指挥所留在大别山,指挥其他几个纵队,方针就是避战,一切为了站稳脚。那时六纵担负的任务最多,在大别山那个丘陵地带来回穿梭,一会儿由西向东,一会儿由东向西,今天跑一趟,明天跑一趟,不知来回跑了多少趟,调动敌人,迷惑敌人。别的部队基本上不大动,适当分散,避免同敌人碰面。这样搞了两个月,我们向中央军委、毛主席报告,大别山站稳了,实现了战略任务。
——1989年11月20日邓小平会见编写第二野战军战史的老同志时的谈话
邓小平、李先念、李达在大别山坚持内线斗争的两个多月,是刘邓大军“反攻以来面临的最大考验”。在险象环生的情况下,辗转于大别山北麓的丘陵地带。特别是第六纵队担负的任务最多,来回穿梭。一会由西向东,一会由东向西,今天跑一趟,明天跑一趟,不知来回跑了多少趟,调动、迷惑敌人。
据一位老同志的《前指纪事》记载:1947年12月11日,邓率前指在湖北省黄安(现红安)县;16日到河南省新县;22日东进到商城县;24日东进到安徽省金寨县;26日返回商城,连续3天北上,30日又东进至金寨县,6天后又返回商城,第二天又继续西进。正如邓小平以中原局名义发出的指示电所言:“好击必击,不好击就游。游,必采取以迂为直的行动,不可老走一路,不可老驻一地。”
令人感慨的是:率部与敌人日夜周旋的邓小平,自己虽然时刻处于艰难危险之中,却时刻惦念着转战陕北,吸引胡宗南重兵的党中央和毛泽东。有一次,他高兴地告诉大家:我们已有3天没有得到陕北方面的消息了,今天收到党中央发来的电报,说毛主席和中央机关安然无恙,所以喝一杯庆贺酒。
邓小平不仅着眼于全国战局,还关切着友邻部队。当粟裕等得知大别山区斗争十分艰难,要支援大别山,并得到中央军委批准时,邓小平于12月22日提出:大别山局势虽然严峻,但我们已做好思想准备。“我们在大别山背重些,在三个月内,陈粟、陈谢能大量歼敌,江汉、桐柏、豫陕鄂和淮河以北地区能深入工作,对全局则极有利。”
而他告诉自己所属的指挥员:就是要多背一些,背重一些,釜底抽薪就不要怕烫手,调动敌人回援根本重地,是个关系全局的战略行动。我们多背一些敌人,宁愿本身多忍受一个时期的艰苦,也要拖住敌人几十个旅于自己周围,使山东、陕北的兄弟部队能腾出手来大量消灭敌人,这对全局有利。1948年2月9日,他还致电党中央、毛泽东表示:为继续拖住大批敌人,更有力地配合粟裕的机动,大别山区的主力兵团不宜抽得过早,“须留在大别山再打一个月圈子”。
胸怀全局,勇挑重担可以说是邓小平一贯思想和精神。鲁西南战役结束不久,刘、邓不顾未及休整,敌情严重等巨大困难,为解决陕北、山东之危,服从全局,毅然提前出动“以应全局之需”;为减少兄弟部队损失,建议党中央不要派增援部队或运送物资前来;淮海战役中邓小平说:只要消灭了南线敌军主力,中原就是打光了,全国各路解放军还是可以取得全国胜利,这代价是值得的;渡江战役后,党中央曾考虑让刘、邓驻守南京、上海等富庶地区,而刘、邓又主动承担了进军大西南的重任;成都战役结束后,刘、邓又严令所部不准进城,而让兄弟部队驻守成都。邓小平曾经称赞刘伯承:“考虑问题从党的全局出发,事事顾全大局,服从大局”,“总是主动挑起最艰巨、最危险的任务,兢兢业业,排除万难去圆满完成”,“堪称坚决执行党的各项决议和中央战略方针的模范”。实际上邓小平也正是这样的模范。
留在大别山指挥其他几个纵队(2)
在坚持大别山斗争最困难的时候,警卫员看邓小平特别瘦,就想法找到两个鸡蛋,冲了一缸子鸡蛋茶给他喝。邓小平只喝了一半,另一半一定让警卫员喝下去。还有一次,他发现警卫员鞋前头露出脚趾头,就心疼地让警卫员把自己的那双旧皮鞋穿上。吃饭困难,烟也没有保证。以往他想抽烟时,总问警卫员“咱的小饭锅还有没有?”一听说没问题,他就很高兴,而如今,数万名官兵吃粮困难的压力是很大的,平时言语不多的邓小平更加沉默寡言。没有烟抽,他就一个劲地摆牌。经过反复考虑,他命令部队打粮食。正因为有了这个决心和行动,部队才渡过难关。解放以后,邓小平还专门组织人到大别山区中调查,对当时供给部队粮食的群众给予赔偿。
1948年的元旦,邓小平是在金寨县漆店区楼房村度过的。他这次到漆店区楼房村,主要是检查各项政策的落实情况,克服出现的“急性病”,如工商政策的落实情况。前一天上午,他了解了贫雇农情况,强调必须建立贫农团,有了这个核心,才能充分发挥贫雇农组织的作用,把根子扎牢,经得起斗争考验。对当地干部汇报“有些中农多余的耕牛可不可以分”的问题,邓小平听得很认真,但未马上回答。李先念表示不能分,并说:“这个问题,只要向贫雇农讲清政策,是很好解决的。”邓小平表示同意这个意见。然后又仔细地询问当地有没有工商业,指示在地方工作的干部,要把工商业发展起来。夜晚,邓小平等又听取各县县委书记的汇报,并和他们一起收听新华社广播的主要新闻——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据这次见过邓小平、李先念、李达的同志回忆:几位首长“个个穿的都是很单薄的灰土布棉衣,面容清瘦”。但是,他们并没有接受地方同志临时凑起来送给他们的过年东西。第二天,他们在给部队首长下达的命令中规定:“要有计划地协同地方工作。”
1948年的春节,邓小平是在大别山北麓一个小山坳度过的。在这里,他给大家留下了不要“竭泽而渔”的难忘“小事”。一位老同志回忆:为了过春节,同志们出去捉鱼,大家放掉了池塘里的水,一下子就弄到了几百斤鱼。正当大家兴高采烈欢庆时,邓小平从山坡小路走了过来。见此情景,先是对大家在非常艰苦条件下仍保持饱满、乐观的情绪予以鼓励,然后严肃地说:池塘水是群众备旱用的,你们采取了“竭泽而渔”的做法,贪图了眼前利益,损害了群众利益。经他这一指点,大家后悔不及。水已流失,不能复收,大家就向群众道歉,并赔偿了损失。为此,邓小平当即亲自起草了一个通知,下发给前指所属各部队,号召全体指战员处处留心照顾群众的利益,决不能竭泽而渔。
在大别山区坚持斗争期间。邓小平几次给党中央、毛泽东写报告,汇报大别山区军事、经济、土改、政策等方面情况。对此,毛泽东极为重视并作批语转发:“小平所述大别山经验极为宝贵,望各地各军采纳应用”。“报告非常之好”,“立转各地仿办”,同时电告邓小平:对所能联系的同志,“将你所提的那些策略观点、政策观点普遍通知他们。只要有机会就不失时机地指导他们,并要他们向你处反映结果。”
与南下跃进大别山的紧张气氛相比,邓小平等人北上转出大别山区,却显得从容、轻松。根据中央军委指示,2月9日,邓小平提出拟将前指“相机移与野后会合,部署作战”。12日,邓小平签发关于主力转出大别山后与华野、陈谢协同作战意见的电报。22日,他又以中原局名义发出《关于开展大别山游击战争的指示》,在此前后,他又在潢川县双构造村东南的环山主持召开会议,并作全国形势和主力北出后军区部队继续坚持大别山根据地斗争的报告。随后,他们经该县高店、春河集,跨越潢(川)固(始)公路北渡淮河,于24日同刘伯承所率的野后在安徽省临泉韦寨胜利会合。一些老同志回忆当时的邓小平:“衣着黄旧,又黑又瘦,惟两只眼睛仍炯炯有神。”有的老同志在日记中写:会合后,“白天、黑夜,旧友新朋喜相逢,各叙情长忆东风。前后(指)都遇到许多险境。可是并无增减人员,照样干。”
留在大别山指挥其他几个纵队(3)
对挺进和坚持大别山的这场斗争,邓小平印象相当深刻。他生前多次提起这半年多的军旅生活。不过,对这一中外军事史上著名的壮举,他只是平静地说:“战略反攻,二野挑的是重担,还是那句话,叫做合格。”笔者等曾于1996年10月下旬到过大别山,从北麓到南麓,从东至西,从商城县五里畈邓小平两次住过的房屋,到“王大湾会议”旧址等等,实地走过以后,对书本上介绍的49年前发生在那里的事情印象更深,感慨更多!
“转出大别山,以后到了豫西,成立扩大的中原局和中原军区。”这是邓小平讲坚持大别山革命斗争前后情况。对淮海战役他这样讲:“淮海战役前,打了一些小仗,取得了胜利,我们没有丧失机会,该打的都打了。”“迎接淮海战役的时候,总的形势很好。”“中原三足鼎立”。
1948年2月,邓小平率部北出大别山与刘伯承会合后,直至1948年11月那场震惊中外的淮海决战以前,这9个多月刘、邓在自己的回忆中很少谈到,似乎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仗。所以,很多史书、电视片中均没有或未详细地讲这段史实。实际上,这段时间是刘邓大军的休整时期,地点是在豫西,其中在伏牛山以东的宝丰县,刘、邓就住了将近7个月。
4月10日,刘、邓率部越过平流线挺进豫西,与陈粟、陈谢部会合。5月26日,中原局、中原军区等各领导机关分别进入驻地。刘、邓率领的在原军区司令部驻地北张庄村,位于洛阳至叶县公路以东2公里,村子不大,南依土岭,北邻小溪,环境很幽静。在这个村的东北角,有一所较大的地主家宅院,宅院有东、南、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