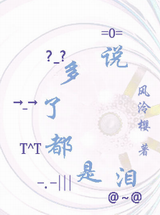说出来已是泪流满面-第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山村震惊了,村里的乡亲都很为我们一家高兴。我虽然没有上大学,但通过自考,也取得了文凭,文章经常发表在报刊上,爸爸经常高兴得合不拢嘴,对乡亲们说:“我就知道这些孩子争气。”
我们都有了自己的生活,儿女就像是起飞的风筝,他们开始有自己的天空,父母希望他们越飞越高,但那份思念和牵挂是永远的线。在每次的电话里,爸爸都会叮嘱我们注意身体,对于努力学习或工作反而说的少一些,他对我们是有信心的。
每次回家,只要爸爸在家,他都会笑呵呵地迎出来,早早给我们准备了我们喜欢吃的花生、地瓜,哪怕是一把酸枣。不论何时,爸爸总是笑眯眯的,有使不完的劲。可是爸爸真的老了,劳累的生活让爸爸的身材变得不再挺拔,岁月的纹路悄悄爬上他的眼角,头发也开始花白了,但他开心地笑着,从不抱怨生活的苦。
爸爸最大愿望就是等他退了休,他就和母亲在老家,种几亩花生,打最纯正的花生油给我们姐弟几个吃。他还在工作之余栽了一片板栗树,他说这是不卖的,是给孩子们吃的。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我要挣好多好多钱,让爸爸和娘过上好日子,可是爸爸终究没等到那一天。
去年的三月,接到母亲的电话,说爸爸最近不舒服。赶紧和弟弟请假收拾回家,爸爸还在地里忙着种花生,他说:“没事,就是有点恶心、没劲,估计没大事,等种完这些花生再去看吧。”
在我和弟弟坚决地反对中,爸爸几乎让我们押着去了医院。一路上还说:“这片花生再不种就种不上了。”
看着爸爸暗黄的脸,我心中有种不祥的感觉。太多的苦难把握吓怕了,总把事情往最坏的方向想,还自己安慰自己:不会有事的,命运不会这么残酷的。
谁知,命运就是这么残酷。在一系列的检查过后,医生严肃地告诉我们:肝硬化中晚期,门静脉高压,重度腹水。一瞬间,我有晕眩的感觉,但我告诉自己:不能慌,要镇定。在争取了熟人医生的意见后,我们当天就赶往临沂市医院。我知道,肝硬化是不可逆的,但不一定危及生命,治病,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我告诉爸爸,县医院的设备不行,我们需要进一步的检查。在临沂经过了一段病毒控制和营养补充的治疗后,最终确定了由中医治疗为主,西医治疗为副的治疗方案。此后的长达一年多的时间,爸爸每天都要喝那苦苦的中药,看着他皱着眉头喝药的样子,我真想替他喝下去。
母亲精心地照顾着爸爸,就像照顾一个婴儿,因为爸爸的病对食物的新鲜要求特别严,娘就自己种菜,每天给爸爸做最新鲜的菜,因为爸爸对盐的摄入量很严格,娘就连自己吃的菜也不怎么放盐。真的像《激情燃烧的岁月》的情节一样,在漫长的岁月中,爸爸用自己的一言一行,一点一点的感动着母亲,让母亲从心里接受了他。
爸爸的病控制的很好,一度腹水全部消失。他是个闲不住的人,在家也不闲着,干些力所能及的活。我经常在网上查一些好的医院和医生,打算如果现在的效果不好,作为备选。但对于这个病,我也有了更多的认识:这是一个并发症很多的病,因为肝脏的解毒功能不能正常工作,毒素在体内越积越多,但又没有很好的治疗捷径。
每次看到这些,都会使我泪流满面,我祈求疾病不要带走我的爸爸,哪怕用我的寿命缩短来换。我们尽可能的陪着爸爸,给他讲生活中的趣事,就像小时候一样,爸爸开心的大笑,那脸上的皱纹,就像九月的菊花一般灿烂展开。
可是没过多长时间,疾病再一次袭击了爸爸孱弱的身体。先是腹痛,再是呕吐,接到电话立即接到济南。省立医院,当检验医生把检查结果交给我时,我心里就一直往下沉:左肝增大,右肝缩小;胆囊占位性突变,发现2个边缘不清瘤体。医生说:没有手术的必要了。
爸爸一直想吃的猪蹄,因为我担心他吃了油腻的东西对肝脏不好,一直不让他吃。去买了上好的猪蹄,炖得烂烂的,看着爸爸吃得香香的,转过头,泪水偷偷地滑落。
疾病的威力显现出来。有时候会很痛,腹痛起来,大滴大滴的汗从爸爸的额头冒出来,爸爸是个隐忍的人,每当这时,他总是咬着牙,一声不吭。有时候就是吐,吃什么吐什么,一口水也会吐出来。看着爸爸日渐消瘦和痛苦的表情,那是怎样的心情,你一点办法也没有,就那样手足无措。只有握着爸爸的手,希望可以给他力量,直到这时,爸爸还会惦记:“别,别,别传染了你。”我告诉他:“我打过疫苗,不会传染。”我敬爱的、可爱的爸爸,上天告诉我怎样可以帮助您?
命运再一次让我们绝望。2006年6月18日,被疾病折磨得瘦弱不堪的爸爸陷入了昏迷,别人喊,他都不会回应,唯有我们姐弟几个喊他,他会努力的睁眼。我不相信我爸爸会离我们而去,他最爱的孩子除了我,都还没成家,他还有太多的牵挂。我相信他一定会醒过来。
静悄悄的夜,白炽灯光下有小小的飞蛾,爸爸静静地躺着,仿佛睡梦中,我静静的陪在他身边,长久的盯着爸爸。脑海中一幕幕,就像放电影一样的往事,爸爸憨厚的笑容、晚归的等候、声声的叮咛宛如昨日。蓦然发现,18年来,爸爸从没有打过我们、骂过我们,从来没有。
“爸爸、爸爸”,一声声的呼唤,我相信爸爸听得见。整整两天两夜,我们用尽了方法也没能让他再醒过来,我们的呼唤终究不能挽留爸爸离去的脚步,爸爸还是走了,眼角,是不舍的泪滴。
泪水早已不能代表我们的伤痛。我平凡而又伟大的爸爸,他用无怨无悔的行动,教会了我们爱和付出。我不识字的爸爸,用他踏实的双脚,给我们书写了真正的人生教程。
爸爸走的那天,送葬的队伍很长很长。
我们都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尤其是母亲,整个人的精神都跨了。安慰,是彼此取暖的方式,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感觉爸爸没有离开我们,在我们回家的时候,他还会展开笑容从门里迎出来。但是再也不会了,爸爸只活在我们的心间。
千言万语,唯有祝福我的爸爸,天堂里没有病痛。
高克芳,30岁,作家,现居济南。出版有《七年之痒》、《亲人爱人》等长篇小说。
欧阳娟 给初为人母的友人
欧阳娟
在这样的乐声中扒在桌上给你写信,分开四年以来的第一封信。昨天你打电话跟我说,你生了一个小男孩,我的心突然充满了柔情和疼痛——那个和我肩并肩走在一起的女孩已为人母了。
你是唱着这首歌走到我生活中来的,那天我埋头坐在教室里看书,初冬的第一次冷空气袭卷了整个城市,我一抬头就遇上你的眼睛,坦率又调皮的神情。不知为什么,整个教室突然就温暖如春,我在你的眼睛里找到自己的着落。
天是蓝的,友情是绿的,十七八岁的生命就像新生的麦子一样脆弱清爽,在这样的年龄里,我们用自己的生命浸润着对方的生命,在清清脆脆的年龄里互相扶持着,见证了对方的成长。
很多女友之间的形影不离只是一种形式,但我和你不同,我们都是喜欢独处的人,以前没有什么固定的朋友,现在天天同进同出,只是因为感觉很投合。你总是走在我的左侧,年轻的笑脸灿若春花,你总是赞叹着树叶和草地:“真绿呀,真美呀,就像爱情。”你扑向每一棵新生着叶子的树,就像扑向爱人的怀抱。
记得待在校园的最后一晚,坐在没有星星的夜里,两个人都长久地沉默着,夜色一点一点的爬上来,又轻手轻脚的离去,晨露湿了绿色的裙子。没有太多的离情别绪,只是一种惘然的惆怅,我们以为相见的机会还多呢,谁知,一别四年少有音讯。是我们太不了解生活的翻云覆雨了。
从校园走向社会,生活像潮水一样汹涌着推到我们的面前,需要面对的东西太多太乱,我一时间失去了语言,找不到合适的词语来向你诉说近况,每次面对着信纸和电话,我都觉得自己像一个得了失语症的人,思绪纷乱无法诉诸于语言。
在这四年里,你在用着怎么样的姿势生活着,为了你向往的,那如绿地一般葱郁的爱情付出过怎么样的代价,你追到了什么吗,又失去了什么呢,心痛的时候有没有试着点起一支烟或是喝上一杯酒?我知道你是好女孩,不可能放纵地变成烟鬼或是酒鬼,最多就是在有限的范围内对生活做出这么一点微不足道的反抗。
隔着四年的光阴,我还是一下就听出你声音中的落莫。你说:“不知应该用怎么样的语调和声音来跟你交谈现在,现在这种略带疲倦和苟且的生活。”这也是我的感受。青春都快过去了,经历过那么长久的寻找和飘泊,年少时的梦想永不重现,生活还是一团理不清的麻。
“谁这么有本事,让你爱他到可以忍受生育的疼痛。”我问。你说:“不是谁。是自己吧。我想创造一个生命,天天浇水施肥看他一点一滴的成长……生活会给我一个果实的,不管是甜是苦,我甘心。”作为创造这个生命的合作者,孩子的父亲突然退得好远好远。是啊,我们结婚,是因为我们需要一个家,我们生孩子,是因为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母爱想要给出去……不能把责任全推到丈夫的身上。
你变得智慧了,不再抱怨生活的不公,你说:“其实不是生活给得太少,而是以前要求得太多。”经过漫长的经验,终于肯承认自己是和别人一样的普通人。下雨的时候我们不会比别人淋得多,掉陷饼的时候我们也不会比别人捡得多,意气风发的少年时代过完了,没人是公主也没有王子架着马车出现在午夜。结婚、生子、老去……我们过着每个普通女人的生活,从中收获一些小小的乐趣。
信已近尾声,我舍不得搁笔却已无话可说了,人真正活得通透了就会觉得所有的表达都是多余。如果说四年前的那一场别离让我误以为还能相见的话,那么今天,随着一个母亲的诞生我真正体会到了别离的滋味。那个我所熟识的青春易躁的身体被抛下了,你带着一个平淡但注满母爱的身体重新上路。
如何做一个母亲,一条未知的路摆在你的面前。青春的飘泊结束了,你又毫不犹豫的开始了另一种形式的飘泊。人是永远靠不到岸的,我们只有在不断地飘泊中力求做得更好。
我对你是放心的,充满了母爱的身体无所畏惧。在我搁下笔的这一刻,看见同样的命运向我走近来。
欧阳娟,27岁,作家,公务员,现居江西樟树。出版有《交易》、《手腕》等长篇小说。
费新乾 水 域
费新乾
一
母亲从山里嫁到湖边,带着她亲手刺绣的嫁装与青春。这个小巧俊俏的新娘,被装在雕有八仙的轿子里,推过结冰的湖面。她该看见精白精白的雪,纷扬于她的前程。锁呐热腾腾地奏响由家权所导的婚姻。她自负的父亲告诉她,那是个可以打包票的庄稼人,有牛有地,双亲健在。母亲的脑海不由浮起一个后生,结着她前世缘今世份,像蚂蚁样扛着几倍于自重淹没全身的水草捆捆。一根金色麦状饰物别在头上,期待出离羞涩。母亲将自己移植于水边。“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从此,无论风霜雪雨,她都将坚守自己的位置,自己的男人。
雪纯洁,高贵,飘忽,把握不住。一旦掌在手心便不成为雪。男人敦朴然而骄傲,对爱坚贞不二但又惯于流浪。方额厚唇,眼里却蕴着令人不安的火,能燃烧自己点燃别人。从根子上他就缺乏庄稼人的本色。造化将他安在这里,于是他像不良作物一样向外畸形生长。他天赋惊人,甚至不得不借沉默和劳作遮掩自己的锋芒毕露,借流浪来突围。但因为他的女人,一次又一次回到从前出发的地方。男人归来,用他精良的种子,给惯于守望和劳作的妇人培出她麦田的作物——孩子,一茬接一茬地生长起来,生长着吃饭的嘴巴与同样惯于劳作的手。女人来不及怪罪,肩上便负担起了全部。在集体农社里,一天插两亩田挣足工分,傍晚出外收两担粪,给挂着名额而忙于照顾孩子的奶奶添上工分,晚上缝缝补补,洗洗浆浆。偶尔,她会想起男人,想着他也许就在明日归程上。她赤足淌进岁月的河流,挣扎着植根于水域,渴望男人的肩膀荷叶般护住她将近尾声的绽放。
父亲送过礼物给母亲,纯银打造,由银片勾出纷繁复杂的图案,关于图腾崇拜,神圣宗教,人间爱情。这样一件抽象化包融性,神圣秘密地分享母亲悲欢的礼物,却用来干最实用的事儿:挖耳、修眉、饰腰、包胸。它永不褪色地记载下母亲生活的轨迹。
母亲决定抓紧父亲,是在爷爷去世后。爷爷在队上当会计记帐,兼耍笔杆写感谢信及生产挑战应战书。人高马大,一表人才的爷爷曾是特务连精干,跟随过彭德怀元帅,在大部队撤离后,留在故乡待命。然后国民党打过来大肆搜捕,明令交枪者不杀。爷爷交枪投诚,结束传奇成为一介顺民。但阴影已植下,一生无法摆脱。每当夜深人静,他都不停地擦一杆木枪,溜光溜光却涂成夜一般的黑。爷爷坐到黑夜里啜泣抽搐不能自抑。他死得突然却必然。属于几个点灯夜晚的某个深夜,他狂吐鲜血,轰然倒地。母亲无法平静面对,梦里第一次出现血,灿若桃花,怒放在父亲的胸口,而父亲一伸手,竟将带血的心交给了她。然后母亲醒了,哭肿了眼。
母亲为了男人和孩子,决心做一座红砖屋,一个金银不换的窝。她守望的过程太长,日升而起,日落而息。太阳从地球下面移到地球上面,连爷爷坐南朝北的坟都浸到湖底了。她手搭凉棚,望穿秋水,依然不见自己的男人。等待将日子的影像打磨得尖历深刻。
八十年初的一个夏日傍晚,父亲驾着一辆东风汽车出现在村口,几乎所有的村人都出现在那个血色黄昏下,拿眼一遍遍一琢磨这个铁玩意与放逐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