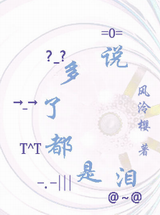说出来已是泪流满面-第4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梯子,你就顺着怕到了桌子上,最让我们害怕的是桌子下面是姥姥用来腌咸菜的大缸,开着口,你差一点就掉进大缸里。那次把妈妈和姥姥吓得半死。宝贝,我不敢想象,在漆黑的夜里,你醒来,不哭,自己在黑夜里爬着,你是多么的勇敢啊。
别人问你爱爸爸还是爱妈妈,从来你都是回答:爱爸爸也爱妈妈。再问,还是爱爸爸也爱妈妈。我的意志坚定的宝贝。
为了工作,一岁半,你就被妈妈送进幼儿园,你从来都不哭,快乐地和妈妈再见。下午妈妈去接,你还不乐意回家呢。你是幼儿园老师最喜欢的宝宝,从来都是。
过年,妈妈带你回姥姥家,你和那些鸡呀,羊啊,狗啊,成了好朋友,每次它们都跟在你的身后,你很爱它们,把姥姥给你的好吃的都给它们吃了,所以,它们像簇拥公主一样簇拥着你,那时你才一岁多。在回济南的路上,有一只大公鸡站在高高的墙上,你立即紧张的大喊:“鸡,摔着你。”你紧张得通红的小脸逗得大家哈哈大笑。我的满满爱心的宝贝。
二岁,楼下有人结婚,妈妈在阳台上抱着你看,你看到洁白的婚纱,漫天的礼花,对我说:“妈妈,我也要结婚。”眼里是无尽的向往。我的宝贝,这个妈妈现在不能答应你,等你结婚的时候,妈妈一定给你买世界上最美丽的婚纱。
三岁,你会抱着妈妈的脖子和妈妈撒娇,害得你爸爸嫉妒得眼红。你会在妈妈的耳边悄悄的说:“妈妈,我好爱你。”嫩嫩的声音,呵出的气弄得我的耳朵痒痒的,我的宝贝,妈妈幸福得想晕过去。
四岁,你开始变得狡猾了,你会很认真地对妈妈说:“妈妈,等我长大了,我会送给你一样好东西。”妈妈纳闷,你会送给妈妈什么好东西呢?你很神秘地说:“妈妈,等我长大了,我会送给你不老的药吃。”哦,我的宝贝,你的小小的脑袋里究竟装了多少东西?
五岁,你已经可以一本正经地和爸爸妈妈一起讨论问题了,也可以帮妈妈做力所能及的家务,你自己洗的袜子干净而香喷喷地,因为你喜欢用香皂啊。
欣欣,你就要六岁了,你的身高一米二二,体重五十斤,在同龄中你是一个又高又壮的孩子,我希望你不要像个小老虎一样爱吃肉了,妈妈喜欢乖巧的窈窕淑女啊,明年你就要上学了,我知道你一定是个热爱学习的好孩子,让我们共同为以后的学习而准备,你已经是个大孩子了,有自己独立的思想,爱思考,爱看书,爱画画,爱打破砂锅问到底,好吧,我的宝贝,从此我们就是朋友,我们一起来学习,一起来成长,好不好?
牵着你的手,在人生的道路上,也许还会有风雨,但是有你,我会知足。
艾美 她把这快乐倾倒一点出来
艾 美
毋宁说用笑颜冲上一杯青绿飘香的茶
三月的风是多情的,它来,含着笑,吹动少女晶莹的心,折一个或无数纸风车放在格子窗。那样的窗格子,无疑于风化的石头,泛着斑驳的色泽,仿佛岁月对风的言说。
风来的时候,扯起风车的叶子呼拉拉地转动,发出啪啦啪啦的声音,像堕跌的蝴蝶的滑落声,丝丝扣入空气的骨骼。少女的视线越过风车,嘴角牵起淡淡的微笑,如同绚丽的阳光。
这时候的山泉清澈而甘甜,用它、毋宁说用笑颜冲上一杯青绿飘香的茶,这是再好不过的了,把个清甜的春装到肚子里去。
从小溪里盛上一小壶清澈的凉水,用柴火烧开,缓缓地冲到可爱的透明杯子里去,无需着急。透过杯子看山泉滋润茶叶,像刚睡醒的少女慢慢舒展美妙的身姿。山泉青绿起来,悠香四溢。
这样的清晨,阳光虽然算不上好,但薄薄的,也显得清丽可爱,挂在树梢,千丝万缕的洒泻在大地上。
她和他踩着这极浅极淡的阳光……空气是早晨独有的清新,呼吸,身体每个细胞被浸渍,心爽朗明净。
北方的早晨很少见雾。风倒是常来光顾,所幸的是,今晨的风很温柔,顶多风情地吹着你的发丝,轻抚着你的脸蛋。他忽然停下步子来,定定地站着,轻轻闭上眼睑,张开双臂。他的思绪,她想用柔情的吻抓住。她嘟嘟小嘴,对着他的耳朵说:“你敢看那太阳么,不眨眼地看着它,会有许多小碎片!”他牵着嘴,露出一个美美的笑,她的心弦被这美美的笑轻轻地拨了一下,“聪明的人才会这样看,我就不会。”他说。他夸她,她觉得幸福包围着她。
在他身边,他给的宠爱无处不在,即使在日子最紧巴巴的时候,他都不会忘了给她买果冻或她爱吃的零食。今天早晨就是这样,他们到食堂吃饭,时间尚早,食堂里只有稀稀拉拉几个人。他端来面条后说着“你先吃,我出去一会儿”语音还在人就不见了踪影。她看着面条冒出的丝丝热气,猜想着他的去向,面条只剩三丝热气的时候,他拎着一大口袋东西跑回来了,五颜六色的果冻在她眼前欢跳着……
春的新绿浅浅地浮在空气中
轻轻推开小窗,一股清凉、湿润的风迎面扑来,漫溢在这略显沉闷的小屋里,流响的世界也扑了进来——鸟鸣、轻语、小孩嬉笑、车喧声。
望去,春的新绿浅浅地浮在空气中,让人担心一阵风就把这看来不合实际的绿吹跑了,又使人担心会把行人的衣服染了个透。说它浮在空气中,是它与树干看来像是脱开的,那浅绿只是罩在树干的周围。这与南方的新绿不一样,南方的新绿总是实实的和树枝一片,色彩丰富鲜艳,浅绿、深绿、嫩红、鹅黄浓浓的一大片一大片,非常养眼。而北方通常只有柳树最先感到春的到来,其它树还是灰秃秃的枝干,仿佛还在冬的沉睡中,还没感受到春的到来,这大概是使它的新绿看来很单薄的原因。还有那莫名的花,没有叶子,把金灿灿的黄一簇簇洒泻在路的两旁。而南方的花则开得更新盛。这里的春像工笔画是慢悠悠地罩上去的,南方像浓墨重彩画。
把整个日子晃得响亮,到处都有阳光的艳影
新筛的阳光真的很好,砸到地上,她分明听到流泉洒落琴键,澄澈而斑驳,那份只有她与他才用心听到的乐音把整个日子晃得响亮,到处都有阳光的艳影。
她轻轻扣着他的手指,有一些液体化作水汽,在他与她之间交融。
她扣着他的影子,用她的。
他们流水一样潺湲倾泻着脚步。
脚下是他的校园,或自南向北,或由东而西。或者,就扯一条曲曲弯弯的折线。
风还冷,因为揉进他的体温,也有她的,渐渐有了暖意。
风因此称得上和风。和风吹拂着他略有些长的头发,露出棱角清明的脸。
她看得到他的笑,她尝到了,甜丝丝的,像他的亲吻。
此刻,他没有吻他,她是从他轻微上扬的嘴角读出他诡谲的心思的。
她拍打了他一下,声音清脆,一只鸽子飞过,要么是喜鹊,在空气里划出一道鸣叫,以及翅膀滑翔的轨迹。
你坏,她说,脸藏进他的怀抱。
他疏朗的大步,她的步子细碎而频繁,她是峭拔的高音,他则是山谷低回的厚而重的中低音。脚下的声音因而清脆而复沓,是一阕天籁——其实是天籁不及的她与他合奏的歌子。
天天天蓝,今天的天尤其蓝,是纯净飘逸的蓝,刚从天池里捞起来似的,水灵水灵的,他说:“白云,蓝天,宝宝,好心情。”她被他抱满怀,心空晴好,天缀大片的蓝,并不见白云的影子,谁知道飘哪儿去了,许是幽会远方的情人去了吧,她嘟噜着嘴,在他耳边申说。
他看了她一眼,一直看到她潺潺流转的心里去。爱死你了,他说。她忍不住在他脸上印了一朵火红的吻。
阳光打了个喷嚏,那蜜真的顺着他的柔情注目注到她的舌尖上
阳光打了个喷嚏,震得满地生辉的碎片闪耀不已。许多叫单车的工具被一么多人驾驶着,穿梭在他们身旁,留下滞留在空气中还没来得及传送的轻语浅笑。铃声听来像行走的绸缎上摔打出的休止符,在这个还算静谧的校园早晨。
道旁不知名的树上结满了毛茸茸可爱的果子,看上去像桂圆。他却笑她嘴馋,爱怜地揉揉她的鼻子,她的心里甜得能流出蜜来。吐吐舌头,那蜜真的顺着他的柔情注目注到她的舌尖上。
校园工人们在忙碌着种一些被圈上很多草绳的树桩。问他可是旧相好,他说,那树,我可不认识。那它认识你吗?她复问,重得掮不起的幸福吊在他的胳膊上。我在这儿的时候,它的尊臀还没来得及挪到这儿。他努努嘴。
他们的视线总比常人抻得格外绵长,不须着力,总能触碰到常人无力触碰的格致。
她想,如果上帝长着人形,他的胳肢窝在她与他的手指下一定来得尤其敏感。只消她与他层出不穷的对话,上帝保准眼里常年汪着泪水。只是,那份欢乐上帝有福消受么?
阳光依旧和煦,他们的影子拉得更长了。她用双脚追逐着他的黑影子,他也不躲闪,任她的脚细细密密地在他的影子上撒娇、跺脚,他也许是懒得搭理他的幼稚,又或许娇惯她……
她的眼里盛满了要流溢出来的快乐,她把这快乐倾倒一点出来,涂抹在他的胡茬上,用脚丫按摩他的额头和与她同样红润的唇,跺脚的响声吓得脚底下的地皮簌簌瑟瑟……
她已柔柔地把他注入自己的生命,连在梦境里也舍不得分离片刻。
远远近近的草坪上,有人拿着耙在为草们挠痒,她真担心大地忽然抖一下……
入夜,晕黄的灯光把树的肢体投影在光滑的水泥地走道上,错落有致,深深浅浅,粗粗细细都刚好合适,很有水墨情趣。
若行走,沿着树影生长的方向,如同他拥抱她的方向。
偶尔,她也会在树影的分丫上跳着走,像在她与他小小的家里,她像小棋子一样调皮地在他的快乐上跳舞……
这晚的夜静着哪……
艾美,27岁,作家,策划人,四川宜宾人,现居北京。出版有《美妙人生》、“少年天才”系列图书。操作的畅销书有《最青春小说》、《品婉约词》等。
唇是一条双轨,一直走啊
艾 美
支起的窗棂,霎动的长睫毛,火红的柿子挂满树
遥遥的四川,遥遥的记忆,温暖地在雪夜融入我的思绪。那些还未走远的脚步在此时此地敲响。
在此间我忽发奇想地忆起我的童年旧事,旧事里藏匿于时间之轮的人,她忽深忽浅地留在某人的记忆。那人就是我早已不知所踪的启蒙老师。
她年轻而漂亮,温驯而飘逸。她投身于我儿时的记忆,以天使的姿势,那时候,我是那么狠狠地喜欢她,那么狠狠地崇拜她。有时候,甚至狠不得长了她的骨头,彻头彻尾都像她。
她的睫毛那么长啊!一直从我的手掌中走过,直接投影在我雪白的书本上。她的头发甚至是卷曲的,像一夜春风吹过的湖水散开来,再也收不拢。我小小的年纪,年幼的心思猜透那上面的故事,卷曲的妩媚跳荡着怎样的心事。多么不简单,你看我虽然还不懂得男女之事,却知道揣摩女人发间的秘密。后来,我和飞说起,他那么早慧而聪明透顶。
我记得最清晰的她,穿荷叶边的衬衫,像一朵一朵的蝴蝶花,沿着领子一路漫无边际的开过去,明亮而清冽。她的裤管上细下宽,上面恰好勾勒出她青春的线条,下面像漫山遍野盛开的野百合。
那时候,她最多像个孩子,有着时间一样的光华,潮水般的温暖。我总是远远地看着她,躲在自己的座位上,静静地,毫无声息的,她的手上沾满了雪白的粉笔灰,就连衣服上、眉毛和嘴唇上都有,就是这些微不足道的细节,足以打动我年幼的心思。
第一次上课的时候,她笑眯眯地给我们讲一篇课文,课文说找春天,至今我都还记得那远去的字字句句,‘我们来到田野里,我们来到山岗上,我们找到了春天’。我身后一个瘦小的男孩突发奇想地问你,老师,火车是什么样的啊?我当时就扭过头去说:“走的时候像车一样地走,停的时候像房子一样。”我在你的眼中发现了一刹那的惊异,你直接夸我少年早慧,让我欣喜若狂。
你姓黄,日落黄昏后的黄,又说“还”,后来我记忆力老是不好,推脱于责任,我把所学的都还给我的老师。
入学前夕,我开始拥有书包,拥有铅笔和书本。军绿色的书包,深红的大头铅笔。我对他们谨小慎微,赋予热情。我抱着它们做了多少梦啊!此去经年,我那些骄傲的幻想,甚至有些狂妄的,一并在来不及说出“黯淡”退色和凋零的时候,就挥手作别了渐行渐远的童年。
那年报名那天,母亲很早就把我和妹妹叫起来。我们梳一样的辫子,我们的头发一摸一样,包括长短和颜色,我们秉承同样的父母。很多人分不清我们俩到底谁是谁,他们瞎猜一通后,难得费心思,干脆把相差仅此一岁的妹妹叫姐姐。而且不止一次,我纠正他们,我不怕费口舌,在每一天的某个时刻,他们就会粗暴唐突地把妹妹当作姐姐,他们这样把姐妹混在一起,相互错位,一直到我们长出不同的容貌来。
妹妹出生那年闹计划生育,有了我,妹妹不在计划生育之类,气急败坏的乡镇干部接到通风报信后,连夜赶来,抬走了父母仅有的一头猪,事后,母亲无数次说那头猪长得膘肥肉满。风波尚未平息,干部们不辞辛劳连连驻足我们的小屋,顺手牵羊,把东西拿得###不离十。后来以一张一千元的发票平息了这场长达数月的闹剧。
第一天去上学,正值秋天季节。由于早的缘故,太阳躲在云彩里不肯出来,红彤彤的,完全不晒人。薄薄的白雾,一圈一圈地不知疲倦地依附在突出的山与山之间,葱茏的松树若隐若现。
庄稼地里该收割的庄稼都收进了粮仓,只乘了成堆的玉米杆子或是成片的还未砍下来的,庄稼地里并没有因为玉米大豆的老去而枯萎,大片大片的红薯叶铺满了山。
路边的青草上缀满了晶莹透明的露珠儿,好看极了,蛐蛐在草丛里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