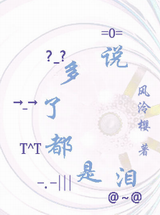说出来已是泪流满面-第3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喝不同的酒有不同的味道。不同环境下喝,更是有不同的感受。
白酒总是那幅清清白白,不染一尘的样子,喝白酒就要与自己要好的朋友,心淡坦然地大杯,大碗喝,喝出豪爽,说出真语,但是白酒酒精度浓高,岂是能轻易大杯大碗地喝的,真心朋友岂是能轻易交的。
我见过大碗喝酒的女人,那是在哈尔滨,表哥去那谈一笔裘衣领的业务,那时正值严冬,白雪纷飞,我与表哥的几个朋友在吃饭,我看到一个女子穿着厚厚的红裘衣站在雪地里,雪花飘在了她的头上,衣服上,红红白白的,她不躲雪,静静站在那像是在等人,目光清澈而坚定如误入人间的天使,我被这美妙情景惊呆了。
同桌的一位大婶看到我傻痴痴的样子就说,是不是看上人家姑娘了,我把她叫过来。
好啊,你得给我介绍介绍,我说。
这大婶喝了大大的一口白酒,也不吃菜,就真去叫她了。
那女孩进来,原来她们认识。奇怪的是这女孩也喝白酒,也大口大口的喝,她们说这的女人能喝酒不奇怪。
我问女孩,下雪了,为什么不进来。女孩吞下一口酒说,我在等人,说好的在那等。
你不会进来等吗?我问道。
怕不小心错过了,女孩也豪爽,说到就做到。
红酒像女孩绯红的脸,显然已经动了真心,喝红酒最好是在有月亮的夜晚,与情人一起喝,要有曲,还要有诗,最好不要“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这样的词太过感伤,要情意绵绵的,酒不醉人自醉。
红酒的酒性缓而慢,慢慢地,一点一滴地,侵袭,渗入。不容易发觉,也不好防备,它无声无息地让你灼热,让你耳红心跳,让你分不清是酒醉了还情醉了。
黄酒你看它只是浑浑浊浊的,看它象什么又不是什么,看它不像什么又似什么,长久的酝酿已经让它心性更加澄明。
在朋友的奶奶的96岁生日里,我看到了一个喝黄酒的女人,她笑靥满面,90多年的时光从她瘦小的身躯里流过,她有一种在经历世事沧桑的淡泊……
我也要了一碗黄酒,入口,苦涩又麻舌。含着眼泪终于把一碗喝完,我想,它的心性并不是我这样的年轻的汉子所能悟透的。
而我喝酒很多时候都是在回忆,回忆曾经的浪漫,我记得她喝酒时的样子,她喝下酒后的样子,她在微醉中依偎在我身旁行走的样子。或穿越,我仿佛穿越时光的隧道而到了梦寐之境。
有的人不再喝酒了。是已经麻木了,不懂思想了,确切地说更彻底地面对现实了,他们小心打拼着,如爬行的虫子,在黑暗只摸索,小心地计算着荣辱得失,他们的喝酒不叫喝酒只是应酬这物欲的城市。
他还有闲暇听鸟声蝉啼吗?
有的人过着没有节制的生活,无法自控的生活,他们走不出自己,他们有思想,但是仍然走不出平凡。
如果喝酒是为了逃避,那么醒来会更加彻底地面对。
韦一,作家。出版有长篇小说《桃花夜》。
谢有顺 人为什么恐惧
谢有顺
现代心理学家发现,人与动物之间最大的差别在于,人对不存在的东西会产生恐惧。探查这个问题是非常有意义的,它比我们探查一部作品更能有效地触及心灵的秘密通道。照英国神学家詹姆士?里德的说法,“许多恐惧都是来自我们对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不理解,来自这个世界对我们的控制”,“为了实现完满的人生,需要我们做的第一事情就是去获得控制恐惧的力量”。在现代社会,恐惧越来越有力地折磨着我们,到了每一个人都无法规避的地步,这让我想起19世纪英国诗人和散文家麦尔兹同他的朋友一道访问埃及时,有人问他,假如允许他问一个问题,并保证能得到回答,他将向斯芬克斯提出什么问题,麦尔兹说,他将提这样一个问题:“宇宙对人类是友好的吗?”这个悬而未解的问题,困扰着许多自恃聪明的人,让人倍感世界无常。正是由于人的有限与渺小,比之于宇宙与世界的深不可测,差距太大,才使人对许多无法理解的事物生出恐惧。比如,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都幼稚地认为“四”、“十三”这些数字会给他们带来不来不祥,可见,面对世界的无常,人是多么脆弱而无助。
还有许多具体的事物,也在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使人不得不恐惧。比如,苦难,或者说精神创伤,在我们的生活中是无处不在的,不说人类历史上那些血腥、黑暗的段落,就是现在,思想贫困,情感颓废,爱情正走向欲望,高贵的精神正在世俗化的生活中退席,暴力增加,无处不在的核威胁,等等,都已经把人类推向了危险的边缘。这个问题重重的世界,不是人类所能轻易承担的了。尼采所预言的“超人”并没有诞生,而现代人却承受着“超人”才能承受得起的生存重负,这就是他们为何恐惧和绝望的原因。精神问题也是如此。人从文艺复兴之后被确立为宇宙的中心,存在的终极,人便开始要为自己的生存负责,这就好比要把亚特拉斯肩上的世界扛在人的肩上一样,最终会被压垮。人要为自己所作的付出代价。一次又一次存在的挫折,把生存的严峻性摆到了每个人的面前。在弗洛伊德时代,人类遭遇的还只是性受挫,到现在,成了生存的受挫,显得更加严重了。悲剧也许正是这样开始的:人作为有限的存在,根本无力为自己承担一切。我现在回忆起那些古代圣徒跪在地上祷告的情形,他们可以将心中一切的烦恼、痛苦、不幸向那位至高者倾诉,伤心的眼泪可以向他而流,难以负荷的生存重担可以交托给他,是多么的幸福啊!
可是,20世纪的人类选择了自我承担的道路,这样,离弃了神圣的信仰,除了人的顾影自怜之外,还有谁来安慰我们呢?当我读着梵高写给他的恋人的书信时,我感到这个孤独的画家是那样地需要爱与慰藉;绘画大师毕加索,一生都用立体法则绘画,将人抽象成一些线条和方块,可是,他将他的妻子与情人却画得充满人性,这说明毕加索希望在这些情人的肖像中找到安慰;弗洛伊德在写给恋人的信中也说:“小公主,当你来到我身边时,请无理性地爱我吧!”这说明弗洛伊德也渴望在爱中得安慰,只是,他说出这样的话来,与他自己所坚持的理论差距是多么的大:弗洛伊德认为性是一切事情的最终目的,他在理论上并不相信有爱的存在。但只要你是一个人,里面就有一个原初的渴望真爱的本质,这个本质将咒诅弗洛伊德那种以性为中心的思想。当弗洛伊德说出“请无理性地爱我吧”这句话时,你无法想象他的内心经历着一种怎样的荒谬和寒冷。
梵高、毕加索、弗洛伊德的例子指明了一个共同的事实:人与自我分离了,即存在与本质的分离。就如卡夫卡所说的那样,我说的与我想的不一样,我想的又与我愿意想的不一样。这些分离的事实使梵高、毕加索、卡夫卡、弗洛伊德等人深深地陷于恐惧和绝望之中。他们无法使自己成为想要成为的那种人。更严重的是,每个人所生活的文化境遇仿佛都是一个巨大的茧,把自我囚禁在里面。这个茧导致人不单不能顺畅地与他人交流,甚至与自我的交流都疏离了。交流的不可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交流,而是人格与人格之间的交流)所带来的一个结果是:每个人的我都成了孤独的我。孤独,真正的孤独。我想起安东尼奥尼的电影《放大》,整部影片充满的是按照相机快门的声音,几乎没有什么对白,即使那几个模特儿非理性的表演场面,也没有任何交流的暗示,最后,在网球场上,一个戴着面具的人孤独地打着网球,没有对手,这时,镜头不断地拉远,画面中的人不断缩小,直到剩下一个空旷的球场。这部影片与安东尼奥尼的另一部影片《红色沙漠》一样,充分表达出了现代人的孤独、冷漠、毫无交流与慰藉的空洞景象。同一时期的电影大师费里尼、英格玛?伯格曼,几乎都在表达这一主题,以揭示人类普遍的精神困境。
人以这样的面目出现在艺术家的视野中,里面一定包含着艺术家对世界、对人自身的深深的恐惧。鲍斯威尔说:“没有比恐惧更让人苦恼的情绪了:恐惧使我们痛苦不堪,并使我们在自己眼中也可鄙到了极点。”蒙田则说:“恐惧甚至比死亡本身更可憎,也更难以忍受。”在这里,恐惧意味着尊严的丧失。当卡夫卡在《地洞》这部小说中写到那只小动物竖起耳朵紧张地谛听着地洞外的动静时,他已走到了孤独与恐惧的深渊;英玛?伯格曼在1962年拍完了著名影片《沉默》,并说他发现了一个重要事实:神已经不在,现在这个世界只有沉默。在这个事实面前,伯格曼非常恐惧。事后他对记者说,他是一边听着巴赫的音乐,一边写完《沉默》这个剧本的。我想,伯格曼是在用巴赫的音乐来抵挡他内心的恐惧。让我们再回想一下科波拉的著名影片《现代启示录》吧,“我”行走在仿佛永远走不完的河流上,越来越对将要面临的事实感到恐惧,当“我”见到那个隐藏在森林中拒绝作战的军官(马龙?白兰度饰)时,恐惧驱使“我”举刀向那个军官砍去,想以此来解除内心压力,这时,画面上只有军官在血泊中痛苦地翻滚,以及他低沉的、绝望的叫声:“恐惧!恐惧!”这里面,科波拉让我们看到战争把人性伤害到了什么程度。
恐惧,它比害怕更深刻。害怕是面对一个具体对象的,恐惧却与焦虑一样,可能是没有具体对象、无边无际的。肉体遭到攻击(如一只老虎朝你扑来)会使人害怕,精神的伤害却产生恐惧,最终带进绝望。害怕是现在的,恐惧则可以针对未来和不可知的事而发生。那么,恐惧是如何发生的呢?或者说,人为什么会恐惧?一只猪晚上要被杀了,中午它照样可以很快乐地进食,人却做不到这一点,原因在于人会为未来的事而忧虑。未来如果没有安全,没有因慰藉带来的幸福,没有人格与人格之间的交流,人就无法为自身的存在找到合适的位置。他一旦跨出存在的本位,任何的事物都可能给他带来威胁。没有了更大的保护者,自身又不可靠,慰藉从何而来呢?人把自己抬高到了宇宙的中心位置,却又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在这种严重的生存境遇面前,恐惧是在所难免的了。
在探查恐惧发生的原因以先,我首先要说到恐惧的基本形式是什么。恐惧有许多种面貌,但经历代哲学家的研究,归纳起来大概有以下几种形式:一、对不具人格的未知事物有所恐惧;二、对“不存在”感到恐惧;三、对死亡和消失的恐惧。也许我们还可以想出一些恐惧的其他形式,但以上的三种实际上包含了绝大多数的恐惧类型。恐惧的强度也有不一样,有的较弱,有的强烈到足以导致绝望的地步,有的则在这二者之间。许多现代人经历了这种可怕的黑暗,并由此发展出绝望的哲学,基尔凯戈尔就专门写过一部著作,叫《绝望论》。绝望是恐惧的极端形式,而恐惧又总以颤栗为心理特征的,他表明人承受了过于他们所能承受的东西,以致心里失去了安全感,失去了依靠。在存在的威胁面前,人是需要一个更大的保护者的。
人为什么会对不具人格的未知事物感到恐惧呢?原因在于,自从每个人的自我成了一个茧,把自己与他人之间封闭起来之后,人就无法再了解自身之外的存在,他漠视神圣的存在,也不再想象人存在中的完美性。事实上,人自身的存在是开放性的,他渴望与更高的存在联合在一起,以弥补自身的不足,所以,东方有“天人合一”的思想,西方有“神人相调”的启示。古代中国人强调“人”必须与“天”相统一、协调、一致、和睦,所谓“参天地,赞化育”,但中国思想中并没有哪一个神圣实在与“天”相对应,“天”显得非常空洞,最终就把“天人合一”理解成了“自然的人化”,结果是“人”,而不是“天”;西方思想中的“天”被指称为神,基督,赐生命的圣灵,“神人相调”是指三一神的神性与它所救赎的人性在时间里相遇,但不产生第三性,是神人二性,以“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为代表,其最终的合一是合一于“天”——“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如今,在这个渎神的物质主义时代,东西方似乎都不再崇尚“天”了,而是热烈地去追求属地的事物,人的存在彻底地向神圣存在关闭。这种存在的闭抑性使得人开始用人的立场来认识人自己。结果,现代人越认识自身的人性,越往自己的内心深处走,就越会发现人是一个空洞的存在,你根本无法认识自己,甚至越认识还越模糊,以致一切都处于晦暗之中。这个时候,人自然就会产生对不具人格的未知事物的恐惧。这也就是现代的艺术家们越想认识人,人在他们的作品中就越没有地位的原因。其实,古希腊的名言“认识你自己”的本来意思是“记住:你将死去”,可是,现代人普遍理解错了这句话。
很早以前读过美国的薛华博士写的一本书,里面举了一个例子,或许可以说明人为何会对未知事物感到恐惧。他说,小孩通常很害怕被单独留在黑暗而“不具人格”的房间里,人怎样安慰他都无济于事,但在有基督教传统的西方国家,父母会对孩子说:“不必怕,因为神也在这里。”这是个简单而奇妙的真理,因着他们相信神是真实存在的,同样有人格的人就不必再惧怕“不具人格的”东西了。许多的心理学家,都用这个办法,实用主义式地表现出相信“神存在”的模样,却能对患病者有某种程度的帮助。卡尔?荣格就经常告诉他的病患,在一切生活中要“好像”神是存在一样,就可以对付心理上的恐惧。在荣格去世的前八天,他在记者对他的最后一次访问中谈到他所认为的神是:“凡是从我外面切入我意志的东西,或是由我的集体潜意识中涌现的东西。”他的建议是,姑且把它称作“神”,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