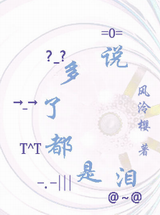说出来已是泪流满面-第1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父亲走时悄无声息。那是凌晨2点后,黎明欲出的时候。夜已随他的生命永逝了,黎明会出现在他生命的另一个渡口。
父亲走时我们无人赶上,姐姐在昨日的梦中是赶着要为他送行的,是父亲回身告诉姐姐:“别送。让我一个人静静的走,你们要放心,爸很好。”梦其实已预示结果,父亲是要一个人走的。
人世间是有沧桑的,父亲走了,了结了俗世的尘怨与无奈。
依稀可见他临走前,静静注视光盘中朵朵青莲与佛陀的超然神采,人将去时是会大悟的。尘世的烦恼在人走时,依然会留给尘世。与他们结伴的是一路清爽,一路清凉。
冬日的喜鹊是罕见的,可父亲灵车前飞来三只喜鹊,一路引领。它们一路歌声为父亲送行。
郭艳华,网名雨莲静荷,37岁,吉林镇赉人,现居黑龙江松花江农场,商人。
孔庆先 奶奶的天堂
孔庆先
奶奶生于1913年,卒于1982年,享年69岁。没来得及说一声告别的话就离我们而去,对于一向做事周全的奶奶来讲,总归是个遗憾。奶奶,奶奶,人群中再也寻不到她的身影,再也听不到她那洪钟般的说笑声。十多年来在我寂寞的成长中一遍遍回忆奶奶,面对生,甘于寂寞也罢,不甘于也罢,那种久违的苦痛却实实在在浸透了无奈的心。
1982年6月的天气很好,雨水很多,也没有听见特别响的惊雷滚过。傍晚奶奶给她的小孙子喂过饭去后院小河边刷鞋,就一头栽倒在小河边,这样糊里糊涂地睡着了。等叔婶从地里回来时她还睡在河边,脸上红扑扑的。
我放学回家时父亲和叔叔已经把睡在河边的奶奶背到大筐里并装上马车,我们一起坐着马车去了乡卫生院,那里的大夫说这样的病人他们治不了,叔叔赶着马车转头来到村头火车站。这是一个一天有两辆客车在此停留的小站,那天那个傍晚有一列拉煤的货车在那里待停,安静的小站上只有一部专门用来铁路调度用的电话专线在不停地摇着,喂喂喂的声音起起落落。我们被特别批准,上了那辆货车的最后一节车厢,驶向了天津辖区的一所医院。
爷爷在这个时候平静地摸着棋子跟人对弈,以为奶奶像往常一样头疼脑热,挥挥手吩咐报信人说给她喝点凉水,就没有动地方接着走下一步。爷爷的独断与专横,源自于他曾经是没落的孔府的七少爷。奶奶是他的二房,大奶奶早已去世。从十三岁嫁进孔府,奶奶心甘情愿地为爷爷做着一切,永远笑容满面听凭爷爷无端的呵斥。奶奶说,他是你男人,还能离得了他?离不了他就得听他的,这样的女人贤德,修得死后往天堂里升呢。爷爷说没柴了吧,奶奶扭着三寸金莲去野地里背。爷爷说你去上房晒玉米,奶奶打着晃眼不敢往下看也要爬上房。直到土改前夕,爷爷无心种田就把最后三十亩田卖了一笔大洋,成交后爷爷说地里还长着好多苇子买主不要,就让奶奶对着西北风一沟一沟点火,把个田野烧得焦黑一片,奶奶嘴里呵着白气,两颊泛红,不知疲倦,快活地奔跑着。爷爷边下棋边想,这个老婆子是多么的结实呀!而我亲爱的奶奶,正一步一步走向她崇尚已久的天堂。
守在奶奶的床边,如何也流不出眼泪,只当她像往常一样的睡眠,并有不断的鼾声传出。那一夜我被一种安宁笼罩着。亲人在病房里外进进出出眼睛红肿,而我却在认认真真地端详着奶奶,发现紧闭双眼的奶奶依然很好看,她的两颊红扑扑,光泽得很,看不出她有任何不祥。大约第二天的凌晨三、四点钟,一位年轻而且长着一对大眼睛的女医生告诉我,病人不行了,去找大人商量一下,是留在这里火化还是拉回家埋了。她的大眼睛里荡漾着一种深深的同情。
想着奶奶以往的慈祥,还有昨日高高嗓门的说笑,我不相信奶奶即将离我远去,离这个她无比热爱的世界远去,她那稍蹙的双眉仿佛在提醒我做错了什么事,但此时我再不用担心她会伸出手在我的屁股上拍一记……
在我上学的第一天,奶奶就帮我打了一架。奶奶双手叉腰指着欺负我的男生破口大骂,并找到他们家长评理。从那时起,奶奶便成了我生命中一面永恒的墙。可是奶奶每次帮我打完架回到家,却先在我屁股上来几下子,教训我说:看你下次再打架,要知道死了该下地狱!
奶奶总是在人多的时候骂得精彩,她不怕热闹,似乎在向世界展示着被爷爷压抑了的那种骄傲,在我和同学面前,奶奶威风极了,有奶奶呵护的日子,我神气而自尊。
此时的奶奶睡着了一样安详如旧。
天亮时叔叔红着眼睛赶来一辆马车,三十里土路,颠颠簸簸,载着奶奶和我,氧气仍然维持着奶奶最后一点生命。叔赶着马车,车子哐当当,哐当当,不快不慢,宛如几年前奶奶回娘家。那时奶奶抱着我一路上哼着歌儿: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吱吱叫奶奶……奶奶笑着说:你说小老鼠是谁呀?我赶紧接过话说:是奶奶大孙女。奶奶说真聪明,天堂仙女托生的。于是奶奶又哼起这支歌,也是她唯一会唱的歌,我就在她温暖宽大的怀里睡着了,做着仙女才做的梦。
马车在土路上扬起灰尘,路两边那时还很荒凉,猪猪草绿油油一片,六月开放的喇叭花扑满露水,远远望去有一些农人在锄地,他们有时拄着锄头朝马车这边张望,他们一定以为这辆马车拉着闺女回娘家的,于是奶奶的歌又一次从心底荡起……小老鼠上窗台,偷油吃下不来,吱吱叫奶奶……这一次却是奶奶睡得香甜,我叫喊着,奶奶,奶奶,我唱得好听吗?奶奶紧闭双眼,不予理睬,我再喊,直到眼泪喊了下来。奶奶认定了前面有个天堂在等她,所以她走得毫不迟疑。
爷爷说人死了一捧尘土,奶奶说积善要升天堂,尘土也是要升天的,奶奶的道理大概是这样吧。
奶奶离开了我们,母亲顿时暗淡了许多,很少见她大声说笑。往日母亲总是抱怨奶奶拿不多的粮食做好饭叫别人夸奖,你夸好吃就坐下吃呗!奶奶图的是虚名,她自己却饿肚子纺线,纺车摇起来带着风声,发出的声音像那支歌的配乐,我那时想,奶奶摇纺车心中哼的肯定是小老鼠上窗台喽。
奶奶是这样的人,她永远需要一种称赞,不断用自己的真诚换取着一声声赞美,奶奶喜欢。母亲说,这世上,你奶奶是最好相处的人。
奶奶的死最伤心的当属爷爷,他一个人常常拄了拐杖走到奶奶坟边,坐下去一把一把往奶奶坟上填土。奶奶在世时爷爷常说:我死了你别太伤心,往我坟上抓几把土就行了,而先去的却是小他十几岁的奶奶。叫他如何不一遍遍感伤呢!
爷爷已九十有三,在离开奶奶十几年光阴里,不下地只下棋的爷爷,身体出奇的好起来,渐渐扔了拐杖,倒背手在大街上漫游,不再下棋,嗜书如命,记忆越发清晰,能讲述出《红楼梦》中的每一个人物,亦能一段一段给村里老人唱评剧大戏,人们说是奶奶把阳寿借给了爷爷,这当然是一种美好的想象,但奶奶在世时对爷爷的深情,足以支撑爷爷再走好长的路。
谨以无限真诚的心去赞美一声奶奶的美丽,换得奶奶天堂里不灭的笑容,一脸的红扑扑。夜静时,我在问,奶奶,你在天堂还好吗?
孔庆先,作家,现为河北某市报社副总编辑。
苏善生 刹那雪乱的青春悲歌
苏善生
我一直在听《恋恋三季》,一部越南电影的主题曲。哀伤,无奈,支离破碎。
又是一年,今晚开始总结过去的岁月,竟然是一首悲歌。我得到了什么?我失去了什么?竟然似乎是一无所有。
生活是为了什么,人的一生究竟是为了什么?圣经中告诉你人活着就是一次考验而已,有的进天堂,有的进地狱。如此看来,人活的意义真的很微不足道,人活了几十年,其实只是一道考试题。
我曾经怀揣诸多梦想,做能给家乡贡献的企业家,做能留下千古经典的作家,做一个逐臭的名人。有的实现了,有的即将实现,有的似乎永远也无法实现。
这个世界,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有的人即将死去,有的人即将出生。有的在熟睡中安详,有的人在睁眼中煎熬。
日照还是没有下雪,却飘起了春雨。我在这里过了三个冬天,只遇见一场大雪。那个夜晚,在橘黄的路灯下,在蔓延的公路上,我们为终将逝去的青春大声的歌唱。
我的青春是什么?我的青春是中学辍学,是家庭贫困,是出门在外,是受尽凌辱,是住潮湿肮脏的地下室,是在高高的楼顶做广告牌。
我的青春是什么?我的青春是白手起家的公司因资金无法周转而破产欠下一屁股的债,是深爱的女人患了绝症我倾家荡产终究一无所有,是远走他乡另寻出路遇到苛刻的老板三个月只给了四百元钱,是在陌生的城市里和一帮陌生的年轻人在雪地里大声的歌唱。
那歌声是冷夜里温暖的火炉,它以为能改变世界,改变冬天,改变身边的零下三度,最终他才发现,除了自己,身边的一切依然如故。
我的青春在祭奠的香火中灰飞烟灭,在春节的烟花里一地尘埃。
我一直在努力的向上走,可是那年的天太冷,路太滑,于是我始终无法前行。我在青春的印痕里阅读,读川端康成,读爱因斯坦,读安妮宝贝,读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
我的青春外表软弱,以为内心便会坚强。却在除夕的夜晚,与母亲的电话里满脸泪水,哭声震天。那是可以撼动青春的哭声,他让年华裂了一条大缝,这条缝隙,是处女的血,幽深而无法复原。
我试图寻找一种依靠,我试图在城市的角落里安稳的站住脚。于是我深思熟滤,于是我勾心斗角。于是我成了一个商人。天天尔虞我乍,夜夜阴奉阳违。早上醒来,太阳照常升起,我已不是原来的我。
我厌倦如此的生活,于是放弃一切。感情却如影随身,我爱的人,希望她也爱我,却总是事与愿违。我写作,写爱情,写亲情,写生死离别,写圈来套去,写千古绝恋,写的天地间神鬼莫测,风云四起,漫漫飞红。
深夜,我突然想起过往,忽然想起去年夏天,一个认识不久的女孩给我打来电话,她说她和她男朋友分手了,来到这个城市,想问我借一百五十元钱,好安身立命,寻找新的一种生活。我拒绝了,后来又遇见那个女孩,她成了一家洗浴中心的小姐。我请客人去那个洗浴城时遇见她,她已不是我曾经认识的她,浓状艳抹,神情落泊。她说,因为我没有给她那一百五十元,于是她卖掉了身体。我只有无言以对。这不是我想要的结果,难道这就是她的应该的结果吗?我劝她离开,我说你去我工作的那个公司做个文员吧,一个月给你1200元。她笑:我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
我仓皇逃走,以为能逃脱自己的罪责。
忽然想起去年的秋天,一个女孩爱上我,她的男友纠集了几十个社会上的混混在胡同里拦主我,他说,你如果听话,就立刻在这个城市消失。我呵呵的笑,走近他,然后挥拳,我身材弱小,被他一把拿住按翻倒地。我闻见泥土的骚腥味儿,然后感受到几十只皮鞋在我的身体上弹着音乐。警察来的时候,人已经散光。于是不了了之,第二天那个女孩却没有上班。警察对我说,你赶紧搬家吧,这种人算不上你去拼命。我捂着红肿的脸,我挪动酸痛的身体,在派出所门口呵呵的笑。这就是我身处的社会,和谐,安定一个崭新的具有特色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我在潮湿的角落里苟延残喘,在十面埋伏里四面楚歌。我无路可退,艰难前行,只是为了无聊的生活。我穿行,拨开蒺藜,砍掉藤蔓,最终浑身是刺。
我又是另一个我。
这个社会,到处是造假,到处是欺骗,到处都是真理,到处都是狗屁。我在这汪叫作人生的浑水里渐渐长大。口鼻污浊,四肢肮脏,神经麻痹,没有了幸福的知觉。
我出生的时候就以哭声来呼喊幸福,我在学会走路时以脚步寻找温暖。我成年之后却找不到一件可以称心如意的道具满足我微小的残缺。
小小的世界,小小的城门,小小的人。小小的温暖无处可寻。
前几日,家里打来电话,是我的二姐要在腊月结婚。这是她第二次的婚礼。第一次没有参加,我不知道会不会去参加第二次。我的二姐的人生和我决然不同,我一直在外奔波,寻求可以到达彼岸的路。彼岸其实很近,就是走出家门口的那座山。我的二姐却一直呆在家里,小学毕业就开始去山上割草喂养,和母亲一起操持那个家。我二姐结婚的时候,已经26岁了,是个大姑娘了,因为我二姐有点傻,她不是那种傻,只是脑筋反应不够灵活,有点迟钝而已。她和山的另一边的一个男人结婚,三个月后决定离婚。原因是那个男人有遗传病。那个男人不同意,我二姐只好躲了起来,那个男人找到我的家,用衣服裹着一块碗大的石头,他走进我的父亲,扬言如果不把我二姐交出来,就用石头了结我父亲。那年我父亲已经6两岁,弯腰驼背,满脸皱纹,牙齿已经掉光,眼睛看不清五米之外的天空。我的母亲身子骨很小,又瘦弱,她已经56岁,那是她56年来第一次看见有人要行凶,而行凶的对象是和自己的一起生活了38年的男人。我父亲努力的直起腰,想看清眼前这个男人的脸。却是一片狰狞。那个男人以为我父亲在挑衅他的凶狠,甩起膀子就要把石头往我父亲的头上抡。是我的母亲,有那么多围观的乡亲,只有我的母亲像一头小鹿一样整个人顶了上去,她那一刻的力气应该是惊人,当时我在三百多公里外的城市,也许正在办公室里喝着茶水。我母亲安分收己,也是这样的教育我们,一遍遍的叮嘱我们不要惹事生非。母亲平平淡淡的过了56年,第一次去顶撞别人,而且用的不是语言,是自己弱小的身体。那个男人轰的一声撞在地上,久久爬不起来。我父亲已经就这个时间,在墙角抡起了铁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