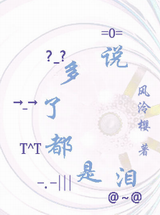说出来已是泪流满面-第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张承志 静夜功课
子夜清时,匀如池水的夜静谧地等待着,悄悄拍了拍,知道小女儿这回真地睡熟了。
蹑脚摸索,漆黑不见门壁。摸索着突然踢了椅子一下,轰隆砰然的炸响惊得自己晕眩了刹那。屏息听听,暗幕中流响着母亲女儿的细微鼾息——心中松了一下。
摸至椅子坐下,先静静停了一停。
读书么?没有一个读的方向。
写么?不。
清冷四合。肌肤上滑着一丝触觉,清晰而神秘。我突然觉察到今夜的心境,浮凸微明的窗棂上星光如霜粉。
我悄悄坐下了,点燃一支莫合烟。
黑暗中晃闪着的一星红点,仿佛是一个异外的谁。或者那才是我。窗外阴云,室内沉夜;黑暗充斥般流溢着,不知是乌云正在浸入,还是浓夜正在漾出。其中那一点红灼是我的魂么,我觉得双目之下的自己的肉躯,已经半溶在这暗寂中了。
我觉得那红亮静止了,仿佛不愿扰乱此界的消溶。于是我坐得牢些,不再去想书籍或纸笔。
这样,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了真正的夜。我惊奇一半感叹一半地看着,黑色在不透明的视野中撕絮般无声裂开,浪头泛潮般淹没。黑的粒子像溶了但未溶匀的染料,趁夜深下着暗力染晕着。溶散有致,潮伏规矩,我看见这死寂中的一种沉默的躁力,如一场无声无影的角斗。
手痉挛了一下,触着的硬硬边缘是昨夜读着的书,高渐离的故事。
远处窗外,遥遥有汽笛凄厉地撕裂黑布般的夜,绝叫着又隐入窗外沉夜。高渐离的盲眼里,不知那永恒黑暗比这一个怎样;而那杀人呼救似的汽笛嘶叫,为什么竟像是高渐离的筑声呢。
我视界中的黑暗慢慢涌来,在我注视中闭合着这一抹余空——若是王侯根本不懂音乐呢——黑潮涨满了,思路断了。
我在暗影里再辨不出来,满眼丰富变幻的黑色里f没有一支古雅的筑。
那筑是凶器……
我决心这样任意遐想一回。应该有这样的夜:独自一人闭锁黑暗中思索的夜。如墨终于染透了、晕匀了六合的纸,我觉得神清目明,四体休憩了。我静静地顺从地等着,任墨般的黑夜一寸寸浸透我这一具肉躯。
墨书者,我其其中信任的只有鲁迅。
但这夜阵中不见他,不见他的笔。渐离毁筑,先生失笔,黑夜把一切利器都吞掉了。是的,我睁大双眼辨了许久,黑色的形形色色中并不见那支笔。只有墨,读不破的混沌溶墨。春秋王公显然是会欣赏音乐的,而到了民国官僚们便读不懂鲁迅的墨书。古之士子奏雅乐而行刺,选的是一种美丽的武道;近之士子咯热血而著书,上的是一种壮烈的文途——但毕竟是丈夫气弱了。
因为乌云般的黑暗在浸漫淹没,路被黑夜掩蔽得毕竟窄了。
我心中残存着一丝惊异,仍然默默坐在黑暗的闭室之中。黑暗温暖,柔曼轻抚,如墨的清黑涤过心肺,渐渐海上来,悄然地没了我的顶。
近日爱读两部书,一是《史记?刺客列传》,一是《野草》。可能是因为已经轻薄为文,又盼添一分正气弥补吧,读得很细。今夜暗里冥坐,好像在复习功课。黑暗正中,只感到黑分十色,暗有三重,心中十分丰富。秦王毁人眼目,尚要夺人音乐,这不知怎么使我想着觉得战栗。高渐离举起灌铅的筑扑向秦王时,他两眼中的黑暗是怎样的呢?鲁迅一部《野草》,仿佛全是在黑影下写成,他沉吟抒发时直面的黑暗,又是怎样的呢?
这静夜中的功课,总是有始无终。
慢烃地我习惯了这样黑夜悄坐。
我觉得,我深深地喜爱这样。
我爱这启示的黑暗。
我宁静地坐着不动,心里不知为什么在久久地感动。
黑暗依然温柔,涨满后的深夜里再也没有远处闯来的汽笛声。我身心溶尽,神随浪摇,这黑暗和我已经出现了一种深深的默许和友谊。
它不再是以前那种封闭道路的围困了。此刻,这凌晨的黑暗正像一个忠实的朋友,把我和我的明日默默地联系在一起。
张承志,著名作家,原籍山东济南,1948年生于北京。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北方的河》、《黑骏马》、《西省暗杀考》、《清洁的精神》、《心灵史》等。
张承志 师傅窑
如今回顾那样的地方,确实有些隔世之感。
人总是难逃次次的离别,而离别久了,又难忍阵阵的向往。
这也是在大西北惯见的一种地方。泛碱的秃山,焦黄的干沟,可是走在弯弯的沟里,看见不高的房坎上,有个半塌的小小窑洞。山沟和窑洞配在一搭,平添着荒凉的气氛。只有一扇嵌在窑口的粗木头门,因为雕有些花,露出些新据的白木碴,才显出这不是一眼废窑。
一
记得那时我和娃娃,还有他爷一共三人,就从窑上头的这个愣坎跳下。下头窑门对着一片场,三面的陡坎,像围了一个护院。喘着在窑门站定,说也怪这场上没有风。那时我们看着下方,见夹沙的狂风就在鞋子下头,顺着干沟呜呜穿过。我还眺望沟口的平坦处,见一溜烟尘,白烟滚滚地奔到沟尽头,在开阔地里消散了。
如今在兰州的馆子,娃娃已经干了八个月。
若是他家里非要在今年娶上亲,娃娃也已经能掏出个数。而那一天,他爷的表情严肃,粗嶙群的大手捏着两支香。记着那天的步步举动我觉得新奇;山外头,文学界,那一年闹了些什么,都忘了。其实当时我尚不能觉悟到,那以后,它们一天天地,与我两不相干。当然不是真的两不相干,而是千年的擂台,咱们比个生前身后。
进了窑,风声被隔开,眼睁睁瞪着洞里的层层石渣硬土,突然觉出一片寂静。我总忘不了他爷“噗”一声,把皮祆甩在地上。大皮袄,西海固汉子的心爱物,翻着厚暖的白花花羊毛,平摊开铺着,使我看得暖和。
——即使此刻也忍不住一股冲动,想跪到那白软的羊毛上去。人声鼎沸的外界正骚情什么“千禧”。人和人就这么不同,不知是该为这伤心,还是该感到庆幸。娃的爷说,国民党的三个师从陕甘两省合围,把我父亲他们一伙子围了一个生铁桶,四下里打炮。我听得入神,我没有见过家族和历史连得这么紧的例子。
百姓造反没下场,没下场……他爷自语着。
而一座孤窑平衡了成败。那以后世间便不见了一个人的模糊影子;而这眼窑,却渐渐地瓦匠木匠各修几下,成了生者对他的念想。那个冬天,娃还是一个俊秀的少年,巴闪着一双水灵灵的大眼,听话地跟在一旁,手里握着色兰香。我暖暖跪坐在羊毛主瞥一眼窑外,看见了绵延的黄土浪头。
二
一个时期里我无法安心,一个字写不下去,痒痒地幻想着什么。一个背影,一个魅人的影子,充填了我饥渴的想象。如今娃已经拔节长大,到了着急娶亲的年龄。农民嘛,急完了春天的吃食,就忙着急冬天的媳妇。他爹不像他爷心大,自从娃进了二十岁,便忧心忡忡,生怕娶不上媳妇惹人家笑话,天天地催娃。
而我,心里怀上了这个影子,便一眼透过,在深层和农民相遇了。农民的心事,就寄托在这家窑荒山。这么想着,久了,甚至连一扇扇粗木雕花窗也愈发好看,上立邦漆太白,上平价清漆太黄。添一斧过多,减一刀太少。无论当面或是想象,每次我望着它,都活生生像望着个西海固的孤苦农民,禁不住心怦怦跳。
后来恍然感到,我也该去窑里点个香。路上遇见个本省知识分子不以为然,智里一般数落我,“你怎么把自己降低得和农民一样呢?”他说。
要紧的是我别降低得和你一样,我想。
青白色的一缕烟丝扶摇上升,纠缠又线绕,像我们烦乱的心绪。和人事一样,地理也是不平衡的,陷入赤贫的民众,总是向土地索要些安慰。所以我们不单有脾气大的知识分子,还有机密大的地点。窑外黄土山如耀眼的白浪。我舒服地跪坐在娃和他爷中间,那缕青烟旋绕着,流入了我的怀抱。
那一年娃娃长得像个俊俏姑娘。大人们开玩笑时,说以后娃娶亲不用花钱,反过来向女家要也能成。他爷呢,从来他爷不露本色,他总揽家族大事,包括引我走师傅窑。
一扇门,关着刚烈的感情。一方土地,藏着感人的地点。谜底是什么并不重要,人们在窑里找的,也许不过是个人的心愿。
我在那一年,曾经是怎么个样呢?我总在问自己。也许今天的这个并不是我;真正的,魂儿随着一缕烟,从那天就没有回过家。
在窑洞里,青烟还在缥缈地一摇一闪,沉思般渗入粗额的窑壁。艰难的是十数年如一日,人总要打发死板岁月。本来,人们虽然没有那么想,可是意识里却暗暗以为,会来个什么变化。不,只有水流不尽的日子,堕落无边的现世。
青壮打工去,割麦重与姑。我也和朋友商量,把娃娃弄到兰州,向城市要钱。如今娃娃已经棱角租拉,下巴和颧骨都穴了出来。只是架子薄弱,下苦打工好像挺吃力。
后来我在兰州见了娃娃一面,千叮咛万嘱咐,要求他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一定要把钱拿上。娃娃说,已经挣上了两千五。再过半年多,一次,他在远远的电话那头告诉我,已经挣到手六千个元……我逼真地觉得,电流里传着暖暖的希望。
手抓电话说着,说着,眼前突然跳出师傅窑。有人说他牺牲了,有人猜他隐遁了,说着猪着几十年。他也永远是一个谜,使西海固更加难解。
凄凉的风景若是看得太久,渐渐会“无视”。我就已然不见身近,无论围着什么世界。他们几十年地怀念一个人,这感情令我陶醉。我的心事、年龄以及视野,都固定在那天,那个和娃娃、他爷一块在师傅窑度过的冬日下午。在窑前波涛滚滚的,那些红岩石白碱土的穷山,在心事和想象中生动地变移。
我喜欢这陶醉的感觉。此刻,我对面的墙壁,现出了层层石渣硬土。一股青袅袅的香烟,对着怀抱,旋绕着飘起来了。
。。
徐小斌 母亲已乘黄鹤去
2006年12月1 日,入冬以来最寒冷的一个日子,妈妈走了。
正在做晚饭的时候,电话铃突然想起,侄儿轩轩的声音传来:“三姨,姥姥不行了!”我的心剧烈地抖了一下,因为前几天似乎就有强烈的预感。“抢救啊!赶快抢救!!”——“已经叫了九九九,正在抢救!”我急如星火,竟然忘了穿毛衣,披了件大衣就冲到夜晚的寒风里。
在寒风里抖了七八分钟,竟然打不到一辆车!坐地铁!刚刚走进地铁的站口,手机又响了:“三姨,你直接去积水潭吧!”“什么?这么冷的天还要把老人折腾到积水潭?把大夫请到家来抢救,告诉他们我愿意出双倍的钱!”“……三姨,不是的,姥姥……已经走了,抢救无效,已经宣布死亡了……”我的双腿一下子奇怪地软了,走路就象在水上飘,我机械地走进地铁车厢,听见轩轩在说:“三姨,你直接到积水潭后面的太平间吧,等着你来挑寿衣呢!……”
然后,就再也听不见了。
第一眼看到的是妈妈的手。妈妈的手,曾经那么丰腴、漂亮、秀气的手,现在干瘪得挤不出一滴汁水,是那种干裂的土地的颜色。妈妈的脸是灰白的,大张着嘴,似乎还想向上天要一口气,只要有这一口气,妈妈还能活,可是上天就是这么吝啬,他再不肯把这一口气给这位耄耋之年的老人了。
妈妈的身上,依然盖着那条家常的旧被子,身上穿的,依然是那件旧毛衣。不知给她买的那些新衣裳,新被子上哪去了,还是因为她舍不得穿,舍不得盖?
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大约是憋得太久,已经滚烫,那样滚烫的泪一滴一滴落下来,好象能够熔化金属,但实际上无比寒冷——在太平间里化成一股白色的水汽,令人寒冷彻骨。
我什么都不懂,一九八二年父亲去世的时候我还太年轻,一切都是姐姐说了算,可现在一个姐姐远在外地,一个姐姐远在美国,弟弟全家和侄儿轩轩,四双眼睛都在看着我。
我说:寿衣当然要最贵的,最好的。
太平间的师傅立即把最贵的拿出来,是紫红绣凤的,凤凰是机绣,做工粗糙,土得掉渣,否定。
然后又把各种寿衣统统拿出来:选定了一套紫色绣万字花的,师傅说,老人西行应当铺金盖银,一看,果然垫的是金色,盖的是银色,就点头要了。穿了一半,轩轩突然跑进来说不行,他说姥姥高寿应是喜丧,按规矩要穿大红的衣裤,告诉我医院附近有卖寿衣的,可选择的很多。
挑寿衣挑到手软。终于挑到一种真正的大红,手工绣花,福寿字,缎面,金丝绣的垫子,上下有荷花寿字如意,紫红绣梅兰竹菊缎鞋,最满意的是我把那条盖被换成了一条银色绣古画的,上面还绣着驾鹤西行四字草书,雅致且古色古香。
母亲的脸经过淡装和修整,变成了生前的模样。
我是最不被母亲待见的一个孩子。这大概是因为我虽然外表温顺,但其实又倔又拧又叛逆。很小的时候便显出这个特质,譬如有一个下雪天,和姐姐们一起到外面玩,把新棉袄全都弄湿了,妈妈说该打,就让我们三人伸出手,由爸爸用尺子打,大姐二姐还没挨上就哇哇哭了,求饶。我却被尺子打到手肿还坚持着:“就出去玩!就出去玩!”含泪咬牙不哭出声——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可惜这句老话在我很大了才知道,那时我早已改不过来了,于是这辈子也就只有吃亏。
小时候我只上过几天幼儿园,阿姨说,走,我们看小鸭子去!我们就排着队走过院里(现在的北方交大,那时叫北京铁道学院)那条石子马路,那条路可以路过我的家,我远远就看见了妈妈在门口晾衣裳。门口有两根晾衣竿,形状有些像单杠,中间系四根铁丝,这两排房的衣裳就都晾在这儿。对我们来说晾衣竿还有一重功效,就是当作单杠悠来悠去,比谁悠得高,比谁做得花样多。
那一天,我毫不犹豫地向妈妈跑去。尽管阿姨说,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