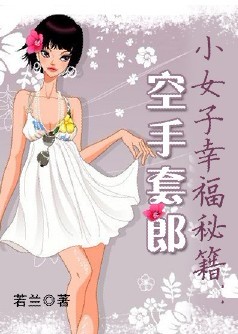一个小女人的常春藤之旅-第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既然是为乔庆祝,理所当然先看菜单,点些平时难得享受的美味,像山羊奶酪、香槟、沙拉、酸酱之类的。可是我在干什么呢?我从钱包里找出刚才保存大衣时服务员给的小票。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我不由自主地审视小票背后的铅字。字体如此之小,以至于裸眼几乎看不见。它这样写:“餐厅对客人超过两百美元个人财物的损失不承担责任,除非有书面收据能证明它的价值;餐厅对客人超过三百美元的损失不承担责任,除非有过失或疏忽。”
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但是我很有兴趣知道。“我不喜欢这种腔调。”我断然地对乔说,他正忙着看酒水单。
“什么?”他说,还沉浸在有皮诺、赤霞珠的长长酒水单中。
“他们把丢失我们大衣的责任限制在二百美元和三百美元以内,我不能完全理解。但是也没关系——大衣是无价的!”我声音提高了很多。
这时旁边座位的人朝我们方向窥视。
这件大衣在我看来就是无价之宝:它是家族祖传物,是用深棕色的皮制成,缝制得恰到好处,穿起来嘻哈帅气又有点怀旧的味道。我是读大学时从乔的衣橱里偷来的,然后向他宣布这是属于我的了。我记得乔当时告诉我,他哥哥很久以前打猎时打到一只鹿,家里人把鹿肉吃了以后,把鹿皮制成了这件大衣。他哥哥打猎得来的鹿皮做成大衣跟我没关系——我不关心打猎——但我真的很喜欢这件大衣。我心安理得地穿着这件大衣,觉得自己酷极了,这可是我当时男朋友哥哥打死的鹿皮做成的。乔的家族和大部分土著美国人一样,绝不浪费猎物,这不是很引以为豪吗?
上法学院之前,我一直幻想哪天穿着这件大衣能遇到乔的哥哥。“哦,我记得这件大衣!”他开始如数家珍,把故事又讲一遍。
随着故事的展开,我知道乔不仅有一位坚韧、爱他的妈妈,会做很多炖菜,用很多番茄酱;还有一位在威斯康星小镇上担任狩猎监察助理的爸爸,他工作的一部分是记录汽车撞死鹿的数目,然后让人把动物尸体拖到镇上集中处理。我信奉的犹太教教规规定,不能吃汽车撞死的鹿肉,在乔家也不行,但是可以使用合法得来的鹿皮,因为鹿皮有很多用处,其中之一就是制作大衣。这些鹿皮说不定哪天会穿在毫无戒心的姑娘身上。
我跟乔说这件大衣是不可替代的,我并没有说谎话。对这样一件家族祖传物的丢失竟然不承担责任,我的法律思维该怎么发挥作用呢?显然这张小票背后的告示是胡说八道,我不能放任不管。我喝了皮诺(酒单上最便宜的酒),变得有恃无恐了,我向乔狂言,我要求服务员马上把大衣还给我。
乔望着我,提议我们开始用餐,并且把鸡块放在中间。“吃你的烤虾吧,还有芒果…罗望子酱,快尝尝,我们好好庆祝一下!下个月,我们也许就可以经常吃得起这样的大餐了。”乔把一叉食物硬塞到我嘴里,让我闭嘴。
“嗯,但是……很不公平啊,真好吃,虾的味道好极了。”我笑眯眯地看着他,“再次祝贺你找到新工作,亲爱的。我真为你骄傲。”
晚餐愉快地进行,吃完饭乔坚持他去取大衣,还留了一笔不少的小费呢。我还没来得及开口,他就已经把我推挤出了大门。不过我还是很高兴地穿上这件漂亮、温暖的大衣,和乔挤入地铁的人流中。到了学校后,我敢说我是哥伦比亚大学唯一一个穿马路轧死动物做成的大衣。
。 想看书来
第四章 恐惧厌恶综合症(1)
“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
——中国谚语
感恩节就要到了,我似乎能感受到远处爆竹的隆隆声。我远远没有料到暴风雪真正来临时的残酷。期末将至,所有人关注的期末考试——考试结果将记入我们整个学期的成绩——很快就要降临了。我想没有哪个法学院一年级的新生会不害怕即将到来的考试,这将是一场残酷的考验。
没有钱(或者坦白说,没有这个意向)回威斯康星州度假,乔和我计划跟雷切尔、戴维一起举办感恩节盛筵。我和自己默默约定不要想令人恐慌的考试,一切等盛筵结束之后再说好了。我们四个达成了两条简单的协议:所有的酒必须喝光;谁都不许说一个有关法律的字眼。我们的公寓——感恩节盛筵举办地,被宣称是法学院豁免地带。我是这样计划的,当雷切尔和我做饭时,戴维和乔看球赛,我们会准备好火鸡等材料。筵席后,男人们收拾厨房,女人们休息,看Grease——一部我和雷切尔都喜欢的电影。
我把学习暂时推倒一边,花了好几个小时专心阅读菜谱,虽然是临时抱佛脚,但至少对烹饪有了粗略了解。虽然我的实战经验有限,但我有很多奇思妙想,我要举办一场真正盛大的马莎?斯图尔特宴会。有了这个想法后,我去商店买了好几种烹饪杂志:《美食》、《食品和酒》、《口味》、《烹饪说明》,它们给我提供了很多种不同的感恩节盛宴方案(经典的、南方的、新英格兰风格的、西南的、泛亚洲的、质朴意大利的)。我翻着彩页,陷入沉思,咸味火鸡肉卷加蘑菇、攸面烤火鸡加菠菜、熏肉、腰果馅,或者火鸡三明治加黑橄榄、酸酱,酸酱可以用第二天的剩菜做,我还会做豆瓣汤。
列出购物清单后,我突然意识到,我的助学贷款恐怕负担不起一个需要187种配料的感恩节晚宴,其中包括烤栗子、面包圈、山羊奶酪、新鲜柠檬香草。事实上,我们公寓的宜家熨衣板都没有《缤纷家居》杂志上的好看。尽管不情愿,但我还是得承认我只是马莎,成不了马莎?斯图尔特。
最后我还是屈服于我的草根地位,准备了这样一份菜单:有烤黄油圈加火鸡、蒸绿豆、奶油蘑菇汤、罐头油炸洋葱、山核桃派,还有加红糖的烤通心粉、奶油酱以及大量的便宜酒。我所想象的丰盛感恩节晚宴应该在罗利大厦举行,女仆身着利落的统一制服,手托银盘来回穿梭,怀特默家就是这样的,想到这我有些嫉妒和遗憾。但我又想,我们这儿也可以开怀畅饮啊(虽然都是便宜酒),还可以看Grease呢,证明我们没有喝醉。
虽然我幻想感恩节盛筵应该是华丽丰盛、极有情调的,但我还不至于太脱离现实。乔和我能抽到哥伦比亚大学的福利房就已经很幸运了。我们的公寓算不上华丽,但我们没有任何怨言。当其他同学必须住在法学院的学生公寓时,我们真的很幸运能住119号大街的一居室公寓,我们有三个壁橱呢,地上铺的是拼花地板。这就是早结婚的好处,至少在哥伦比亚大学是这样,可以不用住宿舍,安排住房时还排在毕业生的前面。当然房子没那么完善,厨房壁橱是改装的,热水从来都不热。冬天还必须把窗子打开,因为散热器超负荷工作了。最大的好处是离法学院只有三个街区。总之,我觉得住在这里非常好。不像雷切尔和戴维住在昏暗、肮脏的铁路第六公寓,周围全被住宅包围了。他们公寓的电梯很不稳定,每次去他们家我都情愿爬五层楼梯,也不想坐电梯。 。。
第四章 恐惧厌恶综合症(2)
我们公寓挺大,但没怎么装修。当我计划感恩节晚餐时,突然想到厨房只有两把椅子,加上我书桌前的转椅也才三把。我们有四个人参加,我只好向隔壁邻居借——他家总是散发着水煮白菜和烤马铃薯的奇怪味道——最好是折叠椅。接下来的问题是炊具,乔和我几乎没有什么炊具,我们只有一个长柄的煮锅,雷切尔和戴维跟我们情况类似,只能贡献一个平底锅了。最后我们东凑西凑,炊具差不多够用了。还有一个障碍是,我们厨房太小,一次只能容纳一个成年人,这个问题不好解决。
不管怎么样,雷切尔和我开始动手了。先把火鸡的内脏掏干净,我们俩捏着鼻子把这些恶心的东西扔到一边,然后把准备好的点心拿出来,看看往火鸡哪个地方塞,有蘑菇黄油、蒸过的冰冻绿豆,做成每年感恩节我们妈妈折磨我们的那些吃食。我们打开真空包装的火鸡和啤酒,然后打开意大利面条。这时我们突然意识到,我俩压根不会做呀——我俩对视片刻,再看看压缩面条,忍不住哈哈大笑。看来我们举办一次豪华盛筵的计划要泡汤了。
好啦,我们去街上饭店也可以过感恩节啊(没准比我们现在吃得好,还便宜呢),我们也不用这么劳神费时了。不过雷切尔和我都很为我们亲手做晚宴而自豪。我们做的火鸡恰到好处,配的馅丰富又美味。我们还准备了好多酒。避而不谈法学院就像在感恩节获得了一笔意外之财。
晚餐结束后,雷切尔和我退守二线,躲在起居室看碟。先进行练歌前的热身运动(每个Grease粉丝都知道约翰和奥利唱“夏夜”时是全剧的高潮)。我俩拿着酒瓶当麦克风,雷切尔唱丹尼部分,我唱桑迪部分。“迷人夏季,疾风吹过”,雷切尔用假冒的男中音开始唱了。“迷人夏季,突然降临”,我用令人难堪的颤音回应,我们步调一致,鬼哭狼嚎,直到男人们忍无可忍,强烈要求我们闭嘴。
考虑到邻居透过薄墙可能听清每个曲调,乔和戴维及时制止了我们的演唱。我们四个围坐在沙发上,吃着黏乎乎的山核桃派,喝着啤酒。感恩节就要过去了,为了给节日增加气氛,大家不住地插科打诨,笑声不断。
我们已经尽最大的努力,谈话绝对不涉及法律,但戴维还是忍不住想出击了。
“马莎,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他避开我的目光,看着我的书房,我书桌上还放着一本法学院一年级注册簿。
“戴维,我们说好了,今天不谈法律。”
“不谈法律。噢,这真是一出有趣的益智戏剧!”他承认错了,醉眼矇眬地看着我。
“哦,继续吧,亲爱的。我从没见过戴维今天这副德性。”乔说。
“好啊,该死的书都滚到一边去吧。”我舒了一口气,雷切尔和乔哈哈大笑。
戴维不可救药地被哥伦比亚法学院的注册簿萦绕着。我们报到时,340名法学院新生都要在大厅的白墙前拍照、登记。这些照片被制成小册子,每张照片下详细记载了每个人的姓名、家乡和本科学校。戴维是福德姆法学院的学生,福德姆是曼哈顿很不错的法学院,不过跟哥伦比亚的排名第4相比,它排名第32。我猜戴维和他女朋友学校28名的差距使他有一种自卑情结。这也难怪,哥伦比亚学生对他具有一种奇怪的蛊惑力。他对我们注册簿上的每个人烂熟于心。他对自己超强的记忆力颇为自豪,我们经常拿此做测验。
第四章 恐惧厌恶综合症(3)
我拿起注册簿,随手翻到一页,选了我同学的一幅照片,“米兰达?哈钦森。”我大声念出。
“哦,这个我知道!”他欢呼,“她来自纽约的富兰克林广场,本科是布朗大学。我要补充一句,她不是特别上镜。”
“安东尼?皮日娄。”我继续出题。
“他来自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布鲁克林,上过耶鲁。他这张照片上系着领带,谁会在报到时戴这玩意儿?”
雷切尔从我手上夺过注册簿,“戴维,你真是个怪胎,你怎么能记住这么多人?”
“我都是上厕所时研究的。”他回答,好像这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
“不管怎么说,怪胎,这个你肯定不知道,丽莎?曹。”
“哈,你别以为那么容易愚弄我,宝贝。她来自中国北京,但是她在梭尔邦大学学习过。”
“一点没错。”
我们三个轮流出题考戴维,这样玩了好一会儿。戴维基本都能答出,只在极少数时需要提示(“你只要告诉我他从哪来,其他的我就会记起来了”仅此而已)。后来,我的胃疼了起来,我们只好终止这个游戏。我起初以为是吃多了山核桃派的缘故,但是过了一会儿,我的肚子开始咕咕响了。游戏结束后,我怀疑自己是不是生病了。
“我觉得很不舒服。”我软弱无力地说。
“你摸火鸡前用热肥皂水洗过手了吗?”乔问。
“当然啦,我摸火鸡之前非常仔细地洗过手了。之后我就不确定了。”
“但是,马莎,你难道不知道生火鸡有上千种细菌吗?大肠杆菌、沙门氏菌、利斯特菌等这些狗屎。”雷切尔说。
显然我不知道。显然我不够吹毛求疵,我在往火鸡体内塞东西时,火鸡的传染病毒都到我身上了。我全速冲进了洗手间,为了准备美食,我差点遇险。戴维冲我背影大喊,“马莎,你确定你不需要带上注册簿吗?”
我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我的胃还被沙门氏菌搅得难受,我的头因为酒精残余物直犯晕。我必须面对现实啊,现实是我在法学院的第一场考试即将来临。还有三周的课,接着是假期后两周的“复习时间”,考试就来了。仅仅想想这件事,我的灵魂就和我现在的身体状况一样糟糕。
法学院的考试是一次性的,没有期中考试,没有平时测试,课堂表现也不打分(这对旗手来说真是太不幸了)。只有通过四小时的考试测试你一学期学的所有东西,结果呢……事关重大。第一学年的考试成绩对于将来能否到法律评论工作,毕业后能否在有声望的司法机关实习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只有获得这些殊荣的人才有机会进大律所,拿高薪水。但是参加这样极其重要的考试是很盲目的——因为参加这样的大考前,你对自己的学习情况没有得到任何反馈,就是说你对自己完全没底。你只能交叉手指、屏住呼吸、祈祷最好的结果。要么祈祷,要么蜷缩起来大哭一场。当你像胎儿一样脆弱时是很难答题的。
我想得越多,心情就越糟糕,不仅仅是因为食物中毒和残余酒精在起作用。我认识到,虽然学了一个学期,我大部分是熬过一天算一天。我每节课都要准备大量的案例,但是很多时候上完课或者点名过后,我马上就把这些东西忘掉了。我的学习没有形成体系,我对侵权法、合同法或民事诉讼法没有进一步的理解,更不知道这些内容是如何组织到一起的,而这些正是考试要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