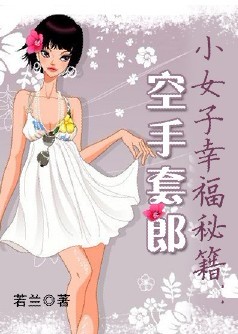一个小女人的常春藤之旅-第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不,我不这么认为。”我回答。
“为什么不呢,金小姐?黄油很危险,不是吗?”
“我想是的。”
“那么和枪有什么区别呢?”
“哦,人们买黄油是明知它对身体有害,但是还会去买,所以他们是自找的。我想人们买枪的话,知道枪在什么情形下是危险的,但是他们不可能知道枪会偶尔走火——这是他们当初购买时没有料到的。”
我答完后,等待我的不是猛烈抨击,而是我迄今收到的最轻松、愉快的回应。“啊哈!”他说,“这么说黄油购买者虽然购买的是有潜在危险的商品,但这种危险他们是事先知道的,他们愿意接受这种危险,所以呢,他们应当承担吃黄油的风险!非常好,金小姐。对于一个自愿的人,伤害不存在。”
第三章 像律师一样思考(4)
我紧紧抓住非常好,金小姐这几个词,像只瘦弱的松鼠拿着它唯一的橡子准备度过漫长、压抑的冬天。虽然,他没有说“你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学生,金小姐”,“我相信你总有一天会成为最高法院法官的,金小姐”,“我的课上肯定给你A,金小姐”,但我没有任何抱怨,一位教授对我说了赞扬的话,“非常好”这三个字足以让我飘飘欲仙了。
侵权课除了极大地提升了我的自信心以外,还给我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获:随着课程的继续,我的思想盘旋上升,我简直成了偏执狂。侵权法主要研究人们之间的“民事过错”——主要是一些疏忽、愚蠢但不构成刑事犯罪的行为,你需要分析遭受损失的一方是否应该获得金钱赔偿。民事侵害的案例有阑尾切除手术时手术器械不小心遗留在病人体内的,也有因为可口可乐瓶意外爆炸导致肢体严重伤残的,总之五花八门。
研习这些伤害案件让我懂得了很多东西,它使我意识到,危险潜伏在每个角落。一旦学习了侵权法,你看待生活的眼光绝对与以前不同了。我最开始意识到这一点是在我们学习20世纪20年代一个著名案例——帕斯卡夫诉长岛铁路公司案时。在这个案件中,一位叫海伦?帕斯卡夫的妇人(我想象的是一个善良的老妇人,浅蓝色头发,戴着有繁复设计图案的丝巾,穿着翻领大衣)买了一张去若克尔维海滩的火车票(我可以想象到了那里,她马上换上旧式的海滩装,包括有褶皱饰边的灯笼裤、保护发型的泳帽,和她的孙子们在海滩上尽情嬉戏)可怜的、毫无戒心的、无辜的帕斯卡夫太太正在站台上等她的火车,期待着她的海滨之旅,这时,灾难突然降临。
突然,一个男人跑出来,慌慌张张地赶火车,他的火车已经在轨道上开动了。事实证明,他真是个极其愚蠢的男人。他不仅仅蠢在试图跳上已经开动的火车,更要命的是,他还拿着一大箱烟花。他跳了一下就滑下来了,这时两个列车员帮着把他拉了进去。在拉他的过程中过程中,一盒烟花掉到了铁轨上,火车驶过的时候发生了爆炸。爆炸波及的范围如此之广,以至于“数英尺远的另一条站台”也发生了坍塌,这场灾难袭击了可怜的帕斯卡夫太太的头部,她受到了严重损伤。
帕斯卡夫太太是不幸的,但她不是个笨蛋,她选择对铁路方而不是烟花持有人提起伤害诉讼。法院所面临的争议是帕斯卡夫太太的伤害是否属于“合理预见”的范围?铁路方是否因为其雇员的过失——帮助烟花持有人上火车——而承担责任?
最终,法院决定铁路方不承担责任。因为谁能够料想到,在站台的一头帮某个人上车会导致帕斯卡夫太太头部受伤(顺便说一下,多大范围的受伤应当承担责任,是无法解释清楚的)?
经过连续几周这样的案例学习,我脑子中冒出一个奇怪的想法。虽然这些倒霉事情的发生令人捉摸不定,但我还是总结出来了规律——“反常现象大约每年发生一次,多半发生在那些行为古怪的人身上”。我现在变得有点神经质了,每当我在地铁站台上等车时,会紧张兮兮地观察站台另一端的等待人群——有没有人拿着形状可疑的包包,会万一脱落、爆炸、袭击我的头?
从学校公寓出来,走了几个街区,我脑子就开始胡思乱想了。要是鸽子飞到窗外的挂式空调上,拍打空调,空调承受不住,正好朝我这个方向跌下来怎么办?要是万一空调真朝我砸了下来,我慌不择路,不小心撞伤老妇人出来散步带的约克夏狗身上怎么办呀?要是我跑得太快,从小狗身上踩踏过去怎么办呀?会发生什么后果呢?我应当承担踩踏小狗的责任吗?或者责任应当归到纽约市政,如果早把这些鸽子毒死了,不是从一开始就杜绝悲剧了吗? 。 想看书来
第三章 像律师一样思考(5)
是的,这就是侵权法的思维,显然不是多好的视野。
尽管我精神上失衡,但我一直非常清醒地认识到,遵守如下法学院规则的重要性:绝不要跟任何人讲你学习多么努力。目标是表面上最小程度地学习,实际上最大限度地付出。要让学习看起来非常轻松、惬意,就像一切自然属于你一样。
然而,我还是准备打破这条戒律,向雷切尔、凯蒂和伊丽莎白吐露我的心声:我自从上法学院起就神经衰弱。每周四晚上是我们四个的玛格丽塔
由墨西哥龙舌兰酒、酸橙或柠檬汁以及橙味酒混合调制而成的玛格丽塔酒。
会议。我们通常选在百老汇上一家灯光幽暗的墨西哥餐厅,酒吧的吊顶装饰得十分考究,这里的酒别具风味,还不贵呢。我们四个整个学期的周四晚上都是在这里度过的,在这里结下了深厚的友情,我们谈论的话题主要是酒和法学院的闲琐之事。我从雷切尔口中得知,据说旗手以前是个童星呢,他小时候在阿尔夫屋以及一些类似的节目中出现过;从凯蒂口中得知,据传怀特默和A组的一个女生睡过;从伊丽莎白口中得知(她和那个女生在宾州是同学),怀特默的情人已经承认她是从哥伦比亚大学候选人中递选的。我们一致认为早上八点半的民事诉讼课,对刚从睡梦中醒来的女孩子都是一种折磨。
“你们过得怎么样?我想我正在迷失。”我坦言,透过玛格丽塔玻璃,我望着外面的霜冻,心不在焉地说,“我觉得自己要被击垮了,我承受太多了,你们明白吗?”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竟然在这些新朋友而不是乔面前大声说出这种话,承认自己的失败,“有时候我觉得自己简直冻僵了,什么都干不了,因为我甚至不知道从哪儿开始。为什么别人看起来都那么轻松呢?”
“没有人轻松。”伊丽莎白答道,擦了擦眼镜上的雾气。
当我们都点了冰冻玛格丽塔时,伊丽莎白坚持要把它带走。为什么呀?在这儿饮酒是多么畅快的一件事啊,没有人会赶我们走,我经常弄不懂伊丽莎白。
“你们自便吧。”她继续说道,“我必须严格执行我的时间表,每天晚上一个半小时学习准备第二天的课程,然后是四个小时准备下一周的课程。就这样,没有一分钟多余的时间。”
“我明白你的意思,马莎。”凯蒂说,“不仅仅是学习,你知道吗?是一种……是……无处不在的竞争气氛!他使我成了十足的偏执狂,我没有办法不和周围的每一个人比较。”
“是的!”我大喊,我很高兴不是我一个人在和自己的缺点较量。
“我告诉你吧——住法学院宿舍一点帮助都没有。”凯蒂补充道,“我敢说,和室友之间就是一场巨大的、古怪的竞争——谁是最努力的?我们都默默地注意对方,看别人学习如何。如果你晚上第一个关灯睡觉的话,似乎你已经承认被打败了。”
我耸耸肩膀。大部分法律学生都住得很近,以至于他们完全失去了理智,这样没有任何好处,我至少还有乔冲抵我的神经质。
“我这里也一样糟糕,”雷切尔说,“我的意思是,戴维和我每天晚上在床上详细研究美国统一商法的每个细节,这太发狂了,我不知道怎么停下来。我不确信我们是在相互支持、相互帮助,还是在相互超越。不管怎么说,法学院对我的爱情生活没有任何好处。”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三章 像律师一样思考(6)
我想起了昨天晚上,乔和我这么长时间以来第一次同时睡觉。我每天晚上习惯性地学得很晚,乔通常十点半或十一点睡觉,因为他干的临时工作要求每天早上八点半必须到办公室。但是昨天晚上我提早结束了学习,所以我们的睡觉时间趋于一致。当乔在我身上微妙地摩挲时,我努力使自己想点别的,不要再纠缠于双方合同和单方合同的区别。注意力集中,马莎,别再想法律了!*起来!听到没!但是我做不到,我的脑袋全被学校里那些无聊的东西塞满了。当我不情愿地拒绝乔时,我肯定不小心咕哝出了什么法律单词,因为当我意识到时,乔已经在卷被子睡觉了,他愤慨地说:“也许你应该和你的合同法教授睡觉——你们肯定有很多兴奋的枕边谈话。”这就是一对新婚夫妇的性生活。
突然,服务生端来一大盘薯片和沙拉,放在我们的小桌子上,差点撞翻我的酒。
“乔什上周末从过来看我了,简直就是一场灾难。”凯蒂说,她脸颊明显一阵红,看来她真的很难过,“他想出去参加派对,我想待在家里学习。他想谈论运动,我想谈论法学院。我们谈论审判时,他偷偷地看运动中心。周一我把他拉到我们的民事诉讼法课堂上,让他体会一下施德教授。他走之前我们大吵了一架——太糟糕了。他说我变了,他说这句话的方式真可怕。他走之前我们甚至都没有时间*。也许这样还好些,我是有些发疯。他不明白我的处境。”
犹豫了一会儿,伊丽莎白说:“你们怎么样?别再犯傻了,行吗?你们都需要放松一点,我也是学习负担过重,我们可以换一种视角。”
“哦,是吗?你能幸免吗?”雷切尔出击。
伊丽莎白无语。
“老天,我们真可怜。”我抱怨,“我们再来一瓶龙舌兰,怎么样?扮成*小猫,不要再做法律学生。”
第二天,我回想凯蒂的男朋友乔什对她说的话。他是对的:有时候法学院对我们的改变很微妙,有时候对我们的改变很深刻。开始时从小处入手,像写案例摘要成为我的自然反应。事实上,我对法学院图书馆的熟悉程度就像对自己的手背。当我在合同法课堂上被教授点名时,我似乎有些卖弄。当我在侵权法课堂上偶尔自愿回答问题时,我认识到举手并没有引起大灾难。我好像已经陷入了法言法语中,我没法不使用它。我变成什么样的人了?我和以前是不一样了。虽然我不情愿承认,但事实证明,我学到的东西着实令我兴奋。法律其实有点意思,有时甚至令人着迷呢——虽然很难理解。
第一学期快结束时,我已经完全进入了法律术语的新天地——我连续几个月以来每天读、听、说的东西。我已经习惯用这些古怪的新词汇,我一点都不觉得惊奇了。偶尔,周二的下午我会去法学院隔壁的汉密尔顿?德利的柜台找点吃的,我不会说“我想来点肉丸和一杯可乐”。我发现我在反刍法言法语“出于善良和价值考虑,菜单提供了充分的选择,我愿意购买,德利愿意卖给我三明治、五个全熟肉丸、六盎司的番茄酱、意大利干酪(德利刚获得许可证),这些食品被做成了新鲜的三明治卷,在最低230华氏度下加热,然后用不粘的锡纸包装,加上24盎司的碳酸可口可乐,统统放在密封箱中,可以供外卖消费。”
第三章 像律师一样思考(7)
从更基本的层面上说,法学院不仅仅是改变了我说话的方式——虽然我不时会冒出几个拉丁单词,也不仅仅是教会我准物权的司法性、合同的法律约束力,而是教我彻底改变了思维方式。
在前几天的合同法课上,作为表扬学生的一种方式,布绕夫教授这样评论:“是的!你没看到吗?你正变得堕落、乖戾,因为你掌握了我的精髓!”虽说这是句玩笑话,但也确实有几分真实。我们正变得愤世嫉俗、惯于怀疑,对一切都再三猜忌,对每句话都要剥离表层,看看有没有漏洞或隐藏陷阱。对每个词分析到底,不相信别人,变成别人都讨厌的人。的确,我们正学习像律师一样思考。
十一月初的一个晚上,我早早地从图书馆回来了,我在立体音响旁找鲍勃?马利的一张击打唱片,发现桌子上有瓶鲜花,然后看到乔笑逐颜开的脸。
“我找到工作了!”他大声宣布。
“我知道你会找到的——恭喜你!”之前乔干了几个月的临时工,那份工作不仅让他身心俱疲,也让我们的经济颇为吃紧,“真正的雇员了!我真为你骄傲!”我高呼,跳起来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
“噢,哪里,贝蒂。”他说,我跳得太用力了,差点把我们俩撞翻。“虽然比大部分临时工作多不了多少钱,但这是一次伟大的职业变迁。会有好处的,嘿,不用再乘公交上下班了。”
“你的具体头衔是什么?”我问。
“发展伙伴。”
“发展伙伴,听起来真专业!乔,真是太棒了。赶紧换衣服——我们应该出去庆祝一下。”
乔在哥伦比亚商学院找到了一份融资的工作,离我们的公寓只有两个街区。虽然收入不算太高,但是个好工作,一个正走向职业发展道路的工作。庆祝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正准备出门。
一个小时后,我们还在A大街上闲逛,我想去别致东村餐厅,这样的餐厅对于我们两个从中西部过来的穷鬼来说,平时是想都不敢想的。十五分钟后,我终于找到了——外面没有显著招牌,只有一个大写字母A挂在前门。女老板从头到脚都是黑色,领着我们穿过拥挤的人群,到达后面的一条沙发桌前。座位用帷幔与其他位子隔开了,虽然只隔了大约三英寸。
既然是为乔庆祝,理所当然先看菜单,点些平时难得享受的美味,像山羊奶酪、香槟、沙拉、酸酱之类的。可是我在干什么呢?我从钱包里找出刚才保存大衣时服务员给的小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