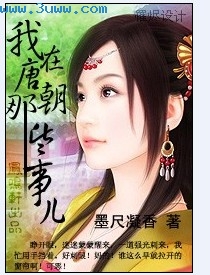我在京都当艺伎:一个美国女学者的花街生活-第1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的丈夫。无论如何,在日本人看来,为了营造愉快的宴会氛围,觥筹交错的饮酒方式与酒品本身同样重要。
日本人认为鸡尾酒会恰恰表明了美国人的内在性格。{61}参加鸡尾酒会就意味着显露自己对某种酒品的个人喜好;全部食物都一次性端上来,不会专门送到某个人身边,更不会帮某个人单独斟酒;每个人都只顾自己喝自己的,不管其他客人。当宴会上的每一个人都握着自己的酒杯时,感觉就如同一个个自我封闭的个体,而简单的碰杯根本不足以融化彼此之间的坚冰。只有当酒精的作用上来之后,大家才有可能跨越交流屏障。日本人对于这种交际方式是没有办法满意的,所以站着进行的男女混合鸡尾酒会在日本一直流行不起来。
我在京都以艺伎身份参加了半年座敷之后,遇到一个偶然的机会,到东京一个美国朋友的父母家里住了几天。由于我已经习惯于做一疑了,所以坐在椅子上、说着英语都让我感觉有点怪异。有天晚上,朋友的父母邀请三对美国夫妇到家里开鸡尾酒会,我也参加了。经过日本文化熏陶以后,我确实也对这个酒会感觉很奇怪。
H先生为大家调好了酒,并且在桌上摆了一圈,充分履行了他作为主人应尽的义务。可是根据日本人的观点,这样一个有地位的男人做这种事情显得有些滑稽;因为在日本人的宴会上,斟酒的工作是完全由艺伎来承担的。H太太的表现属于非常理想的女主人形象,她对朋友们笑脸相迎,眼神里流露出她的真心诚意。但是由于在客人到达之前,她跟我说了不少客人的坏话,所以这个形象在我心里就大打了折扣。
艺伎们在客人到达的前后表现也不一样,但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个艺伎会在尖酸的批评之后,马上又奉上甜蜜的职业微笑。这个鸡尾酒会在客人们的极度陶醉中落幕,女人们互相亲吻对方的脸颊,男人们互相诚挚地握手,男人和女人之间还有恋恋不舍的真情拥抱。再一次,我在自己国家的文化背景中,感觉自己像一个陌生人。在艺伎宴会上,虽然也会发生大量的身体触碰,可是日本人从来不会以这样的方式进行彼此的身体接触,尤其是在说再见的时候,大家会全都退回原位,恭敬而正式。也许正是因为在美国的鸡尾酒会上,只有结束的时候身体接触才被允许,所以大家就把这一机会发挥到极致了吧。
真心与表面
要想在社会当中左右逢源,常常需要我们隐藏自己的真实意图,这种情况在日本和在美国都存在。虽然这两种文化都承认在真实意图与表面态度之间有巨大的鸿沟,但是对这种鸿沟的反应却不太一样。
日本人将人类在社会中这种进退两难的局面称为“本音VS建前”,也就是真实感受与社会所需表现的对抗,而且他们认为这两者的分裂是社会生活的必然产物。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在一部电影中,一位承受着丧子之痛的母亲,依旧端正僵直地坐着,和儿子生前的老师进行交谈。所有的日本人都既同情又崇敬这位母亲,因为她没有被灾难打垮,没有将真实的感情倾泻而出。观众会格外敏锐地体会到母亲的心境,因为他们自己就常常处于类似的情境中。日本人认为某些表面态度是社会的一种需要,这根本和虚伪扯不上什么关系。这是帮助人们在社会中生活的一种方式,考虑到社会和其他人,真实感受不应该时时挂在脸上。
但是从美国人的观点来看,这种两难的困境往往会招致人们的猜疑,他们倾向于认为真心与表面之间的差异意味着欺骗,特别是如果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太大的话,人们更会将之视为奸诈的表现。H太太的客人们如果亲耳听到那些诋毁的话,他们一定感到很伤心——或者他们实际上也对H太太颇有微词。尽管现实政治迫使人们不得不持有这种两面性,但承认这一事实总是让美国人不太舒服。这也就是美国人对艺伎抱怀疑态度的原因所在。
“你怎么能在那么虚假的谄媚中泰然自若呢?”一位美国妻子刚和丈夫及其日本同事参加了一个艺伎宴会,一回到家,就迫不及待地这样质问丈夫。美国女人会认为艺伎们蜂拥在自己丈夫的周围,是应该受到谴责的行为。她们一定不是出于真心而那么做,女人心想。其实,艺伎的这种行为根本无关虚伪,而只是为了社会和本身职业的需要,但这一点对这位妻子来说却很难接受。在美国客人离去以后,艺伎们迷惑地问我,为什么那些外国女人的目光都像刀子似的飞过来,这让她们很不舒服,因为日本人的妻子是不会做出这样的反应的。我想,这种限于语言障碍而做出的无声的谴责,就是因为美国人对真心与表面的差距有着本能的敌对情绪。
非正式座敷(1)
有些客人就像一双合脚的鞋子一般令人舒服,例如佐藤先生。这位先生是先斗町十年的老顾客了,他还和其他先斗町的本地人一起上小歌课程,这儿所有的艺伎都很喜欢他。佐藤先生是那种不需要艺伎装腔作势的客人,在他面前,艺伎们可以坦白地说任何想说的话。有些艺伎称呼熟悉的客人做“哥哥”,如果年纪比较大就称“爸爸”,当然这些称呼都带了一点调笑的色彩。不过,艺伎们确实把佐藤先生当哥哥来对待,而且决不会在他面前卖弄风情。
像其他先斗町的艺伎一样,我也和佐藤先生有着这种亲切的关系。由于我们是小歌课程班的同学,所以佐藤先生见证了我在小歌演唱上的艰难起步。他常常用赞扬来鼓励我,还把自己研习多年得来的技巧和经验传授给我。很多中年商人学习小歌只是为了修饰自己作为艺术鉴赏行家的形象,但佐藤先生不一样,他是发自内心地喜欢这门艺术。有一次他请我出去吃晚餐,结果我们聊的全都是关于小歌的话题。
那天我们用餐的饭店也是由小歌课程班的一位男同学经营的,起初这是一家茶屋,当他从母亲那里继承下这份家业之后,就在妻子的帮助下把茶屋改造为一家饭店了。十年之前,他就清醒地意识到,先斗町不可能负担得起这么多家茶屋了,而他家这栋倚靠着鸭川河的建筑地理优势十分明显,如果改造为一家更多元化的门店,生意应该会更不错。不过,这家名叫珍酒屋的饭店,依然保留了不少旧式茶屋的风味。在先斗町,并非所有的旧式茶屋都能完成这么漂亮的转型。在珍酒屋旁边的那家山富屋,现在就变成了一个聒噪的家常饭馆。其实这家店地理位置也不错,但里面的榻榻米都磨旧了,让人很难想起它从前那高雅精致的模样。还有一些茶屋干脆就直接拆掉了,取而代之的是新式的漂亮酒吧。
当我们在珍酒屋吃过晚饭后,佐藤先生提议到凝香茶屋去坐坐,于是我们给凝香打了电话,然后慢慢地溜达过去。凝香穿着宽大的棉质上衣和裙子在玄关迎接我们,从她的装扮一望而知,今晚的座敷是纯粹的非正式座敷。凝香在厨房里搜寻可以用来下酒的小吃,但是找来找去也只有一些干沙丁鱼能够烤着吃一吃。不过,她也知道,我们到这里来主要是想让她作陪,而不是为了美味的食物或者漂亮的装饰。
这个座敷真像一曲蓝调音乐。凝香在唱歌方面是主攻清元节的,那些比较有鉴赏力的人都说,凝香在唱小歌的时候都带有一股清元节的风味。这就像歌剧演员的嗓子唱民谣,自然地散发着一种独特的魅力。
凝香叫来数惠——一个年纪比较大、专攻三味线的艺伎,参加我们的聚会。数惠在三味线上的造诣是惊人的,当我用三味线演奏完所有我知道的曲目后,数惠把三味线拿过去接着往下弹,简直没有一首曲子她不熟悉的。在演奏的间隙,佐藤先生问我的年龄,我告诉他我是属虎的。“我也是属虎的,”数惠在一旁说道。我算了一下,数惠应该是六十一岁。一般来说,年纪越大的艺伎,就越坦白直言,数惠也不例外。
数惠放下三味线,佐藤先生帮她倒了一杯啤酒,然后她就开始谈论男人了。凝香和我也加入到讨论中,几乎忘记旁边的佐藤先生也在我们谈论对象的范围内。佐藤先生在一边好奇地听着,或许还带有些微的惊讶。
“我觉得现在的生活前所未有的好,”数惠声称,“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再也没有任何旦那来烦我了。在我可以自主选择旦那之后,我发现把自己和一个男人绑在一起真是一点好处都没有——佐藤先生,请您不要介意。”
凝香对数惠的话表示赞同,“一个女人一生中最失败的交易就是让自己变成某个人的妻子,”她补充道:“因为妻子要替丈夫收拾一切烂摊子,而且她在家庭中没有力量,也没有经济基础。男人可以有妻子和情妇,甚至还有女朋友,但是女人呢?几乎不可能。这种情形是完全不公平的——我也得请您原谅,佐藤先生。”
佐藤先生没有说一句话。从这里我们也能感觉到先斗町的女人们跟他的关系有多么随意,所以才能够在他面前这样畅所欲言。不过,尽管我们的谈论并没有针对他个人,他仍然渐渐显示出了一些不安。
“如果有来生,我要么选择做男人要么选择做艺伎,”数惠说道:“只有这两种人才有自由。”“你算是抓到重点了,”凝香点点头,“在日本做一个妻子太痛苦了。美智子说,如果丈夫们是和艺伎在一起座敷,而不是和舞女或者秘书鬼混的话,他们的妻子内心会觉得自在得多。不过我想,要是一个男人找了情妇,就算这个情妇是艺伎,他的妻子应该也会相当烦恼吧。”
数惠对这个话题越来越感兴趣了,“即使在艺术这个领域,占据顶尖位置的人总是男人。就拿三味线来说,不管一个女人在这方面达到多高的水平,她也永远不能成为这个门类的顶尖人物。”“你还想指望什么呢?”凝香说道:“所有这些事情都是日本社会的一面镜子。”我忍不住问道:“那么花柳界作为女人的地盘,女人在艺伎圈就一定能获得比较高的地位吗?”“这是千真万确的,”凝香立即回答,不过随后她又补充道:“但是这样也远远不足以抵消其他领域中对女人的不公。”佐藤先生这个时候也开口了,我们可以把他的话当作是一种称赞,“就说三叶屋的老板娘吧——如果她是一个男人的话,她一定会成为大人物。也许是政治家,她该会是多么厉害的一位政治家呀。”为什么一个女人就不能赌上自己的一切,和其他男人一起在政治界一争高下呢?这个问题看来佐藤先生连想都没想过——可见日本男人的思维定势早已根深蒂固。
非正式座敷(2)
稍晚的时候,我和数惠还有佐藤先生告别了凝香,信步往祗园那边走去。这是六月初迷人的初夏夜晚,我们在四条桥上缓缓而行。佐藤先生对祗园不太熟悉,于是我建议大家去夏四子的酒吧。夏四子曾经是一位祗园艺伎,二十九岁的时候她退出了艺伎圈,成了这家小酒吧的妈妈桑。她的身材和我差不多,又高又瘦,曾经慷慨地送给了我几套和服。夏四子没有在酒吧里,但是酒吧的男招待盛情邀请我们进去坐坐。当我们到达那里时,是晚上十一点;离开的时候,已经凌晨两点了。数惠在整个过程中都很活跃,可是后来却渐渐有些接不上话,于是我发现,原来她的眼皮都在打架了。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