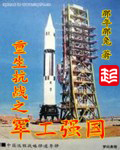秘密战-第1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廖休把俩人挨个儿瞅了瞅,然后来回踱着,又停在地中间,叹口气说:
“算了吧,算了吧!生米已经做成熟饭了嘛!能让他再把刘芳芳扔了吗?她不已经……只好委屈你吧!郭中堂同志弃妻再娶,是不道德的,我们共产党八路军也是不允许这样做的。我们批评教育他,行了吧?再说,弃妻再娶,这是他来我们根据地以前的事,那时他还是个老百姓嘛,而且是敌占区的老百姓嘛!总不能拿一个共产党员、八路军战士的标准去衡量他,要求他吧?况且,这也是战争造成的离散聚合!郭中堂同志来根据地以后,参加了革命工作,表现还是很好的嘛!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应该历史地、唯物地、全面地看问题。看在抗日的分儿上,看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分儿上,你就原谅了他吧,啊?”
秘密战 第八章(4)
这番话,说得女人消了大半火气。善于宣传鼓动的政治部副主任,说话流利、清楚,是他的一大特点。不管在什么场合,什么时候,他说出的话,总像在心里想了好几个晚上,在嘴边上堆放了好多天,就等着张嘴往外吐了。他说快了,你耳朵要是再一恍惚,仿佛只听到“噔噔,噔噔”的声音。
郭中堂坐在炕沿上,垂着头,鼻涕一把泪一把的,一边抽泣,一边说:
“,这年头,兵荒马乱,鬼子杀,飞机炸的。我一离家,天南海北的就是两年,谁知谁咋的啦?你不知我死,我不知你活的!谁能空守谁一辈子呢?”郭中堂一脸难过、悔恨而又无可奈何的样子,一边丧声丧气地说着,一边翻着眼皮子,朝那女人和廖休瞅几眼,“刚才,廖副主任批评得非常对,我弃妻再娶是不道德的!可是……可是刘芳芳思想进步,革命爱国,我和她情投意合……”
一句话不对,那女人便竖起吊梢眉,瞪起眼珠子,用巴掌一拍大腿,指着郭中堂的鼻子,仰脖子骂道:
“噢,就她进步,就她革命爱国?放你娘的狗屁去吧!我落后,我当汉奸了吗?喜新厌旧,没有心肝的东西,真想再扇你两撇子!”
郭中堂好像真叫她给镇唬住了,哭丧着脸,低声下气地说:
“你看你,你看你,话怎么能这么说呢?谁说你不进步,不爱国了?……啥当汉奸不当汉奸呢,这哪儿跟哪儿呀?”待一会儿,他朝那女人斜了一眼,撇了撇嘴,鼻子里哼了两声说,“这是根据地,你黄风雾罩地瞎折腾什么呀!枉口拔舌,胡诌白咧,骂我就罢了,你别涉及人家刘芳芳同志,咱俩的事,她不知道!”
“扯你娘的臊!”女人一听又火了,“噢,就那个小婊子好?那个小婊子香?她的脚指丫缝都是香的!她是你的亲娘热奶奶,含着怕化了,拿着怕碰了,你刻个牌位把她供起来吧!你这个不是人的东西啊!抛下俺们一家,老的老,小的小,我的天啊!”那女人说到伤心气愤时,两手拍着大腿又哭又数落:
“可怜俺那大宝啊!为了你爹,你叫鬼子刺刀头子给挑了,你爹又把你妈丢下说了小哇!大宝啊,你妈的命苦,你妈是中药店的揩台布,揩来揩去都是个苦啊!……”
那郭中堂听到大宝给鬼子刺刀挑了,一高蹿起来,机敏的年轻人涨红了黝黑的窄脸,捶胸跺脚儿地嚷道:
“小日本鬼子,我操你八辈祖宗!你杀了我的大宝,我郭中堂今生今世和你们干到底了。大宝娘,鬼子为啥杀害大宝呢?”
女人从怀里掏出一张陪关鬼子捉拿通缉郭中堂的布告,放到炕沿边,用巴掌使劲拍了两下:“你干的好事,自个儿看去吧。”郭中堂抖落开那张布告,那上面写的是日本人怎么交给郭中堂二十万金票,怎样叫他给日本人买羊毛,他怎样携款潜逃。末了,女人说:“日本人抓不到郭中堂,就到郭家庄把俺娘儿俩抓去吊打拷问,俺们娘儿俩咋知道你在外头闯了祸呢?咋知道你跑哪儿去了呢?气得鬼子把大宝给挑了!”
廖休对于郭中堂的抗日爱国精神深表钦佩,对于他因此遭遇到的不幸,也深表同情。副主任安慰了郭的前妻,又派人把村妇救会主任找来,让她给那女人找个可靠的老乡家,安排吃住。
当屋里只剩下廖休和郭中堂俩人的时候,廖休正要再批评教育郭中堂几句,就听大门外,又是吵,又是骂,又是打,又是闹,乱吵吵的简直快成一锅粥了。
秘密战 第八章(5)
不一会儿,通信员来向廖休报告说:那女人找到刘芳芳,先是臭骂了一顿,然后又揪住刘芳芳的头发,不管头脸儿的“噼里啪啦”地好个打,还揪着头发往墙上撞哩!真是的,老娘们打架就是好揪头发。揪住头发,凭你是个大男子汉,也甭想拉开架。这工夫正打得凶呢,快去吧!
“!”支队领导人心烦地叹了口气,拔腿就往外走,到了风门口,又折回来,对郭中堂说:
“今天不早了,就不要让你的前妻走了。晚饭以后,你要单独和她谈谈,好好劝劝她。这样下去,对共产党八路军影响多不好!对你这个刚刚到抗日根据地来参加革命的人,影响多不好!劝好了,你就是为后勤支队立了一大功!明天我给她开个路条,派人送她下山。”
刘芳芳的脸皮儿,像窗户纸一样薄。她哪儿受得了这般辱骂?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村里的民兵、儿童团、妇女、老人、孩子,还有医院的伤号、游击队的男女队员……刘芳芳挨了打,受了辱。再说,那叫啥打法儿,啥骂法儿呀!完全是一个发了疯的泼妇的厮打和辱骂。多难听、多寒碜人的话呀!临被拉开,那女人还挣扎着,扭着头,伸着脖子喊叫着,说刘芳芳专会偷人家汉子,偷了一打还挂零。听听,这叫啥话?!薄脸皮儿的女文工团员,哪儿受得住这个呀!
当这场厮打辱骂被劝拉开以后,天已经黑了。
刘芳芳回到屋里,把壁龛里的小油灯点上。她一下伏在被褥上,哭泣起来。
她上了炕,拉开被,想和衣躺下。就在她抖开被褥的时候,看见了她每天都夹在被里的蓝底白色印花土布小包。她打开包,拿出衣裳底下的一块小圆镜。
这是有一年反扫荡胜利后,刘芳芳的男朋友张云清送给她的。
记得那天,她们军区文工团赶来慰问演出。演员们正在小学校教室里化妆,忙忙乱乱。敌工科那个长脸形的小伙子,拨开围在门口的一大群孩子,走进去,找到刘芳芳,掏出一个小圆镜交给她说:
“芳芳,得来的,送给你。”
刘芳芳高兴地翻来覆去地抚摸着这件珍缺的礼物,咧着小嘴说:
“你真好,你真好!正缺它呢!你看,小镜背面还有只大公鸡呀!我老早就想有这么一个,就是没有,这回可好了。”她看看周围都在忙着化妆,没有人注意他们,就把脸凑到他的耳根子边,悄悄地说:“你大概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吧?要不,你咋知道我就想这样东西呢?嗯,是不云清?”
长脸形的英俊小伙子,憨实地笑着说:
“县委书记大老乔,听说我有一个漂亮的爱人在文工团,这回也来慰问演出,让我从缴获堆儿里挑样东西送给你。我琢磨,你最喜欢啥呢?我就变成了一个小虫子,钻进铁扇公主的肚子里,探听出来了!哈……”
刘芳芳快活地跟他一块儿笑了一阵子,然后娇嗔地故意说:
“去去去!说你好,你就上脸!谁爱你呀,没羞!”她鼓起小嘴,用指头在脸蛋儿上划一下,“没羞!我要叫你当一辈子小光棍儿,等你变成一个长白胡子的小老头儿,我才嫁给你呢!等着吧,小坏人儿,熬熬你的性儿!”
刘芳芳的漂亮面容,现在变得特别苍白和忧愁。她的神情是悲伤的,她的动作是迟缓的。她收拾好白色印花的蓝布小包,躺下了。
又过了一会儿,郭中堂回到屋里,看见刘芳芳脸冲墙,下身搭一条雪青色的薄被,和衣躺在炕梢。他爬上炕,伸手去扳刘芳芳的肩头。刘芳芳一甩胳膊,没理他。他三番五次好半天,她始终没理他。还有啥好说的呢!末了,郭中堂叹口气,用非常诚恳的语调说:
“她那样对待你,我也是心疼。可我当时有啥办法呢?这事儿,都怨我不好。当初,都因为我太喜爱你了,没敢对你实说,说了怕你不跟我。芳芳,都因为我太爱你了,要不是因为爱你,我能得罪汉奸侦缉队的人吗?要不是因为爱你,我能豁出生意老本、豁出我的身家性命,跑到‘鲁白公馆’,把你保释出来吗?芳芳,你别那么狠心不理我好不好?你知道,陪关的鬼子还在通缉我呢!”郭中堂说着,把那个女人带来的布告拿出来,要让刘芳芳看,刘芳芳又一甩胳膊,不看,不理。
“芳芳,”郭中堂难过地哭了,“你不理我,你知道我心里多难受?你还不如打我一顿呢!你打我吧,你把气都撒到我身上吧,谁叫我太爱你了呢!”黝黑窄脸的青年,哭得真是伤心。
上当受骗的女人,还是没理他。
郭中堂扣过身,两只胳膊把身子支起来,贴着刘芳芳的耳朵边,低声细语地说:
“我都和她说好了,她明天就离开白马村,回娘家去。以后,我身边要是宽裕呢,就给她两个,接济接济,没有呢,也就算了。往后,还不是咱俩一块儿过?咱俩是谁跟谁呀?不是两口子嘛!两口子不互相担待点儿,谁替咱担待?连廖副主任,今儿个下晚,还鼓励了我老半天,叫我好好干,争取火线参加共产党哩!往后,我好好进步,狠狠打鬼子,对你一百一的忠心。要不,来世变牛变马也只长一只耳朵,三条腿儿,火车轧死,枪子儿崩死,不得好死!芳芳,你就饶过我这一回吧,看在咱们患难夫妻的分儿上,看在咱们还没有出生的孩子分儿上,原谅我吧,好人!”
郭中堂嘴都说得冒了白沫子,嗓子里都起火冒烟儿了,刘芳芳仍旧没理他。她太伤心了,她太屈辱了,她太痛苦了。
实在被他缠磨不过,刘芳芳便索性下了炕,离开屋。
她独自一个人走出村来,坐在村西头的小崖头边上,哭了一场又一场。手绢全湿透了,连衣襟也让泪水湿了一大片。
星星一个一个全出来了。
月亮升起,又偏西。
刘芳芳还是一个人坐在崖头边上哭泣。不幸的泪水,屈辱的泪水,伤心的泪水,交混在一起,滴落在崖头底下,滴落在呜咽抽泣的大雁河里。她正陷在极度悲哀的深渊里。她想起了今年春天那次使她终生感到悔恨的陪关之行……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秘密战 第九章(1)
陪关。
在初春漆黑的夜晚,有一个女人,警惕地在黑洞洞的胡同里,顺着墙根儿,轻手轻脚地朝前走着。不一会儿,女人停在一个小街门口。她用窥视的眼睛,在黑夜里前后搜索了好长一阵子,觉得没有人跟踪她,才用事先准备好的半截小钢锯磨成的小刀,轻轻拨动木板街门的门闩儿。门拨开了,她又左右看看,然后敏捷地侧身闪进小院里,闩上门。
她倚在门口,用力观察小院里的各个角落和门窗。当她判断出这个小院的住户,仍然是原来的人家,没有一丝可疑的地方时,才挨身走到窗下,轻轻地敲着窗。屋里没有人应,她又敲。
大约有半顿饭的工夫,屋里终于传出一个微弱的老妇人的声音:
“谁呀?”
“我,芳芳!”敲窗女人回答。
“谁?”
“芳芳……”
屋里接着传出一声惊喜的感叹:
“啊……是……芳芳?!”
“是我。妈,快开门!”
门开了。
芳芳一下扑到母亲的怀里,不住声地叫着:
“妈妈!妈妈!……”
久别重逢的母女俩,紧紧依偎在一起。母亲的手,亲切爱抚着女儿的短发,热辣辣的泪珠子,滴落在女儿的脸上。
“妈,哭啥?”
“不!妈没哭。妈见到你,心里乐得慌,悬在半空的心,总算落了地。”
妈妈高兴得连抚摸芳芳头发的手也在颤抖。
她爬上炕,挂上窗帘,拉开灯,坐在炕沿上,一手拉住女儿的手,一手摸着女儿的脸,歪着老脸,左看右瞧:“让妈好好看看你,胖了还是瘦了?山里,苦不苦?”
芳芳赶忙回答说:
“不苦不苦!妈,不苦!”
虽然在白色恐怖包围之中,但是毕竟是到了自己的家,芳芳刚才闯城门口,一路上的紧张情绪,以及紧张之中略微带有的恐惧成分,完全消失了。兴奋涨红了姑娘的脸。
“妈,根据地就是苦,也是甜!我喜欢。那里抗日,还有那里的人,我都喜欢!……”芳芳说到这里,脸不觉红了一下,又扑到母亲的怀里。
母亲无限爱怜地摸着女儿丰圆的脊背和柔软的黑发,脸上却现出困惑的神色,说:
“芳芳,我的孩儿,那,那你咋回来了呢?……根据地在大山里头,离这几百里,路上担惊受怕的,你是想妈了?”
芳芳直起身子,愣愣怔怔地问道:
“唉?不是您带信让我回来的吗?”
母亲更加纳闷儿:
“我带信儿?”
“是啊!不是说,您病得厉害,叫我回来看你的吗?”
“啊……我是病得不轻。”
“好些了吗?”
“不见好,心口窝儿老是堵得慌。”芳芳妈说,“可我没给你捎信去呀。”她说着,这才注意到女儿是穿了一身便装来家的:山区常见的青裤蓝褂,蓝褂大襟下边露出寸把宽的花边小袄。这是拄天山地区妇女常见的打扮。
“妈,反正是个好心人干的。”天真无邪的姑娘,带着叫人喜爱的热情说,“他看您病得不轻,可怜您,就捎个信儿,让我回来看您,就这!”
“……会是谁呢?”妈妈自语。
突然间,一阵撕心裂胆的猛烈砸门声,好像一阵霹雳从天而降,把小屋里的母女俩惊吓得紧紧拥抱在一起,心高高地提到嗓子眼儿,仿佛喉头堵塞了一般,连呼吸也感到十分困难。
小街门外,胡同里,一辆黑色囚车的前后还停放着四五辆摩托车,车上坐着戴钢盔的鬼子兵。十几个荷枪实弹的伪军,堵在胡同口的两边。
侦缉队队长何兰亭带着几个汉奸特务和日本宪兵,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