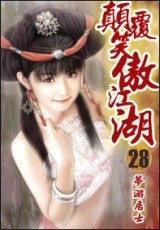笑傲之犹记小时-第3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他竟然活着……他果然还活着……”风清扬苦笑一声,拔剑出鞘,“那我这些年又是在干什么?!”
青白的剑气映在他的脸上,竟去了几分金纸颜色,让他显得与之前判若两人,曾经笑傲江湖的华山剑宗第一人确乎又重归于世了!
“既然他还活着,那末——”风清扬冲低着头不知神色如何的东方不败道,“我的那什么不再当真动手的狗屁誓言,也无甚意思了。”
甘草点点头,手一挥,身后那十几个属下也都架起了剑与弩,只是碍着山道狭小,有几人不得已列在山道的另一面伺机而动。
“他真受伤了……?”
东方不败忽然抬起头,看向愤愤的阿堂,用一种极其茫然的口吻问着:
“他当真……伤得……那样重……?”
“骗你做甚!”
“怎么可能……”东方不败摇了摇头,不信道,“我都打不过他,谁能伤得了他?”
“……那可说不准,”风清扬看着东方不败那般失魂落魄的模样,忽然明白了什么,收剑还鞘,叹息道,“若真的与我想的一样,倒也说得通了。”
“……什么?”东方不败蓦地转向风清扬,眼睛通红,却没了一丝杀气——他的杀气,竟在方才阿堂和半夏那番颠来倒去的话中,崩坍得不剩分毫。
“半夏刚才说,你用的是《北冥神功》……”风清扬缓缓地说道,“如果我想的没错,那的确就是北冥神功了。
“——虽然想不通为什么……
“——但是,十有,我那笨师弟的内力……
“——是被他自己转嫁到了你的身上!”
……
这一番话,说得虽然轻,但是却又无比的重,砸在诸人心上,俱是一道惊雷。
“公子怎么可能把内力传给魔教的教主?!”
半夏张了张口,想要说“不可能”三字,却又说不出来——真要论起来,没有人比她更清楚那两人之间的渊源与纠葛。可能——或者也是有可能的……
她与甘草对视了一眼,俱看到了彼此眼中的震惊……
“……”东方不败嘴唇颤抖了一下,夸张地笑起来,“哈,风清扬,你傻了么?他费尽心机要铲除我教……没理由、这么做……”
“你就是魔教的教主?!”
阿堂瞪大了眼睛看了看面色晦明不定的东方不败,又看了看沉吟不语的半夏,不安地扯了扯她的衣袖,小声道:“义姐?他真的就是那个东方不败……”
“怎么?”
“莫七……茯苓说……当年——”阿堂向面色苍白的东方不败投去复杂一眼,“当年太傅就是因为这个人,才迟迟不愿回朝……真是这样?”
半夏与东方不败俱是一愣。
东方不败听得阿堂此言,第一个念头便是“不可能”三字。
然而半夏却想起了自己与公子在城门外苦等的那一昼一夜——她知道,那时候,公子做的是归隐的准备……只是,后来,那个人没有来而已。
良久,她才哆嗦着嘴唇,攥着袖口点了点头。
“真的是因为你啊!”阿堂扶着甘草,站直了身子,“你口口声声说太傅要铲除你们魔教!那你倒是说说,太傅这些年对你们做了什么?他已经十年不问江湖事了啊!”
东方不败的心,忽然有些慌了——他知道,自己一定是遗落了什么东西,他也知道,这些人说的不可能都是谎言……然而,执念已深,怨缘已久,怎可能被旁人这样轻易地祓除?!
他体内的葵花阳炎又转了起来,与那另一股气劲冲撞在一起,震得经脉生疼,却奇异地让他冷静了下来。
只见他轻笑了一声,斜挑眉梢,环视了一圈对面那些或迷茫或愤怒或了悟的面孔,斜睨着风清扬手中的佩剑,缓声道:“若他果真不问江湖事,何必去找我教的前教主,何必大费周折来寻风清扬呢?”
“这……”半夏等人不由语塞——她们怎么能知道、东方不败怎么能知道——那个人所作的这一切,不过是想劝服风清扬离开华山,不给他传授令狐冲“独孤九剑”之机,以改东方不败将死之局?!
没有一个人知道乔易的想法。
他藏得太深了。
“你何不自己去问他呢?”
风清扬忽然打破了剑拔弩张的沉寂,“无论是你们之间的事儿,还是《北冥神功》——你为什么不自己去问他呢?”
“……问‘他’?”
东方不败心脏猛然一跳,撞得他前肋生疼。
他忽然发觉自己的手指竟不自觉地抖动起来——
你在动摇。
一个冷冰冰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
东方不败死死地攥紧拳头,将自己的颤抖捏在手心、缩在袖里。
他缓缓地抬起头,一步一步地从风清扬、阿堂、半夏和甘草的身边走过。他嘴角牵起一个看起来一点也不勉强的笑,掷地有声地说道:
“这辈子,我东方不败都不想再见到他。”
山壁回响间,他没听到,在弯道的另一面,有个人轻轻地叹息了一声。
作者有话要说:今后也请大家多多支持!
作揖作揖~
——————
预告:
下章是个过渡,会比较短。
剧情从下下章开始转向以京城为核心的新阶段。
以上!
正文 章五十 争如不见
更新时间:2012…1…18 1:12:18 本章字数:6486
“今天本座没兴致陪尔等玩耍了。”东方不败噙着冷笑,头也不回地从神情紧张的诸人中间穿过,“半夏姑娘,《北冥神功》你回去可得备好了。”
“……”
半夏咬着唇,正想说些什么,却被甘草攥住了胳膊,“别说话!莫要横生枝节!”
其实,不管他们此时再说什么,东方不败也听不见了——
他感觉自己仿佛身处黑暗之中,前面只有一点摇曳的灯火,那灯火时而清明辉耀如星如辰,时而又晦暗幽明若狼鬼之目。
配着那黑暗的,是不相称的嘈杂——无数细小的声音在他耳边各说各话。
——山风的呼啸也好、半夏和甘草的低语也好、阿堂的抱怨也好、美好的或是残酷的回忆也好、他心中立场各异的自言自语也好——都化作了嘈杂的噪音,干扰着他本就混沌而不堪重负的思绪……
东方不败发觉,他是真的动摇了。有一种不可抑制的情绪,猛叩着他的心扉。
——十年前被他扼死的那个“东方柏”,仿佛又因为那些人虚假的话而燃起了浅薄的希望,确乎不再甘愿只做为一个苍白的记忆存在着……
十年前的那个“东方柏”软弱的疑问,又一次浮上心头——
若是他存心害我,又何必救我?又何必……
‘……他救你,是因为你是东方柏。他害我,是因为我是东方不败!’十年前,在玄武门外的长亭,捂着胸口血洞跪倒在地上的东方不败,就是这样一边说着,一边掐死了自己的另一半。
他说,自此,再没有东方柏了。
他说,自此,东方不败就只是东方不败。
……
‘公子不眠不休等了你一昼一夜,你倒好,为什么派杨莲亭那贱人来?!为什么要让公子失望伤心?!’
‘大人自从十年前与此人一战之后,就一直没能痊愈,后来又中了宵小的寒毒……前不久又操劳国事染上了风寒,现在病重得根本下不了床,只能在府中修养……’
‘若非是你……大人怎么可能一夜白头、差点死在半夏眼前!’
耳边嘈杂的话语渐渐明晰起来,传到被他锁在角落的东方柏的耳里,‘她说的是真的么?’他问。
——不知道。
‘那如果她说的‘是’真的呢?如果你我的记忆没错,那一定其他的地方错了。风清扬说的对——得去见他。至少也要问清楚。’
——没必要。我,与你不同。自那一日起,我与他再无干系。十年前……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也不想知道。
‘你害怕什么?’东方柏嘲讽地笑着,‘你说我软弱……但其实你才是逃避的那一个罢?东方不败,你我原就是同一人!你把自己的爱恨一分为二,实在是太自私了。你是害怕真相并非如己所料,害怕这十年成了一场失败的笑话?还是害怕……他早就放下了,早就忘了你了?’
“怎么可能……”
‘是啊,‘我’才应该害怕……’东方柏叹息了一声,‘但是……今日既然知道了这些……东方不败啊,‘你’以为不弄明真相,‘我’还能如‘你’所愿地消失么?就算是为了干干脆脆地了结,‘你’也该去见他。不管结果如何,‘你’都不会放在心上不是么?如若不然,你便早早承认‘东方柏’罢……哈,不管你怎么做,你都输了……’
“够了。”
东方不败闭了闭眼,把那声音强自按回角落。
他袖中的十指攥得泛青发白,确乎有冰裂的声音循着经脉从心底蔓上指尖——又疼又冷。
……
不必甘草发话,在东方不败的威压下,山道上候着的侍卫齐齐地往山壁或崖边退了一步,自觉地为他让路。
东方不败走得不快也不慢,宽大的红色纱衣在山风的吹荡下,显出些目空一切的张扬。
转过弯角,山路更加陡峭狭窄,勉强可通一人。
“让开。”东方不败冷冷地斜睨了一眼那个恰恰站在路中的人,面无表情地说道。
从谷底扶摇而上的风终于抵达了悬崖,抚弄着东方不败的红衣黑发,也吹起山径中间那人灰扑扑的衣角还有他鬓边灰白的垂丝。
他与任何一个侍卫都不同。
他更像是一个趁兴登临的文人。
——他穿着文人的长衫,纵使风尘仆仆,束在发冠里的灰白色发丝却分毫不乱。他身上既也没有弩,又没有刀剑,只是两手交握着放在袖中——就如同定州城大学堂前的孔子雕像一般,静静地立在那里,不言不语,平平无奇。
他看起来,就是那种随时可能从袖中怀里拿出本《诗经》或《大学》,侃侃而谈的那种渊博学士。
然而,无论他到底是谁,无论他是否与半夏等人有关,东方不败此时也没兴趣知道,“让开。”他又说道。语气带上了显见的不耐。
那人又沉默了一会儿,终于侧过身,伸手拨开山壁边斜生的松枝,退了一步。
——走过他的身边,东方不败才发觉,这人的身量竟然比他还要高——只不过是因为太瘦,所以才不显……
……
那人低垂着眉眼,仿佛正专注于袖口那因为奔波磨损而绽开的线头,从始至终,也没有与那袭张扬红衣的主人对视过一眼。直到那袭红云转过了下一个弯道,消失不见,他才轻轻地叹息了一声,抬起一双沉静如水的眼眸,对东方不败离去的方向投上深深一瞥……这辈子,都不想……再见么……
“大人?”
半夏走下山道,看见路中那人,不由轻呼了一声。
阿堂正被甘草搀着,一步一步往下挪着,听见半夏的轻呼不由撇开甘草的搀扶,不顾腿上的疼痛,连忙向那个人影奔去。
“太傅?!您怎么来了?”
那人缓缓收回凝寂的目光,转过身来,伸手从脸上揭下一层人皮面具,露出属于大明首辅乔易的那张温润如玉的脸来。
乔易没理阿堂,只是温和地说道,“半夏、甘草,辛苦了。”他,就如往常一般温雅,却不知为何,竟透着让人心头一紧的寂寂之感。
甘草强忍着心头的激动,单膝跪在三年未见的乔易面前,哽咽道:“大人!甘草未能看护好皇上,请受责罚!”
“是朕自作自受,拖累了太傅和你们。”朱祐樘像小孩一样,双手紧紧扯着乔易的衣袖,羞愧地低下头,“太傅,樘儿知错了……”
“知错了?”乔易看了他一眼,目光沉凝,带着种说不出的肃然严厉。
“知错了……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江湖险恶什么的,樘儿都明白了!”朱祐樘那满脸的油滑气在看到太傅的那一瞬间便全部抹去,竟然剩下一张正气凌然、痛心疾首的脸来……“不过,太傅您怎么会在这里?义姐说您病了……”
“我自然是骗他的!!但——看他那个无情模样,显然是十年来没有一丝愧疚!”半夏冷笑一声,纤纤玉手一翻,又摸了摸她的宝贝银链小弩,“不过,说起来,小樘你出走这么久,是不是也太过分了?”
朱祐樘见深受母后宠爱的义姐就要发作,连忙夸张地躲到乔易身后,“太傅!樘儿再也不敢了!”
“皮猴儿……”乔易摇着头按了按隐隐发痛的眉心,勉强让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回来。
他看了眼环抱着手走过来的风清扬,扯着嘴角笑了一笑,“师兄,别来无恙。”
“云三还活着?”风清扬木着脸,直截了当地问道,“这些年你都是知道的?”
“我本不想让你知道他还活着。他亦如此。”乔易点了点头,“时过境迁,他已非魔教教主,十长老业已……死在了璇玑洞——因那断龙石是我所设,所以,这件事,我本来多有愧疚,自然不希望你再与他刀剑相向。”
“那你为何现在又告诉我?”
“我只是想看看,这天命……究竟能不能改。”乔易喃喃自语着,苦笑道,“如何?他既然没死,你就没了理由把自己困在璇玑洞里与死人为伴。下山罢,师兄……你的身子也当调养了。”
“与其担心我,不如看好你自己。”风清扬撇了撇嘴,意味深长地看着乔易,“我看你与那个小教主之间确乎误会颇深。我打赌他八成会忍不住去京师寻你……你现在武功已废了泰半,若他一个激动要跟你动手——”
“……‘恩断义绝,只相为敌’——这是当年他托人带给我的话。”乔易淡淡一笑,竟是说不出的寂寞萧索,“方才你也听到了,他此生都不愿再见到我。不见我,要怎么杀我?”
“他啊,如今大约连恨我都不屑为之了。”乔易摇头叹息着,迈开下山的脚步,“我倒是希望能死在他的手里。”
“恩义也罢、恨也罢,岂是那么容易断绝的?”风清扬感慨地抚了抚手中长剑,“那个东方不败能登上魔教教主之位,必是个果决狠辣的人——然而他看上去却仍未释怀,提到你的时候,他甚至连杀心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