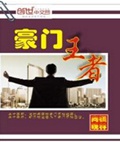所罗门王的宝藏-第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一样的流浪者震惊不已,如果还有人侵入他的领地的话。这件事情给了因寒冷和饥饿而奄奄一息的我们沉重地打击。
“我们走吧,”亨利爵士低声说,“我们把一个同伴送给他和他作伴。”他抬起霍屯督人文特沃格乐的尸体,放在老姆尸体旁边,然后弯下腰,扯断了老多姆脖子上的十字架的烂绳子。因为他的手指实在是太冷了,根本没有办法解开这个绳子。我相信他现在还留着这个十字架。我拿走了那支骨笔。我写这本书时,就把它放在面前,有时我还用它签名字。
之后,我们离开了两个人——那个在当时的年代富有声望的白人和可怜的文特沃格乐,把他们永远留在了永恒的白雪中。我们爬出洞穴,走到舒服的阳光下,继续我们的旅程。此时大家心中波涛汹涌,一直在想还有多少个小时我们也会像他们一样。
我们走了大约半英里,就到了高原边缘。由于晨雾缭绕,看不到下面有什么。然而,不久,较高的雾层似乎稀薄了一些,我们看清了脚下大约500码的地方,是一个长长的雪坡,尽头有一块绿草地,一条溪流从中奔流而过。还不止这些,溪流边,有一群大羚羊,或站或躺地沐浴在晨光下,大约有10至15只左右。由于距离较远,我们看不清是什么品种的羚羊。
。。
第七章 所罗门大道(2)
这一景象让我们感到一种莫名的快乐,只要我们能得到它,就会获得足够的食物了,但是问题是如何到它。这些羚羊离我们有600码,远在射程之外,我们的生命就看能不能得到一只羚羊了。
我们迅速而理智地讨论了一下如何捕猎这些动物,但最终我们还是很不情愿地放弃了。首先,风向不利。其次,我们要想猎到它们,必须穿过眩目的雪地,而且不论我们怎么小心,都会被它们察觉到。
“唉,我们必须得从这里试一下,”亨利爵士说,“夸特曼,用哪种枪好,连发步枪还是快枪?”
这里又有一个问题。我们有两支温切斯特步枪了,就是乌姆宝帕的枪和文特沃格乐使用的枪,当时也背在他身上,这种枪射程达1000码,快枪的射程有350码。不论使用哪种枪或多或少都要估摸着来射击。另外,如果击中了,快枪的子弹会剧烈膨胀,更有可能打死猎物,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但我决心冒一次险,使用快枪来射击。
“我每人瞄准前面的那只公羚羊。要好好地瞄准,肩膀往上一点儿,”我说,“乌姆宝帕,你来发令,我们一起开火。”
接着,大家停了一下,每个人都瞄准自己的猎物。当一个人知道自己的生命维系在这一枪上时,他十有###会这么做。
“开火!”乌姆宝帕用祖鲁语喊到,三支步枪几乎同时响起;一时间,我们面前形成了三股烟雾,寂静的雪地上响起了上百声回音。不久,烟雾消失了,露出——噢,太好了!——一只大公羚羊躺在地上,极度痛苦地猛烈地踢着。我们发出胜利的欢呼——我们得救了——不会被饿死了。尽管身体很虚弱,但我们还是冲上了中间的雪坡。十分钟后,动物的心脏和肝脏已经摆在我们面前了。现在又有一个新的困难,我们没有燃料,无法生火来烤它们。我们沮丧地互相看了看。
“快要饿死的人不应该空想,”古德说,“我们必须生吃。”
要想走出困境,别无选择。噬骨的饥饿让在平时看起来十分恶心的生肉竟然没有那么可怕了,因此我们把心脏和肝脏埋在一块雪下冷却一下,然后用溪流里的冷水洗了洗,贪婪地吃了下去。听起来十分可怕,但说实话,我从来没有尝过像生肉这么好吃的东西。一刻钟后,我们完全换了个人,又变得生龙活虎了,我们虚弱的脉搏再次强壮地跳动起来,血液在血管里也奔驰起来。但考虑到饥饿的胃吃得太饱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我们非常小心,没有多吃,只吃了一点就停下来,此时,我们仍然感到有点饿。
“感谢上帝!”亨利爵士说,“这些畜生救了我们的命。这是什么,夸特曼?”
我站起来,看了看这个羚羊,我也不特别确定这到底是什么。它有驴子那么大,长着大弯角。我以前从来没有看到过这种动物,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新品种。棕色皮肤,淡红的斑纹,厚厚的皮毛。后来,我发现当地人把这些公羊叫做“英客”。它们非常稀有,只有在高海拔的地方才能发现,而其它的动物在这样的海拔上根本无法生存。子弹正好射入了羚羊的肩上部,当然我们不知道是谁射中的。由于古德以前在射击长颈鹿时表现出了精准的枪法,我相信他暗地里把这功劳记到了自己名下,不过我们没有和他去争论。
刚才我们一直忙于填饱自己的肚子,没有时间去看看周围的情况。现在吃饱后,我们安排乌姆宝帕去割下最好的肉,尽可能带上,然后开始观察周围的情况。现在八点了,太阳升起来了,雾已经消散,因此我们能够看到前面的一切景象。我不知道如何用语言描述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壮观景色,以前从来没有看见过这种景象,我想将来也不会再看到。
在我们后面和上面,是高耸入云的示巴女王冰雪覆盖的乳峰;脚下,大约5000英尺的地方是层峦叠嶂的最美丽的原野;面前是茂密高大的森林,还有一条大河泛着银光蜿蜒其中;左边是一片辽阔无际的被远山环绕的肥美草原,上面有无数的猎物或牛群,距离太远了,我们无法看清到底是哪种动物;右边或多或少也有一些山,也就是说,单个单个的山从平地耸起,中间有一块块耕地,还有成群的圆顶小屋。面前的景色如诗如画,一条条河流像银蛇一样闪闪发光,就像阿尔卑斯山的峰顶狂雪乱舞、庄严肃穆,而在这一切之上,就是令人愉悦的灿烂阳光和大自然欢悦的气息。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七章 所罗门大道(3)
四处观望时,有两件奇怪的事情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一是我们面前的这个乡村肯定比我们穿过的沙漠至少高出5000英尺;二,所有的河流都从南往北流。我们惊奇地发现,脚下辽阔高原的南面一点水都没有,而在北面却有很多河流,都和一条大河汇合在一起,这条大河蜿蜒前行,远远超出了我们的视野。
我们坐了一会儿,默默地看着这片美丽的景色。不久,亨利爵士说话了。
“地图上是不是没有所罗门大道呀?”他说。
我点了点头,仍然眺望着远方的乡村。
“嗯,看,那里!”他指了指我右边。
于是,我和古德顺着他指的方向望了过去,那里,只见似乎有一条宽阔的公路向平原蜿蜒而去。一开始刚到平原时,我们并没有看到它。我们什么也没有说,至少说得不多,开始失去了惊奇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么奇怪的土地上发现这样一条罗马道路看上去特别不自然,不过我们接受了这个事实,这就是全部。
“嗯,”古德说,“如果我们从右边插过去,它离得一定很近,我们是不是现在就出发?”
这是一个合理的建议,我们在溪流里洗了洗脸和手,就行动起来。穿过大约一英里多左右的大石头,越过一块块雪地,最后突然走到了一个小高地顶上,我们发现那条路就在我们脚下。这条路是从坚硬的石头上开辟出来的宽阔大道,至少有50英尺宽,保存得非常完好,但是在我们后面往示巴女王山峰方向只有一百步远,路就消失了,整个山的表面到处都是一块块石头和雪堆。
“夸特曼,你看这是怎么回事?”亨利爵士问。
我摇了摇头,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我知道怎么回事!”古德说,“这条路无疑正好穿过另一边的山脉和沙漠,但是沙子把路覆盖了,在我们上方的路又被火山爆发形成的熔岩湮没了。”
这看上去是一个挺好的解释,至少,我们接受了这种解释,然后继续向山下走去。这证明了吃饱喝足走在宽阔的大道上下山和饥寒交迫爬雪山完全是两码事儿。实际上,回想起可怜的文特沃格乐的悲惨命运、回想起在那个阴冷的洞穴里与老多姆作伴的情况,我们现在感到很高兴,尽管前面还有许多未知的危险在等着我们。每走一英里,天气就暖和一点儿,气候也越来越温和,景色也越来越美丽。至于那条大道,尽管亨利爵士说在瑞士有和这相似的大道,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工程。能够想像得出,在古代修建这样一条大道有多大的难度。再往前走,我们看到了一条300英尺宽、至少100英尺深的大峡谷。这条大峡谷下填满了加工过的大石头,在底下掏出一个拱形作为排水沟,大道就从上面跨过。在另一个地方,大路是从500英尺深的悬崖边上凿出来的,呈Z字型。在第三个地方,大路直接穿过了山脊中挖出的隧道,这条隧道有30码宽,也许更宽。
在这里,我们注意到隧道两边都是披着盔甲、驾着战车的精美雕塑,其中有一座雕塑尤其漂亮,描绘了一场完整战斗的全部画面,远处还有押送俘虏的队伍在前进。
“啊,”欣赏完这个古代的艺术作品后,亨利爵士说,“这里叫所罗门大道太合适了,但依我之见,在所罗门的人到达这里之前,埃及人已经来过了。即使这不是埃及人或腓尼基人的艺术作品,我也得说它们太像了。”
正午时分,我们已经向山下走了很远,到了山林交汇的地方。首先,我们来到了越来越多的分散的矮树丛里,直到最后我们发现这条路蜿蜒穿过一大片泛着银光的树木,这片树木和开普的平顶山斜坡上看到的树木非常相似。除了在开普,我在以前的旅行中从来没有看到过,它们在这里的外观让我大为吃惊。
“啊!”古德用极大的热情查看着这些树叶闪光的树木说,“这里有这么多树,我们停下来做顿饭吧。那个生心脏已经消化干净了。”
没有人反对这个建议,因此我们离开大路,来到了不远处的一条小河边,很快就用干树枝生起了一堆旺火。我们把随身带着的羚羊肉切成几大块,开始像卡菲尔人那样穿在削尖的树枝上烤了烤,然后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吃饱后,我们点了支烟,好好地享受了一下。与最近经历的那些艰难险阻比起来,这会儿看上去简直就是天堂般的生活。
。 想看书来
第七章 所罗门大道(4)
小溪岩上覆盖着浓密的巨型铁线蕨,中间还点缀着一簇簇野文竹,河水在我们身旁潺潺流动着,柔和的空气穿过银色的树叶发出沙沙的声音,鸽子在周围咕咕叫着,翅膀明亮的鸟儿像活宝石一样从一个树枝飞到另一个树枝。这里简直就是天堂。
危险感从心中消逝了,目的地最终也到了,这个地方好像拥有魔力一样,深深地把我们吸引住了。亨利爵士和乌姆宝帕坐在那里低声用蹩脚的英语和祖鲁语交谈着,看上去非常真诚,我躺在蕨类植物形成的芬芳的床上,半闭着眼睛看着他们。
不久,我想起了古德,想看看他是什么样子。只见他正坐在河岸上洗澡呢。除了法兰绒衬衫外,他什么也没有穿。他天生爱干净的性格不断地得到验证,他正进行着一次最精细的洗漱。他洗了洗古塔胶衣领、抖开了裤子、帽子和外套,现在正把它们仔细地叠起来,备好待穿。当检查到衣物在这次可怕的旅行中造成的无数裂缝和破绽时,他悲伤地摇了摇头。然后脱下鞋,用一把蕨类植物擦了擦,最后又用一块从“英格”肉上小心留下的油脂擦拭了一番,直到看起来差别不大才停下。他透过眼镜仔细地检查着鞋,然后穿上,开始了一个新工作。他从一个小袋里取出一把梳子和一个小镜子,仔细地打量着自己。很明显,他并不满意,因为他开始小心地整理自己的头发,然后停下来,看看效果,仍然不是很满意。他摸了一下下巴,胡子已经有十天没有刮了,现在长得十分浓密。
我想:“他肯定不会现在刮胡子吧”。但是他却真打算刮。他拿出了一片装在靴子里的肥皂,在河里彻底地洗了洗,然后又从袋子里拿出了一把剃刀。事实证明,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因为在刮的过程中他不停地呻吟着。看到他奋力地剃又粗又短的胡子,我笑得肚子都疼了。一个人在这种环境下,在这种地方,只用一片香皂来刮胡子,看上去真是一件非常古怪的事情。最后,他成功地将右边的脸和下巴刮干净了。正在这时,我看到一道闪光突然飞过他的头边。
古德惊叫着一跃而起。如果拿的不是一把保险剃刀的话,他肯定会割断自己的喉咙。我也跳了起来,但没有惊叫,我看到在离我不到20步、离古德不到10步远的地方,站着一群人。他们个子高大,古铜色的皮肤,其中有一些人穿着宽大的黑色羽毛编成的羽衣和豹皮短披风。站在前面的那个年轻人,大约有17岁,手仍然举着,身体向前倾,一副希腊雕塑标枪手的姿势。很明显,那道闪光是他投的武器。
我看到一个老兵模样的人走出队伍,抓住那个年轻人的胳膊向他说了些什么,然后向我们走来。
这时,亨利爵士、古德和乌姆宝帕抓起了他们的步枪,威胁着向他们举起来。这群当地人仍然向前逼近,我突然想起他们根本不知道步枪是什么,或者说他们对于枪根本就不屑一顾。
“放下枪!”我对其他人说。我明白只有和解才是安全的方式。他们放下了枪,我走到前面,对着那个拉着年轻人的老人说。
“你好,”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语言,就用祖鲁语问了声好。令我吃惊的是,他听明白了。
“你好,”这个老人回答道,不,实际上他用的是同一种语言,是一种非常接近的方言,我和乌姆宝帕都能毫不费劲儿地听懂。事实上,后来我发现,这个人说的这种语言是一种老式的祖鲁语,与我们说的语言属于同一语系,那关系就像乔叟的英语和19世纪的英语一样。
“你们从哪儿来?”他继续说,“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你们三个人脸是白的,第四个人的脸像我们母亲的儿子?”他指着乌姆宝帕。他说这话时,我看了看乌姆宝帕,他说得对,乌姆宝帕非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