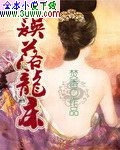葬缸·花床-第3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又刨了一小会儿,我终于绝望地在坑底蹲了下来,就象一对白人夫妇看到自己生了一个黑人婴儿那样地绝望,甚至愤怒!!
在我的面前出现的,是一个农村常见的水缸!高有几尺,直径多少已经没必要测量了!我,以前在如达家好象就见过这种东西!没错,就是这样的水缸!!
我欲哭无泪!怎么会是这样的结果!难道我偷偷摸摸累了一个多月得到的就是这样的结果吗?上帝,你对我也不能这样不公平吧!我想直嚎一嗓子,可是,又不敢!
忽然,我愤怒地站起来,用脚踹了这水缸一脚,伸手去掀缸上的木盖子,我要看看,在这个破烂儿里面会放着什么!
手机响了!吓得我浑身一软!爸的,在这样的情绪中猛然有了响动,也太吓人了!
我赶紧爬出土坑,掠起手机——
竟然是安南方的电话!上帝,此时此刻,安南方,这个老警察,竟然给我这个倒霉的偷缸贼打来了电话!能有什么事呢?我的心悬得更高更傻了——
安南方:“在哪儿呢根伟?”
“我,我在外面办事儿呢叔叔,有事儿啊?”我忍不住向四周看了看,以确认旁边真的没人。
“是这样的,我办了一个和男妓有关的案子,,你以前不是说想写这样的案子吗?”
“对对,抓了几个人啊?”
“两个,一个男妓,一个皮条客。”
“好啊。对了叔,这男人嫖女人了要罚款要劳教,要是女人找男人呢?”我故作轻松地问。
“男女平等,一样的处罚啊。”安南方笑了笑,一转话音,“我们抓的这个皮条客,外号叫‘盛哥’,他有一次提到了如达,好象如达也参与其中了。”
“是吗?”我的心一别楞。
“你也应该知道,他多次带人到你家去,到底干什么,可能你不清楚,但……好了,这样吧,算我徇私,你告诉如达,叫他以后千万注意些,不要让我查到更多的证据,不然……”
我连连答应,马上打通了如达的手机。
听了我的话,如达直吸溜嘴:“我说这一天联系不到盛哥了呢……这个安南方,动手了呀……真得注意了……不过,安南方对我还真够意思……哎,哥,你说他是不是想利用我钓大鱼啊?”
“我哪知道啊。往后,你小子真得把腰带给我扣死了,不然,我可再没空儿给你去监狱送饭了。”
如达连说知道了,不甘心地说:“哥,你不知道挣这钱儿有多容易啊。前几天,听说没有,一个男人,让三个女人给强奸了。这说明了什么呀?说明男人有市场嘛……哈哈哈……”
“男人让女人给强奸了?别他爸的胡扯了,如果男人不硬,女人怎么强奸他?还是咱们男人贱嘛。”
我竟正义凛然起来。
打完了电话,我决定先掀开这个水缸上的糟木盖子。虽然知道里面不会有什么了不起的东西,但心里还是紧张,严格地说还很害怕,但又难免夹杂着一点儿出现奇迹的奢望。
那木头盖儿,宽出缸沿子能有一指,我伸手指一抠就掉下一块儿来。屏息想了想,我又拿起铁锹来,顺着水缸四周儿削了一遍,让缸体和黄土剥裂开来,然后,伸手,用力把水缸往西移动了一点儿。是的,我想完整地,把木盖子一下子掀掉,好象这样更容易有奇迹的发生。到这份儿上,没有人不迷信的,不管他读的书是关于上帝的还是没有上帝的。
往坑上沿又扫了一眼,看到的,是一片望不透绿叶的林梢。我短促地吐了一口气,两手同时把住潮湿腐朽的木盖,顺着劲儿,均住劲儿,轻轻向上一掀,盖儿完整地被掀起了一条缝,我干咽了一下,再用力,眼睛跟着向里面一看,不禁啊地惊叫一声,悚然丢开了盖子——
第76章 其生殖器之长为身长之三倍!
我看到的是一具骷髅!白森森的!空气中,好象也立刻有神秘的气息弥散开来,让我全身都浸入了一种粘稠至浓黑却又空荡得无所依附的巨大的恐惧里……我,无言地祷求着,跪了下来!因为,我,打扰了一个沉睡的灵魂!我必须跪下,我应该跪下,求得他的宽恕……
四周很静,令人窒息的静,让我心跳如鼓,让我全身僵硬——为什么,为什么在这儿会有一具骷髅?他又是谁?为什么他会被埋在这儿?又是谁埋葬的他?他,和那个尚没有下落的葬缸有什么关联吗?……无数的念头,象地震后的群蚊,不择方向地一齐涌出来,让我无名地狂躁,这种狂躁甚至挥遁了那种天生的对死亡的恐惧……
膝盖儿有点疼了。我慢慢地扶着缸体站起来。林间的光线丝丝缕缕地斜扯着,如一张快要织成的网。一团蠓虫滚过土坑的上空,象一团大谜。爸的,灵魂是不是就是这样的?
我突然变得凶恶起来,瞪了一眼这个活活攥死了我的美梦的水缸,我几步跨出大坑,我得处理好这件事。我拿出手机,开始给高皓清打电话。
听完我的话,高皓清沉默了好久,他说,根据我的描述,我挖出来的这个缸绝对不是葬缸,里面的骷髅当然也不是什么高僧,但他让我千万不要放弃,说由一望二,那个真正的葬缸可能真的不远了呢。我能说什么呢,我说我决不会丧气。实际上我丧气得就象男人被摘了什么丸儿一样。想到了这里,我真他爸的打了个寒战。
“不管怎样,你出力不小,这样吧根伟,你用相机把你挖出来的缸拍下来,传给我,也让我看看。还有,你辛苦了这么多天了,别的什么也没干好,也别管你挖多少个坑了,我该给你点儿劳务费了。”高皓清这句话最具安慰作用了,我的钱真的又要花个七开六透了。
说完缸的事,我又顺便给高皓清说了他母亲得病以及我帮她做饭送饭的事。有粉谁不抹个好面子呀。高皓清这回沉默得更久,最后,说了句“你是个好孩子,我不会亏待你的”,就挂断了电话。
平静了一下心绪,我回城取数码相机。
跑到下午四点,我把那个水缸的照片,以及我挖出的那些土坑全拍了下来,是的,我要让高皓清看看我这个精美的城里男人这一个多月出了多少山西老叫驴才可能出的笨力。
坐在电脑前,把照片传给高皓清,坐在沙发上,我有点儿紧张地等着高皓清给我回话儿。
无意中扫到电视机,又站起来,打开,得看看,天热气潮的,别放长毛了。
电视里放的是“自然世界”,讲的是小动物的生殖,挺有意思的——
电视里说,有一种蜂,叫榕小蜂,雄性的它们,生殖器是身长的三倍,但寿命只有一天。
看得我先是发笑后是深沉:要按比例,这蜂的生殖器一定是动物之最了。可这蜂这么长的生殖器干什么呀?不用说,物有所用,一定是为了方便性交。可是,这么方便这么快意的事儿虽然干着,它们却只能活一天。上帝真他爸的公平,这儿多给你那儿一定少给你。就象我们这个杨氏家族,男人个个潇洒出众,偏就过不了那个时时紧缩的46岁的要命坎儿!
可是,这好象还不足以说明性和性命之间的关系,性和性命之间,到底有什么内在联系呢?
正感慨,高皓清的电话来了,他叹气说,那个缸,绝非葬缸,也没有其他任何价值,让我好好继续寻找挖掘,说明天就给我汇三千块钱。
我当然答应了。不管怎么说,这个高皓清对我还行啊。
刚挂断高皓清的电话,手机再次响起,这回,是樱子的。
“哥,你在哪儿呢?”樱子的声音娇里透着屈。
“我啊,在家呀现在。”我没必要撒谎,因为挖出来了个水缸,心里怎么都不透亮。
“人家想你了,看能不能打通,竟然通了。”
电视画面上,一只长得很象豆娘的雄性榕小蜂正颠狂在一只雌性榕小蜂身上,我的心里热了一下,竟然挑逗起樱子来:“想我什么呀?”
“你说想你什么……”樱子吃吃地笑起来。
“你现在在哪儿?来找我吧?邻居,包括你的表叔安南方,都不在家。”我开始主动要求。
樱子有点惊喜地说了一声“好”,马上挂断了电话。
我去简单地洗澡。洗的时候我已经想好了,今天,这一回,我就在书房里和樱子完事儿,在那张许多男女都曾放浪过的床上。
不到半个小时,樱子就来了,慌得脸上都有汗渍了。边拥抱边走向卧室的感觉好得加倍,就象听着音乐煮咖啡一样。
樱子的衣服,外红内白,只有内外两层,象本简明字典,想查什么很好查。可是,这一次,我做得却不太出色,老是心不静,老是想到那个害我不浅的水缸,那具不知身份的骷髅,有时,甚至还会想到惟妙。世界上,最需要专心的至少有两件事,一是小时候在课堂上听老师讲课,二是成年了在床上听性伴侣呼唤你——
“哥哥……哥?”樱子从忘情中清醒了一些,激情中的她,脸上是淡淡的疑惑,“你怎么了……”
“没事儿,我没事儿……”我赶紧把她抱得紧了一些,去亲吻她嘴巴以外的地方,但,亲得很粗略。
“哥哥,先爱抚我嘛……”樱子拿起我的手,放在她敞开的白嫩的胸口,真不错,这竟然让我想到了那个清白瓷的葬缸,兴趣儿还真就多了些,于是,手掌便轻轻地抚了上去……
樱子闭上眼,张开嘴,长长地啊了一声,很悠扬,于是,我又抚了第二下,奇怪的是,这回樱子却嗯了一下,睁开了眼睛,抓住我的手,在我的手心抚了抚:“哥,你的手好粗糙啊……天,还有茧子呢,你这些天在干什么呀?伺候那个女人也用不着这么用力吧?”
我暗暗惊了一下,笑着抽回手:“你心可真细呀。我这几天呀,有空了跟着老孟去农村逮蛐蛐儿呢,这扒那挠的。”
“哥,用心点儿……好好疼疼我……”樱子忽然折起身子,紧紧地倒贴我……
第77章 飞镖·哲理·天堂·地狱
今天晚上,我又得好好灸一回了。累呀樱子走后都有半个小时我都没动。要不是看到窗口越儇越近的夜色,我还想再躺会儿。。我怎么又犯了一次这样的累上加累的低级错误呀?
现在,关于性和性命的关系,我似乎明白了一点儿了:性这东西,如果用得又多又乱,性命就会短又苦。因为,那不是在享受生活,而是在挥霍生活。
忽然,我听到了声细微的蛐蛐的叫。这才想起“月牙白”来。这小东西,几天没喂,大概要饿出胃病来了吧。遂决定把它先送到老孟那儿寄养。不管怎么说,它是条命啊。人命关天,这是人说的,要叫蛐蛐说,那就是“蛐”命关天。所有的命都关天,当然包括我。
21日
早饭后,我在西耳房里扎飞镖。
我把镖盘钉在了北墙上,进门儿就能看见靶心就能玩。
共六支飞镖,三红三绿,有的叭地钉在了镖盘上,有的却从镖镖上跌了下来。这玩意儿,我有一段儿没玩了,退步了。以前,在城里时,在惟妙没来之前,我玩这游戏时是多么地自在呀,有时,就光着身子,一扬手一扬手地把飞镖耸出去,看它们几乎差不多就能落在自己想要它们落的位置,大大小小有点儿成就感呢。现在快不行了,只能先找找感觉了。
惟妙站在院子时在,问我在玩什么。我说飞镖。她竟然就走了过来,颇有兴趣。我赶紧过去,牵住她的手,把她接进屋来,别碰门框上喽。
“飞镖很好玩吗?”惟妙问得很认真。
“当然,有国际锦标大赛呢……呵呵,这锦标赛那锦标赛,都是根据飞镖大赛起的名字。”我信口胡诌着,又飞一镖,还好,中了红心,不过中了也无所谓,惟妙也看不到。
惟妙笑了一下:“你可真会胡说。”
我把一支镖放到惟妙的手心:“感觉一下吧。”
“它的游戏规则是什么呢?”惟妙用手捏住它,轻轻地比划着。
“要说它的游戏,我有自己的见解。”我很得意,“除了镖盘挂多高,飞镖时的距离,在比赛时,它还有一个规定,我给它起名叫强人规则。”
“说说看?”
“它的比赛,谁先出镖,不是抽签决定,而是比赛者每人先来一镖,谁扎的位置离圆心,也就是俗称‘牛眼’的位置最近,谁就先发镖。还有,比赛开始后,如果你不能在第一镖扎中经心,那你下面所扎的分值就不能计算上,直到你扎中为止。”
“这么苛刻呀?”惟妙真摇头。
“还有,这个游戏,我觉得,没有可以变通的地方,黑白是非,一目了然,绝无通融之说。”我又飞出一镖,正好扎在分区的钢丝上,飞镖跌了下来。
“比如现在,我本来想扎进11分那个分区扎出个11分的,可是却扎在了用于分离11分和14分之间的那根不锈钢的钢丝上,那支镖就只能跌下来,不得分。”
“相当于,要么当好人,要么当坏人,没有变更地余地?”惟妙兴趣儿更浓,“还有吗?”
“还有一点,就相当于好事儿和坏事儿总是相连的。飞镖的最高分的分值是20分,最低的分值是1分,而在镖盘上,20分和1分是挨着的。也就是说,你如果想得到20分的这个最高分,也极有可能得到1分的这个最低分。”
“真的充满了哲理性呢。”惟妙连连点头,“这就相当于一个人,如果他十分想去的地方是天堂,但他进地狱的风险也会同时大大地增加。而且,你刚才说,因为分区之间全是用钢丝隔离的,飞镖要么扎在彼区,要么扎在此区,不可能有一个缓冲地带供它附着,那,就是说,一个人,要么上天堂,要么下地狱,不可能生活在介于天堂和地狱之间的人间。我说的对吗哥?”
“对,太对了。”我的心颤了一下,我宁愿不对。
惟妙忽然叹了一口气,“不管去天堂还是地狱,从来没有偶然,都是自己积攒的结果。”
“好了,我们去读日记吧,等你眼睛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