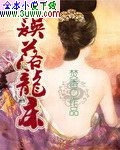葬缸·花床-第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知道他是想收卖我的心,不过,我还是故作高洁之士,推辞。但高皓清一再坚持给,最后,我只好找到我那个只剩十元的银行卡,把号读给了他。
我记好了,高皓清笑了笑,又没事儿一样,问我公安局有没有熟人,他想打听个老朋友。我想到了安南方,说有。他说,让那个人帮我打听一个叫安南方的家庭情况。我乐了,说真巧啊,我说的熟人正是安南方, 我们是斜对门邻居。高皓清嗤地再笑,说,他现在过得还好吧。我说,不太好,离婚了,两个孩子都跟他了,女儿刚结过婚,办婚事把他都给榨干了,儿子还在上高中,听说学费都成问题。
高皓清感慨说,真是人生无常啊。说完,他说先这样吧,我们之间的谈话不要对任何人讲,尤其不要对安南方讲,最要紧的是,不要对如达讲。
我连连答应。他说,明天注意查看一下银行卡,就挂了电话。
真象做梦一样。不会是高皓清在愚人节给我开玩笑的吧?可是他给我开这玩笑干吗呀?他有资本和我开玩笑吗?
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三章 我与和尚的孙子是狗友
其实,我和高皓清的儿子高如达,是好得就象永远在线的QQ一样,好得就差同性恋了一样的狗友。
说来,他们家,也是一个悲惨家庭,而高皓清在我眼里,更是个屈辱的符号:他们家,在天堂庙村,除了他们高家,村子里的一百多户人家,都姓殷。高皓清的爷爷叫高二存,是个单身汉,三十岁时才捡了个男孩儿,取名叫高德印,也就是高皓清的父亲,高德印长大之后,衣食无着,高二存就把他送进了天堂庙,当了一个小和尚。临解放前,高二存去世了,年青而虔诚的高德印就去了杭州,到传说中的济公呆过的那个灵隐寺去求拜佛,回来之后却还俗了,因为他领回了一个美丽的女人、也就是高皓清的母亲,没有人知道她叫什么名字,一张嘴就咿咿呀呀的酥掉人心的南方音儿,现在倒是能说一嘴纯正的我们当地的方言了。而当时,更叫村民爆眼眶子的是,这个女人竟然是个妓女!本来,在这个村子里,高家就是唯一外来户,再加上一个和尚一个妓女凑成的家,这下,他们家就成了村里的痰盂儿,特别是村长殷保成,更是整天嚷嚷着要把他们俩撵出天堂庙。后来,高皓清出生了,也是被村长的儿子殷常乐从小欺负到大,直到后来他考入省城的师范大学,离开了村子。高皓清也是配用“玉树临风”这个词儿修饰的男人,所以,大学刚一毕业,他的老师,一个离过婚的女讲师就对他说,要是他和她结婚,就可以留校,留在省城。高皓清把这种天上掉“可口可乐”的好事儿当成了可耻可笑,于是,他只能回到当地,成了我们市的一所高中的哲学老师,所以,本来神经绷得很紧的殷常乐马上又开始重新欺负他们了。最过分的一次是,这个坏东西竟然企图强奸高皓清的老婆。引发家庭惨剧的,是高如达家的那头黑公驴——那是十几年前的事儿了。这驴,听如达说,经常脱缰在村里乱跑,撵上谁家的母驴,举前腿而上,堪称标准驴种。有一天,那是我们上初三时,离中招考试还有一个多月,是个星期六,我又跟如达去他们家玩。他家在城南三里的天堂庙村。刚到村口,正好碰见他家的那头驴又咬断缰绳在村口撒野,那头驴,通体灰黑,又高又壮,偏长了个四个白蹄子一个白嘴头子,真他哥的威风,标准一个美驴子。如达正给我吹这驴如何能跑能追,那驴忽然一磨头跑向栓在路边树下的一头驴。如达一见,可吓坏了,他一边拾起砖头猛砸那头黑驴一边惊恐地说:那是村长家的母驴,可不能叫它上!但我们两个小男孩儿的砖头无法阻挡大公驴势不可挡的雄风,当我们的砖头落在驴背上时,它的兽根已经准确无误在昂扬挺进了母驴的体内,并顾自享受,直到淋漓痛快之后才掉头而去。那一时刻,我很惊讶,惊讶于驴性之疯狂,也惊讶于其兽根之雄伟。以至于每每在城市的大街上遇到驴车,我还会想起那惊动少年心的暴野而撩人的一幕。而就是那天,当那头驴成功地把队长殷保成家的母驴上了之后,整个天堂庙的人都气疯了,不但帮着殷保成父子杀了那头驴,还帮着他们按住高皓清,让殷常乐把一个黑黑的骗粪蛋儿塞进了高皓清的嘴。最叫人发指的是,当夜,殷常乐还强奸了如达的母亲,之后,他还说这才算扯平了,人驴两清了。惨剧随后发生,如达的母亲上吊身亡,接着,如达的爷爷被活活气死,奶奶也气瞎了双眼,高皓清跑到公安局报案,但殷保成的表侄儿是公安局当时的一个副局长,硬是把这案子给压住了。高皓清不顾一切地去找殷家拼命,又被痛打一顿,于是,他点了队长家的房子,随后不知去向。殷保成亏良心,也没敢再追究,就这样,一波大劫之后,如达痛失三个亲人,辍学回家,和奶奶相依为命。就是这会儿想起来这事儿,我都替他们家心疼,为他们家不平。唯一让人好受一点的是,老村长殷保成十年前就死了,而他的儿子殷常乐又在两年前不知道怎么地就瘫了。
这些,都是去年冬天如达喝醉之后给我说的,他说,他恨他们这个家,恨他的爷爷奶奶,更恨他的父亲,恨他为啥死心眼儿,当初不和那个女讲师结婚,这样,他一出生就是个和我一样的城里人了。他一字一沁血地说:是他爹毁了他的一生。所以,五年前,如达在我的帮助下,在城里租了间房子干起了中介公司,接着又好歹找了个农村的老婆,生了个女儿叫清清,比我儿子小两个月。赚了点儿钱之后,他又赌气在村子最西头弄了个独院儿,盖了四间房,不再和奶奶住一个院了,当然也很少回去看老人了。如达这样做,我很不满意,骂了他好多回。他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又有多少人被谁给毁了呢?又是谁在残酷地折磨着我们这个家族呢?
唉,想想就腌心。
而我现在最关心的是,高皓清到底能出多少钱让我去挖葬缸子,五万?还是十万?如果确实让我心动,哪怕违点儿法我也干,因为我现在太需要钱了。
玻璃窗上传来零碎的叭叭声。下雨了,春天的雨。
外面一定很凉。但我的室内温度是20度,是的,空调开着呢,为的是让室内保持在18至20度,这,是人体感觉最舒服的温度范围。我,就是要让儿子泡在这个最舒服的温度里,虽然他毫无知觉,虽然这需要钱。不说我,光儿子的消费,一个月最少也得一千五。上个月刚从如达那儿掂了两千元,又要干碗儿了。要知道,我连个工作都没有,只是个自由撰稿人,自由撰稿人是很自由是没有人管你,可是,钱管着呢。
第四章 先自慰后自灸 艾草蓝烟
从收藏夹里点开一个黄色网站,刚看了几个女人的裸体,右手就已经开始失控。唉,说实话,做这种事情,心里实在是悲壮,因为我要想找个女人且不用花钱是件很容易的事,如果我愿意。
右手做那种往返动作时,胳膊肘硌得有点儿疼,肘下面一本硬皮书,是那本黑皮圣经,这是信奉天主教的母亲给我留下的唯一遗产。这些天,有事儿没事儿的时候我就翻翻它,感觉这圣经真是了得。怪不得母亲生前曾说:天地可以消失,圣经不能增减一字。有时候,我都后悔,我当初为什么要学哲学,学神学也许更好些。因为,讲哲学的是一大帮人,还各说各理,而讲圣经的,只有一个上帝。
那么上帝,现在我来问问你:我自慰算不算作恶?我不求你饶恕我,只要不罚我就行了。
其实,关于自慰,我有过一次最光荣的经历,那是人家请我自慰的,不但算得上明目张胆,还算得上正大光明。那是在上海读大三时,有个精子库告急,求购精子,我带着学生证就去了,轻松过关后,人家给了一本黄色小说,让我在一个小房间里边看边“拔苗助长”,事后,还给了二百块钱。想想,子孙满天下,走到哪儿都有自己的血统,那该是怎样一种国王般的豪迈呀。就是现在,我也想捐啊,前段儿看报纸,省城新建精子库,公开了收精子,只是省城太远了,我还得照顾儿子呢。
手,静止下来,身子也松弛下来,正好响了一个雷,象是给我喝采。感谢上帝,你原谅我了是吧?
至少,自慰胜过嫖娼。而我的道德底线就是不嫖,经济底线是不能嫖。据说,在我们城里,买一次淫要一百块,够我儿子两天的营养费了。不过,看来,我倒是应该找个不花钱的情人,不为情,只为欲。“纯纯的妓女”要是能过来,应该是个不错的人选,只是,别携性病一块儿来就行。
其实,我这样做应该也不是堕落,因为前一段儿看健康报,说精子在男人体内不好,最好天天通过某种方式将其泄出。科学和上帝是敌人,这样看,我不求上帝原谅也是可以的。
而且自慰永远比自杀强。自慰可以反复成功,而自杀只能成功一次。所以,无论如何我也不能自杀,虽然有时我也有自杀的味儿……
手伸到枕边,我想抓本书看看,它,有可能是叔本华的《悲观论集》,也有可能是高更的《诺阿诺阿》,是的,加上圣经,这三本书是我的精神食粮,我从《悲观论里》寻找堕落的理由,从圣经里找到宽恕自己的理由,然后再从《诺阿诺阿》那里寻找一片幻想中的天堂。
可是,手软软的,唉,算了吧,象自慰之后再看书这样高雅的事,做给谁看呢?
不行,泄过得再补一下。这两个多月,每次自慰之后我都要额外补一下,加倍爱惜自己呀。这决不是毫无意义的减一再加一,这里边有玄妙的中医理论,反正我也说不清。
下床,去隔壁房间,那是我的健身房,除了摆放着跑步机、哑铃、飞镖等器材,父亲的药柜也挨墙摆着,里面还有好多中药,有用的我用,没用的当纪念品,一点儿也没扔,至少闻闻药香也没什么坏处。
进房间,刚拧开灯,放在药柜上蛐蛐罐里的那只“红麻头”就“吉吉吉”地叫起来,它,一定以为天亮了。智商真低。小脑袋,上面再扎两根触角的动物智商都低。人脑袋是大,可一脑袋相当于触角的头发中和了智慧,所以,有时人做蠢事实属正常。
从柜子里取出一根艾条,这种桑皮纸卷就的东西,粗如雪茄,长如两只雪茄,这可是祖宗留下的专治百病的好东西,从新石器那会儿就开始用了。现代人,除了了解的,很少有人对它有兴趣,都拼命吃西药去了。
回到卧室,半躺下,点燃了的艾条,飘出淡蓝的烟霭,散发着淡淡的药香。看了一眼对面墙上的穿衣镜,看到的,是我凝重如斯、世纪末一样的表情。在我们原来那套别墅一样的家,在我的卧室里,在床头,我可着墙也钉有一面大镜子,它最大的用途是可以让我看到艳如桃花的妻子如何在夜晚在床头为我枕上千姿百态地绽放妖娆的身体……
灸的是神阙穴,也就是肚脐眼儿。要是在白天,我还会在肚脐上放上细盐,进行盐灸。这样可以培元固本,健脾运胃,同时,还可以美容,使人看起来年轻。谁不想年轻啊,哪怕只是看起来年轻。
右手捏着艾条儿,一下一下地象鸟喙一样啄向肚脐眼儿,在离皮肉几厘米的地方住手,来回反复。可不能啄到肉皮上,要是直接啄上,那就是另外一种灸法儿了,太痛苦了。啄着啄着,我自己笑了,这动作和刚才自慰的动作太象了呀。
我给自己用的是存了两年的艾条,都是父亲存的。三年存的艾条只有二十几根儿。其实,每一次给自己,我都想用三年存的,但每一次都是拿拿又放下,不舍得用,总觉得自己不值,总觉得它们应该留给某一个人用,但不知留给谁。是的,艾条如酒,只要不霉,存的时间越长效果越好。爷爷曾不止一回地说:九年之病,求三年之艾。我觉得挺高深,后来我才看到,原来这是孟子在他的《离娄》说的,除了这两句,他还说:苟为不蓄,终身不得。意思很明白:要是你不留它,一辈子就别再想得到了。
等有空了,得去城外采点儿艾蒿了,春末夏初,正是采蒿的好时令。得备点儿,别让艾条艾炷断顿儿了,这会儿,对门儿的老孟,还有安南方,有个小病小恙儿的都开始让我灸了呢,我好交朋友,只要能看得起我,看得起我祖辈传下来的医术,我全给他们灸。
肚脐,开始暖意如水,浸上身来,睡意渐浓……
第五章 首次偷窥:对面女人不着内衣
4月2日
醒来已是早上七点了。今天星期日。当然,对我来说,只要我和儿子有吃有喝,星期几都无所谓。
洗濑之后,用“非常可乐”配制了一杯特殊的饮料,放进冰箱的保鲜柜先冰着这样可以增加点儿美味儿。我从来不用美国的“可口可乐”配制我这独特的保健饮料,那样,就连一点朴素的爱国之情都没有了。
大街上有隐约的声音传来,听不清是谁发出的音儿,不外乎汽车,人,也有可能是狗。在五楼,听大街上的声音就象隔着肚皮听胎儿巴嗒嘴儿,听不清啊。
接着,我去跑步机上大口小口的喘,然后,再投一会儿飞镖。这小玩意儿,我挺喜欢的,不管哪种玩法,每一次射中红心或十环,那种一箭中的的感觉,大有得女人到手的英雄味儿。
蛐蛐罐里的蛐蛐儿,没有一点声息。
半个小时之后,左手端着饮料,我进了卧室,站到窗前,皱眉饮了一口,然后,伸右手,慢慢把窗帘拨开一条缝,看我雨后的窗户。是的,我担心有人看到我,因为现在的我一丝不挂。是的,我喜欢在室内裸行,这习惯,是我的家被命运之神搬空之后才养成的。我觉得这种状态特别自在。我的心灵已经不再自由,我不想再用布料和款式囚住我的肉体。每每看到谁谁谁在大街上裸奔的新闻,我就羡慕得厉害,只是,我从来没这勇气去这样奔上一程。
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