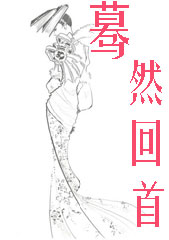回首又见他(清穿)-第1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已经怒火中烧:“什么是奴才!什么是主子!凭什么规定了有人就是奴才,凭什么规定了奴才就应该是主子泄愤的工具!奴才也是人,是人怎么能说打死就打死——”
“啪!”脸上挨了重重的一下,顿时火辣辣的疼起来,我TMD居然送上门来挨打!
我强忍住眼泪,看着他有点慌了神的样子恨恨的道:“好!松萝在太子爷的面前也是奴才,您既然要打,就不用您动手!”
我摔了帘子冲进院子,扑在那个小太监的身上,那两个人还来不及收手,我的屁股上就挨了重重的两下。
“住手!”太子已经冲了出来。
我的心里还是舒了一口气,连忙翻下来。这个小太监已经气息微弱了,希望能救过来。
“太子爷,松萝求您让人把他抬下去吧,他一个奴才搁在这儿也碍眼不是?”我微扬了头望向站在台阶上的太子。
“爷,”表姐脚步匆忙的走来,她身后不远是慢慢踱过来的太子妃,“爷,松萝还小,冲撞了爷,您就饶了她这一回吧。”说着过来扶住我。
我在心里苦笑,大正月的,我这是走了什么霉运。这两板子就疼得我够呛,还不知道这个小太监怎么样了。
我依然毫不妥协的望向太子,他苦笑了一下,对旁边的小太监说:“把他抬下去,再给他上点药。”就自己掀了帘子进了屋。
我的心里再次舒了一口气。
表姐望着我叹了口气,道:“走,去我那里,我给你上点药。”
经过太子妃身旁的时候,我微微点了个头算见了礼,就跟着表姐去了。
“嘶——”
“现在知道疼了?”表姐停了手问。
我趴在炕上摇摇头道:“不疼。幸好穿得厚。”
表姐继续给我上药,说道:“唉,不知道爷今儿是在哪儿憋了气,心里不好受吧。”
说起这个我就上火,支起头道:“他心里不好受,干嘛要把气撒在别人身上,还把人往死里打,更何况他还是个太子,他难道不知道有多少双眼睛盯着他。”
“你少说两句吧,还嫌没挨够?唉,做奴才的,就是主子让你马上去死,你哪敢说半个‘不’字?”
我泄气的又把头枕在胳膊上,小声嘀咕:“万恶的旧社会,吃人的旧社会……”
表姐叹了口气自顾自的说道:“其实爷也不是总这样,平时挺好的、温润体贴,只是有时候说发火就发起来了,无缘无故的。唉……”
“啊?”我抬头望向表姐,她的眼圈已经红了,“太子是不是不能受刺激?一受刺激就发怒,不能控制?”
表姐点点头:“可不是,爷有时就为一些小事大动肝火的,可是平时是真真知道疼人的人……”
我沉默了,用现代的观点,太子可能是患有间歇性精神失常,这种病就不能受刺激。虽然听起来有点扯,但是这个似乎能更容易的解释康熙一废太子时太子被魇而发疯的事了。那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滋味、那种离权欲的顶端只差一步的懊恼并不是谁都能体会到的,更何况太子在这个位置上,一待就是三十年啊。精神,是不是快承受不住了?
我望着表姐半天道:“表姐,太子他、打过你么?”
她咬了咬唇点点头,我的心涩涩的,说不出话来,只能握住表姐的手。
她忽然笑了笑,拍了拍我的手背说:“没什么,他打完了也后悔了,还一个劲儿的道歉,那样子,就像一个做了错事的孩子。”表姐的眼里亮亮的,她的心应该是酸涩中有甜蜜的吧,只是这种酸涩,也是为了太子。表姐为了太子,真的能放下自己的一切,无怨无悔,这种爱,伟大也让人羡慕。
“行了。药上完了。别动,再趴一会儿——”
正说着话,有小太监的声音在外面响起:“侧福晋,太子爷让奴才给格格送金创药和消肿的膏药来了。”
表姐忙出去了,就听见那个小太监又道:“太子爷说了,消肿的膏药一天敷两次,就能见效了,金创药敷三次就好了。”
等表姐进来,就见她笑着说:“正好没了消肿的药了,倒也及时。这金创药比我的这个还好,你回去的时候都拿着,记得按时上药。”
我点头,叹口气道:“得,看来这个脸啊,得顶一天了。”
无奈
在表姐那儿待了一阵,疼得强些了。又和她一起描了花样子,我就起身告辞了。表姐送我出来。
还在穿廊走着,表姐忽然扯了扯我停下来,我疑惑的望向她:“怎么了?”又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
这个角度正好能看见院子里,而因为被斜前方的柱子挡住又比较死角,院子里的人却不容易发现。
太子一个人在雪地里来回走着,双眉紧锁。忽然又停住,深深地呼了口气,在手里呵着热气搓了搓手暖了暖,眉头舒展些,仿佛下定决心一样迈步往穿廊这边走过来。
走了好几步,又犹豫了,慢慢停下来,叹了口气,低着头往回走。那样子,就像受了很大的委屈。
我又好气又好笑。
表姐轻轻地说:“他就是这个样子,这会儿,一定是后悔了,又不好意思过来。”
我叹了口气,慢慢地走过去,他正转过身,忽然看见我,愣住了。
我走到他面前。
“松萝,我……”
“太子爷,您以后要是生气发现不能控制的时候,就围着紫禁城跑几圈,这样心里就能慢慢平静下来,又不会迁怒到无辜的人身上。”
“你知道我、我当时真的不想,可是我就是控制不住,我现在都记不起来自己干过什么……”
看着他手足无措的样子,我的心又软了下去,这是被那个叫权欲的心魔折磨得吧,已经不能控制自己的感情和行为,这时的太子,是不是快要接近崩溃的边缘了。
“我知道,你的痼疾在这里,”我指了指心脏的位置,“可是这不是你视人命如草芥的借口!”我深深地叹了口气,压制住火气,又道:“是不是心里已经变得焦躁不安快要无法承受了,是不是夜里已经不能好眠了?我相信,很早以前的太子,一定不是这样,可是身份没有变,心态为什么会变呢,”是不是现在这里的一切已经无法满足你内心不断扩张的欲望,是不是你已经厌烦了太子这个位置而想试着早点改变,可是这些话,不能说出来。我控制着用词,缓了缓语气,“一个人,要想过得开心,就应该知足,一定不要奢求太多,否则自己的心,终究有一天会被自己丢掉。你知道这个世上,每天有多少人还在为自己的性命担心,有多少人为了自己的尚无着落的下一顿饭在多么恶劣的环境里劳作,又有多少人孤苦伶仃流落街头。你相比于他们,真的是太幸福了,你有你皇阿玛的宠爱,你有妻子的关心,你还有可爱的孩子;你渴了有玉液琼浆,饿了有玉粒金醇,冷了有锦被狐裘……”
他一直望着我,怔怔的听着。只是我不知道我的话,会不会让他心里的负担减轻一点。
他忽然笑起来,开口道:“你终于能这样跟我讲话了,你要是再说重些,或者干脆骂我一顿,我会更舒服的。”
我忍不住翻白眼儿,万分无奈,感情这个人不是虐别人、就是自虐!
我就道:“您是太子爷,我哪里敢骂你。我要是那样早尸骨无存了。”
他看着我的脸,眼中焦促道:“我当时真的不能控制,我、我……唉……你讨厌我了是不是,我都讨厌我自己……”
我没好气地说:“我要是讨厌你还跟你说这么多干什么?你记住了?”我看着这个任性的孩子。
“什么?”他问。
“就是你生气、或者心里难受的时候,在发火前绕着紫禁城跑几圈。免得你迁怒无辜。”
他点点头:“知道了,我听你的。”
嗯,听话才是好孩子。
我道了声告辞,跟表姐一起往出走,刚走了几步,就听见太子喊道:“松萝!”
我回头。他担心的看着我:“……记得上药。”我笑着点了点头。
表姐一直把我送到前星门,又嘱咐了好些,我说了些让她安心的话就告辞了。
我往漱芳斋的画室走去,刚掀了帘子,就看见吉泰在看我的画,我掩嘴悄悄地走过去想吓他一吓,这个人今天反应够迟钝的,居然还没有发现我。正要叫他一声,突然间发现不对劲儿。
吉泰垂着的右手里,是一个荷包,他的指尖无意识的慢慢摩挲。他的面前,是一幅画,只是画上的人让我的心突突的跳起来,这样失神的吉泰,是我没有见过的。
我努力压下快要跳出来的心脏,轻轻退到门口,然后笑着叫道:“哥!你怎么来了!”
他回过头,看到我,掩饰着把手中的荷包塞进袖子里,笑道:“我等你半天了……你的脸怎么了!”
我装作没看见,只是他的眼里刚刚还来不及褪去的温柔的神情让我心悸。我笑着道:“刚不小心被树枝刮了,上了点药,没事。”
他走过来看了看,敲了我的头没好气地道:“怎么又不小心,总是这么不小心,你这性子什么时候能改。走路都能被树枝刮到,我看你哪天把自己弄丢了都不知道!”
我忙打住:“又开始你的碎碎念了。你来不是专门教训我的吧。”
他无奈的看了看我的脸:“真的,丑死了——别打、别打,我有好消息!”
我停下拳头问:“什么好消息?”
他神神秘秘的笑着从怀里掏出一封信:“阿玛来信了。”
我忙打开,阿玛熟悉的笔迹就在面前:
吉泰、松萝吾儿:
新年即临,本是家人团圆之日,然吉泰常年在京,松萝也快离家一年,家中倍显萧索。吾与汝母商议,决定卖掉家产,回京安置,盼之团圆。预计二月抵京。
家人俱安,勿念。
康熙四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夜
我的视线渐渐模糊,抬头笑着对吉泰说:“阿玛、额娘就要来了,还有小晟佑。哥,我都快等不及了。”
吉泰笑道:“我也是。咱们一家人已经很久没有团圆了。阿玛年纪也大了,总是要回京城的。不过看阿玛的样子,也无心官场,反而是对经商兴趣大些。”
“嗯,可是北京城的客栈数都数不过来,到时候看来要想别的办法了。”
吉泰道:“嗯,到时候再说吧,信你拿着,我先走了。”
我把吉泰送到门口,看着他的背影,阿玛来信的喜悦依然不能冲走内心的沉重与担心。哥啊,你可不能在这事儿上犯糊涂啊!
我回到画室,看着那幅让吉泰失神良久的画。
画中那个如丁香一般美丽愁郁的女子安静的坐在椅上,唇角露出淡淡的笑容,那样的神情,让我想到一句话,美人如花隔云端。
吉泰,你到底是怎么想的,你明知道自己一点希望都没有,你明知道最终换来的不是心痛就是心死,为什么你偏偏喜欢的人是她?
可是喜欢一个人又哪里需要什么理由呢。我叹了口气。如果是你和悦宁,我会为你们祝福,可是如果是你和她,你的爱情哪里会有结局啊。
第二天,我的脸好多了。身上的也不疼了,不过这伤没敢让青柳知道,光我的脸就够她啰嗦的了。
“松萝——”听这个声音,除了悦宁还能有哪个。
画室的帘子被掀起来,悦宁笑嘻嘻的跑进来:“松萝啊,那个、我有事儿跟你说。”
我一边做泥塑,一边望向她,一看她的样子就知道没什么好事儿。
悦宁又笑道:“松萝啊,我生日那天你送我的那个兔子吧,被胤礼那小子给抢走了。”
我仍然望着她,预感到有不好的事在等着我。
“所以嘛,你再给我做一个吧。”她天真烂漫的望着我。
我叹了口气,果然我是自己给自己找罪受,还是点点头:“那我这次给你做个别的吧。”
她叫起来:“你答应了!呵呵,这次也要做一个可爱的,最好比那个兔子还要可爱,我要让胤礼那小子羡慕死我。哦呵呵呵……”
这怎么皇室里的人都比较的不正常呢,这丫头都十四岁了,还跟一个六七岁的孩子较真儿,唉,真是拿她没办法。几天前她过生日我心血来潮给她做了一个兔子的毛绒玩具,这次就给她做个小猪吧。
“啊,松萝,你这做的是谁呢?”她笑着问。
我假装生气道:“我手艺没这么差吧,这你都看不出来。”
“啧啧,还别说,嗯,是挺像我四哥的。”她偏着头转来转去的看。
我笑道:“还是的。你也不看看是谁做的。”
心痛
正月十五,上元灯节。
晚点时分刚过,悦宁急急忙忙的跑来找我,把我手上的画笔一夺就道:“你这个人真真没意思,今儿过节,你怎么还在画啊?”
我夺过画笔道:“今儿过节,关我什么事。”
“人家都过节呢,你窝在这里画画,闷死了都。”
我摇头:“我倒不觉得。过不过节对我来说还不都一样,我得愁我这差事啊,照这个速度,别说两年,我看五年也不行。”
悦宁又拉住我袖子道:“行了、行了,也不在这一天。走,咱出宫去玩儿去。”
“今儿你要不怕被挤成汉堡包,你就去吧,”我又斜了她一眼道,“我说公主,万岁爷准你出宫了?”
她撇撇嘴:“皇阿玛正忙着呢,我没去烦他老人家。你不是有男装么,借我穿一件。”
我笑道:“得,亏你能想出来,你不怕,我还怕呢。”
她气得一把抓过我手里的笔随手一扔,拉起我就走,边走还边说:“你就信我一次吧,你今儿要不去,明儿一准儿后悔!”
我苦笑,这家伙什么时候这么大劲儿了,只有跟着。
换了衣服,刚一出宫门,就看见胤祥站在马车旁来回踱步,见我们来了,笑着说道:“可算来了。”
悦宁还拉着我,指指我说:“我好说歹说才把这尊佛请了来,她还真行,大过节的窝在屋里。”
胤祥就道:“幸亏是来了。上车吧。”
悦宁在我前面上车,我紧随其后。掀了帘子,一看,愣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