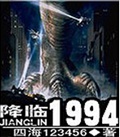1996年,我流浪在东莞-第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第一节
过去流浪的事情,尤其是些阴暗的记忆,我难以开口说出来,就好像自己在与一个女人偷情,里面的快乐和激情的场面及细节,我不可能详详细细地对陌生的你,及我身边的朋友说:啊,我的那个女人是怎样的美丽,乳房如何的饱满和结实,手脚又是如何的细长富有弹性,而最令自己要去留恋的怕是那个深藏的洞府了……
1996年,我流浪在东莞,就是一个值得去回忆的,可写下来的故事。故事没有多少情节,缺少波折,似乎有些不动人。流浪中所奇遇的故事可借助幻想,那可以到电视剧中寻找。我走在东莞大街的流浪是自己的一个真实过去;或者说是自己的一个更符合事实的幻想的1996年。
到底是些什么呢?
奇遇?记忆?幻想?沉沦的故事?不要急于打听结果,什么事情看到了结果,那富有感觉的过程就没有了,这样的事情见多,什么意义也就没有了。好比*一样,*是结果,但最欢乐时刻还是那么一段*的过程。这样的事实,有经验的男女都知道,不用我在这里面写,否则我的文章变了色调,有少儿不宜的嫌疑。
先说两个女人的容貌。
一个是:一顶乌黑的头发总是披在肩上,笑的时候总是把头重重一摇,让黑头发轻轻地飘起飘落。没有不开心的,整天不是咿咿呀呀地唱,就是咯咯地笑。初次与她相见说谈,还觉得其言行举止幽默风趣,久之,便产生了讨厌感,因为总是那几句呶呶嘟嘟,很烦人的老调:
1,婆婆妈妈的,有话就讲,有屁就放,何必这样那样地转弯抹角,细崽,你知……
2,妈咪喲,这好大的屁又来了,还是那股河南味,这里面却还带了点辣椒味。
3,奶奶喲,困死了。
4,舒服,睡觉睡到我好孤独……
这样的老调总不离口,并且还要夹点南方的洋味,还要装一下怪脸。她走路的姿势更好看,如只臃肿蹒跚的鸭子,屁股一摆一摆的,嘴里还哼着不成调的歌,自认为和入时或时尚呢。
另一个是:瘦白的脸嵌了一双迷人的眼睛,充满了灵秀,见人聚在一起说笑时,总是上前露出那排洁白的牙齿,咯咯地笑问:“啥子?”与人说话总以老子自称,总喜欢动手动脚,是典型的四川女人。整天也是开开心心的,连走路都是连蹦带跳的,那姿势怪难看,好似澳洲的袋鼠在直立行走。这样的前俯后仰的姿势身材,却还用那紧身的牛仔裤牛仔衣来紧圆,中间捆一根很宽带的黑皮带,更见其弯曲了。极度高兴时,一边走一边跳,一边唱一边拍手,总是那么不成调的这句词:
高高的高跟鞋——高高的高跟鞋——高高的高跟鞋——高高的高跟鞋——高高的高跟鞋……
这样重复不止,况且声音在嘶喊,生怕人家听不到似的。
这两个女人是一对好朋友,我经常见到她们在一起上班下班,也就是所谓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吧!
呶呶嘟嘟的女孩,我叫她胖鸭子,只唱一句高跟鞋的女孩,我称之母袋鼠。当然后面还有女人,暂停介绍。说了故事里的人物,在描绘一下事情发生的背景,即说我流浪的东莞大街,当然是我在1996年时所记住的样子。
那时候,绝没有现在这么繁华昌盛,灯火辉煌。现在我走在东莞大街,再难以想象出十年前的那些阴暗的破旧景色,还有杂乱的记忆。
1996年,东莞的大街,天是灰白的一片。用灰白只是一个单调的颜色,说清冷的寂寞似乎更合我当时的心情。可是清冷只能形容心情,事实上街面上人迹熙熙攘攘,车流不息。大街最宽阔的地方,就是汽车站出来的十字路口,有一个巨大的环形天桥,人行道横跨在交叉路口的上空,四方道路上来往的人通过天桥就可去对面。随意或畅通无阻更合适些,表达的词汇还有很多。天桥上什么样的人都有,拉客的装出热情的脸,乞讨的摆了可怜的像,做假证件假发票的主动跑了过来,卖小玩意儿的坐在地上吆喝,站在那里看风景的情深深的入睡了,更多的是来去匆匆,像我这样的过路人。
天或是乌黑黑的沉暗,风暴雨从高空中落下来,正打在我要穿越的马路上面。我不想上天桥,看到主街大道上的车流缓慢下来,便趁了一点空隙横闯过去,车就从我身边飞过,雨水向两边卷起,溅了我一身,我就大声骂娘,可人家一点也听不到,或是被哗哗的雨水吞噬了。这时候,抬头往上看天桥,它就空寂了,再也看不到一个人影。
这是我当时对东莞的一点最初影像。
环形天桥人行道现在还在,但桥面底下的花草修葺得齐整了些,压坏了许多的坑洼的路面得到了修补,也打扫得很干净,路边乱放乱摆的小贩摊位也被城管赶走了,总之不是我记忆中的那个样子,美丽了。
我下车的地方是东莞总站,一个很小的地方。它就在贯穿过市区的209国道的大街边,至于我从从总站后门走出来的那条街,我已经忘记了它的名字。印象中,站里很狭窄,一栋四层楼后面的空地,三方被墙围了,可能是太多的大巴和中巴拥挤在那里,或许是上落车的流浪打工仔太多,可以说用潮水来比喻也不为过。地上是满地狼藉的垃圾,记得是夏天的六月里,垃圾中最多的还是那些喝了丢掉的空饮料瓶。有人争抢,不会担心满地滚动而被自己踩到滑倒。
我一个人独身来东莞,当然是去投靠在东莞打工的姐姐。我从广州来,离开那里当然是找了很久的工作没有着落,听老乡们说东莞的厂很多,我又揣了一个大学文凭,当然怀抱了希望的心来了东莞。
现在的东莞总站搬迁到了郊外,而且还有南站和东站来分流走在这个城市里的人。地方宽大了许多倍,建筑物也气派了许多,看上去还真像一个快客的出进港。相比十年前,很多的事物都发生了飞跃变化,东莞大街,我的心情,以及万千走在打工路上的人对自己的认识,职业观念和所处的城市环境,以及社会对流浪打工的看法,提供了更多合理的条件,异乡不再那么生疏,都变了。
我跳下车,心情当然怀抱了来一个新地方的喜悦心情。写到这里,陌生的你就知道我是一个在东莞大街上寻找工作的失业的大学生了。或可以这样来描述我当时的落魄的样子:戴了一副黑边的大眼镜,留了一个中间分的汉奸式头型,说话小声小气的样子,这说话的腔调主要是钱袋空了起来,自己又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工作,心里不死心,但又有些灰心颓废的情绪。
而我现在,早已离开了东莞城市,许多的记忆总无法想起。曾在南方工作差旅途中,我搭车经过东莞,看到那些摩天大楼,宽阔大道,青山流水的公园和人工湖泊,还有一切舒适的景色,我的心情就想写东西,我就想起来了1996年,我流浪在东莞大街上的往事,和社会不完善中给我带来的一些伤害。
我来到天桥上,如那日天空晴朗的话,灰白的天空中也会布满了阴霾一样的烟雾。这烟雾当然加速了东莞城市的发展,可是也给居民带来了空气的污染。我就沿了台阶上去,游荡在桥上,无所事事的样子,其实心里很沉重。
沉重的是一份心情,或说是对自己的人生的迷茫,确实很没有方向感的他乡道路。万千打工的人奔走这个城市,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天空中那日出现的即使是朵朵洁白的云,我望上去也带了自己心里的灰色。
最重要的一点要明白,而且特别要指出来:文章中的这个主人公——我,当然不是作者,这样写是为了叙述的亲身感和塑造一点真实,当然里面也有作者过去生活中的一点影子,或者说是我在那一年中的幻想人物更确实。如果当成了作者自身的事迹来说,好像文中有些矛盾的样子,前言不搭后语;看作是我过去生活的一个空空的影子,似乎又有些不仅是那么一回事。
所以我要取个名字给故事中的主人公,我记得当时胖鸭子和母袋鼠叫我四眼田鸡。这个名字只是说明我当时戴了一副黑眼镜,我已经说过了,而我现在早把那代表了知识分子的象征的最后一点东西都丢了,我的视力好了起来,主要原因是不再喜欢看书,眼镜早被自己锁到了记忆中去了。
四眼田鸡这名字我不喜欢。
我叫夏华,很伟大的一个名字。我喜欢毕业证书上父母给我取的名字,我已经写了二十三个春秋的名字,可是那年胖鸭子和母袋鼠却喜欢用四眼田鸡来跟我打招呼,或用这个我不喜欢的符号来跟我开玩笑。我也是,用自己最直观的视觉来给她们俩各取了一个外号,她们也不爱听,但我也是那样。因此,她们的真实的名姓过了这么多年,我是真的忘记了,一点儿也想不起来。
作者题外话:小说中出现无数的自我否定,情节的重复与不确定性,这是作者以此手法来表达“夏华”对1996年回忆的灰*绪和惊恐不安,他在自我否定的怀疑中走向1996年那一片爱情以及打工往事,从而完成“1996年,我流浪在东莞”的小说记事。
第二节
我不喜欢故事这样开始:一个大学生,他叫夏华,怀了一纸文凭来到东莞,在一个明朗的夏日,天宇灰白,空气中流泻了工业区飘出来的大片烟雾;或在一个暴风雨的天里,横穿过209国道的东莞大街,飞驶过去的小车溅了他一身泥水,气得在那路边骂人,但人家早已过去了……
故事这样来写,好像没一点情节趣味。
对于情节的构建,我想说一点点,1996年的东莞大街,原本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不好的开始,现在所写的那个岁月只是回忆的笔调,很多的细节已经淡薄了,只能借助幻想来美化或沿着过去的一点轮廓扩大,使之更具真实性;说来说去,故事还是一个开始。按照记忆的思路,我应该这样描述:
耸立云空的高楼,杂乱的低矮的旧房混在一起,在一片灰蒙蒙的天空热哄哄地涌动,连成了一片。环形的天桥底下过去,大街小巷满是拥挤的人潮。马路上,飞驶的车流在那里如一串鱼似的来回穿梭。路边墙牌下,女人的内衣广告在明亮的日光下生动起来,一个个明亮干净的女子就好像要走下来想同我说一阵话儿。空气中充满了乱糟糟的声音,我不想再听下去。
我背靠着天桥上的栏杆,一个人站在那里出神。
远望了灰白天空下的东莞城市,我就把自己的眼镜回到近处的天桥上来,心里是沉重的迷茫。我打了电话给我在这个城市的一家台资工厂做文员的姐姐,没想到接电话的是一个男人的生硬声音,我很不爱听可又得继续听下去。
电话里那个男人问我:你是谁?真他妈的啰嗦,他以为我在这里打电话不要钱。他一点也不知道我的口袋空了,电话费又是那么贵。
我忍住气,说:找夏眉,请她接电话。
男人还是那么多话,慢声慢气地说:夏小姐是你什么人?真他奶奶的那么多废话,我边打电话边看手腕上的表,时间跳得特别的快。
我很快回话:我叫夏华,她弟弟。
那个说普通话很别扭的男人终于说出来,我最想听的话,但不是那一句:喔喔,夏眉——她出差了,到香港去了。
电话里传来了一阵子笑声,我心里想出差有什么好笑的呢?这个男人还要唠叨,我就直插话语中心,很客气地问:先生告诉我,她什么时候回来?
男人嘻嘻笑笑的声音更大,说:我怎么知道?我能知道吗?我也不知道啊!过了一阵,又告诉我:喔,她出厂已十天了。
男人还想说下去,我气得骂了起来:你娘的就是废话多,说人走了不就完了。
挂了电话,心里满身火气,付钱的时候,我又把空的袋子掏了一少半给店铺,心里更想骂人:他奶奶的一句话这么长。
靠着天桥的护栏,我望着夜色慢慢地垂落下来,华灯初放的街上一片灿烂,夜渐渐被灯光点亮。歌声开始飘荡,被夜风吹送到了天桥上,我很清楚地听到那些歌舞音。街面上的店铺辉煌,里面出进的人,特别是那些美丽的女子,脸白白的,腿长长的,身材那样的柔软丰满,这时候我的心里就想到了女人,欲望火一样的在我身上烧了起来,空寂的心在虚空的东莞的夜街上飘飞。
故事开始也可以这样写道:我从东莞的总站下车,就遇到了一场狂风暴雨,躲在车站里直到雨水小了下来,我才背了行囊出站。车站很小,三四步就出来到了大街。饭记得还是在广州的一家路边饭店吃了,时间过了半天,我又经过了209国道那不平路上的颠簸,肠胃便慢慢地空泛起来。
此时天色昏暗,我走出车站,并没有见到说好来接我的姐姐。沿了街道往天桥上来,想横穿马路但又不想上天桥,走天桥当然是路远了许多,就站在东莞大街路边看眼前在细雨中来往的飞车,看到路面上空出许多地方,车辆还在一百米的前方就趁机闯过马路,没想到车瞬间就冲了过来,溅了我一身泥水。我气得大骂娘,可人家早在雨水中过去了,就算没有过去,路面上那么大的流水声和车鸣的杂音合在一起,也是不可能会听到。所以,我骂人家的粗话是白废了口水。
过了马路,我就站在去大岭山这路边的店铺上等车,准备去姐姐那里。姐姐没有电话,我们联系总是用很慢的信件,她上次来信说就在这附近。她的脸很苍白,记得上次从广州过来东莞时,我就记下了她那劳累过度睡眠不足的样子。姐姐没有电话,也是一个跟万千流浪在东莞大街上的我一样,无奈地漂泊他乡,为了生活而要受无尽地劳累,只是她是一个女人,所以找工作相对起来要容易些,不像我在广州找了半年,还是一点希望也没有,也不知道何处可以停留自己。
“夏华——”有人喊我的名字。
我听到了熟悉的家乡话,是姐姐的声音。扭转头来,我发现了苍白脸色的姐姐在不远的地方向我挥手走来。她的眼镜真犀利,一点不像我这个从高等学府出来的人,其实是一点用处也没有。我走在东莞的大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