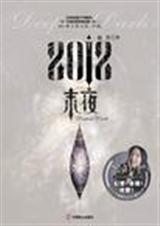暗访十年2-第4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他们最常谈论的话题是攻打日本,他们说日本根本就不是中国的对手,中国这么多人,一人一泡尿,都能把日本淹没了。到时候,不救日本男人,只救日本女人,“咱们这些人,一人一个日本老婆。”他们说得神情庄重,煞有其事。
更可笑的是,他们说起现任一位高级领导人,说他在镇压犯罪分子的时候,戴着钢盔,亲自上街抓人,更高级的领导人说:“啊呀,这是一个人才,就提拔他去了北京。”这位领导人现在已经70多岁,怎么能够戴着钢盔亲自上街抓人?然而他们说得有鼻子有眼,好像亲眼看到一样。
他们还经常幻想着如果首都迁移到了他们所在的那个地区,会是什么情景,他们就会成为首都居民,这样的话题经过了三个人的口述,就变成了首都即将迁移到了他们所在的那个地区了。他们兴高采烈地传说着这个无中生有的消息,每个人脸上都带着莫名的兴奋。
医托,都是些神智不正常的人。他们好吃懒做,好高骛远,他们相信无中生有,他们中的很多人都相信自己不是医托,是在做好事,是医疗中介,是把不认识路的人介绍到好的医院去。
他们认为自己是在做好事。
医托每天的工作单调而轻松,下午四点过后,他们就会陆陆续续地回到旅社。抽烟、吹牛、打牌成为了这个时间段的最主要的活动。他们从散发着霉臭味的房间里走出来,有的围坐在院子里的石桌旁,大唿小叫,将扑克摔得啪啪响,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会打一种叫做“双扣”的游戏;还有的在屋檐下坐成一排,神情木讷,像一群晒太阳的乌龟;我则拿着一本书在看。距离小旅社不远的地方,有一家古旧书店,我从那里淘到了好几本书籍。
小旅社还有一名服务员,是个老年男子,终生未娶,腰身佝偻,满面皱纹,负责打扫卫生。他不会打牌,却又非常喜欢看人家打牌。每天下午,他都乐呵呵地站在石桌旁边,看着这些打牌的人,脸上带着小孩过年的神情。有时候,打牌的人嫌他挡住了视线,就骂他一句,他不恼;或者打牌人哪一张牌出错了,也骂他,他还不恼。他有点耳聋。
有一天,他看到我看书,就走过来问:“你怎么不去打牌?”
我说:“我不会。”
他很认真地想了想,说:“哦,我还以为你说你不会。”
在小旅社里,我见到了人们的种种生存方式和生存状态。
医托的每个房间里都要住十个八个人,夜晚,床上地上都是人,拉鼾声此起彼伏,放屁声间或响起,屁臭脚臭相互混杂,让旅社变成了公共厕所。尽管时令是秋天,然而,这么多人居住在一起,一点也不冷。夜晚,我将报纸铺在地上,裹紧衣服,靠在墙上,就能度过一个夜晚。
在这里,资历浅的睡在地上,资历老的睡在床上,而很多人来后几个月就搬出去了,他们赚到钱了,他们搬迁到了带花园的小区里。
也有人一直在旅社居住,比如蝎子尾巴,他成了医托的宿舍舍长。据说他在这里已经居住了一年。
蝎子尾巴的外号,不是说他为人毒辣,相反他为人很直率,这个外号是说他性子很急,像蝎子尾巴一样,一碰就会翘起尾巴反击。
当医托很容易就赚到钱,而蝎子尾巴一直没有赚到钱,就因为他的头脑不会转弯,他认死理,他性格急躁,他说谎缺乏艺术性。别人看到患者都是柔声细气,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一般让对方相信自己有亲人在私立医院把疑难杂症治愈好了,而蝎子尾巴则是集团轰炸式的,他一看到患者就像猎狗看到猎物一样,兴冲冲地冲上去,要给人家介绍医院,要带对方过去,还强行抢着要拿人家的行李,让对方不由得对他心怀戒备,他总是和对方交谈没过三分钟,就把对方吓跑了。因为他的态度太热情了。过分的热情则会惹人讨厌和警惕。
很多医托都是夫妻搭配,父女搭配,但是没有人愿意和蝎子尾巴搭配,单打独斗的蝎子尾巴很多时候都是空手而归。
有一天,小旅社里来了两个和尚。两个和尚都穿着杏黄色的袈裟,面容沉静,肥头大耳,一副正大光明的神情。而一登记完毕,把两个香色布包放在床上,他们就露出了本来面目,嬉皮笑脸,对着房间对面的女医托打情骂俏,要带着女医托去逛街。
蝎子尾巴看到了,就挺身而出,大声质问:“呔!出家人怎能不懂规矩?”
两个和尚也说河南话,他们仍然嬉皮笑脸地看着蝎子尾巴,给蝎子尾巴发烟。蝎子尾巴摆手不要。蝎子尾巴尽管头脑不太灵光,性格急躁,可是他不近女色,医托们经常在一起谈论女人,话题很黄很暴力,而蝎子尾巴总是一言不发,面红耳赤,像个不谙世事的女孩子,他觉得好女色的男人都不是好男人。所以,很多医托就说三十多岁的蝎子尾巴还是处男。如今,说谁是处男就是骂谁没本事没魅力。
今天,蝎子尾巴看到两个和尚光天化日之下调戏良家妇女,禁不住火冒三丈,是可忍,孰不可忍?
蝎子尾巴一副大义凛然的神情,保护着医托,像武松保护潘金莲,然而,两个和尚的一句话让蝎子尾巴瞪大了白多黑少的眼睛,半天说不上一句话来。
两个和尚说:“看明白了,我们不是和尚,我们只是光头。”
两个和尚依然是一副笑嘻嘻的赖皮嘴脸。
后来,蝎子尾巴说:“他妈的这社会太假了,连出家人都有假的。这社会咋变成这样,除了你的亲生妈妈是真的,再就没有真的了。”
那天,蝎子尾巴认定他们不是和尚,就不再追究他们的责任。两个假和尚和蝎子尾巴成了朋友,他们请蝎子尾巴吃饭,对他无话不谈。他们是老乡。蝎子尾巴说我们是拉人去医院看病的,两个假和尚笑着说:“医托啊,这个早就听说了。”
两个假和尚也告诉了蝎子尾巴他们的生财之道。
他们老家在河南XX县(这个名字不宜公布,江湖中人应该能够猜到这个县的名字),他们说家乡很多男人都做和尚,和他们一样的假和尚。家乡的男人像种子一样撒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当和尚云游四方是他们的工作,他们正月十五过后就出来了,腊月份就回去了。家乡对他们来说,只是驿站。
在这个县城的一些商店里,都能买到和尚的装备,袈裟念珠什么的,还有开光菩萨等等,而在寺庙里则买不到。这个县的很多男人们买到袈裟后,剃光头发,怀揣开光菩萨就上路了。他们想去哪里就去哪里,觉得哪里富裕哪里有钱就去哪里。他们来到一座城市,或者蹲在天桥上给人算命,或者拦住路人说“你有佛缘”。如果你和他搭话,他就会说:“送你一个开光菩萨,保佑你发大财。”如果你接收了,那么不好意思,请菩萨是要掏钱的,一个一百元。到这时候,你的手中已经拿上了菩萨,他说拿上了就不能退还,否则菩萨会怪罪的。怎么办?你只有掏钱了。
这样的假和尚我每年都能遇到很多。他们都操着河南口音。他们见到我就说:“啊呀呀,这位大哥你天庭饱满地阁方圆,最近要发大财,不过有一点点遗憾,需要修正,否则财会走空。”或者说:“兄弟,你最近有一笔横财,但需要人指点。”他们从来不会说你最近要大祸临头,或者遭遇横祸,他们知道说发财会让人高兴,说灾祸则会惹人气恼,弄不好大耳瓜子就会落在脖子上。
更为搞笑的是,有一次,一个假和尚居然说我不出半年就会赚到千万元。我只是一个普通记者,我做梦也不会梦到千万元的。
而每次我和假和尚交谈没有几句,他们就会拿出开光菩萨,要送给我。他们的这种把戏,这些年没有一点点长进。如果你遇到和尚送你开光菩萨,或者要给你算命,你赶快走开。
曾经很多次我看到一些衣着长相都很漂亮的女孩子,坐在假和尚的对面,伸出娇嫩的纤手,让假和尚摸来摸去,而脸上又是异常虔诚的表情,我就忍不住发笑。天下的傻女孩怎么会这么多?
这个县的男人云游四方,这个县的女人也在周游列国,男人做假和尚,女人则跳脱衣舞。
上面这段话不是我说的,是一位高官说的。他在分析这些现象的深层原因时这样说。
还在上世纪80年代,我所生活的那座小县城每年有一个物资交流大会,每年秋天的大会来临时,郊外的空地上就经常有一些歌舞团来表演。节奏强烈的迪斯科音乐声中,帐篷门口的桌子上总有几个穿着三点式的女孩子扭动屁股,做出各种撩人的姿势,一些禁不住诱惑的人就会掏钱买票。
当观众快要坐满帐篷的时候,表演就开始了。当时的很多蹩脚的插科打诨的节目都忘记了,到现在我只记得有一大堆白晃晃的大腿和屁股在眼前不停地晃,那些大腿和屁股开启了我的性意识,让少年时代的我亲眼看到了女人和男人的差别。那时候的我们都把看这种歌舞叫做“上生理卫生课”,我们男同学常常下了晚自习后就相约去看歌舞,有的女孩子问:“你们干什么去?”我们故意大声喊:“上生理卫生课。”一些单纯的女孩懵懂地看着我们飞奔而去的身影,茫然不解;而另外一些有了性意识的女孩则红着脸低下头,相互望一眼,吃吃地笑。
那些女孩的舞蹈动作非常别扭,毫无美感,他们踩着鼓点扭动着屁股,你的手刚刚举到头顶,她的手已经放到了腰间。他们也知道观众来到这里不是看他们的舞蹈,所以她们的舞蹈得过且过偷工减料。台下响起了凄厉的口哨声,还有惊吓一般的尖叫声,她们在亢奋的口哨和尖叫声中走下台去。
我一直不知道这些女孩子来自哪里,她们为什么会选择这种在众目睽睽中脱衣服的表演,很长时间里,我都想当然地把她们当作受害者,被黑社会胁迫着,威胁着,在台上兴奋舞蹈,在台下吞着眼泪。那时候的我总以为妓女都是生活所迫,也总以为这些跳脱衣服的女孩子也受到了黑社会的控制,我无数次地幻想着解救她们,把大衣披在她们赤裸的肩膀上,告诉她们说:“别哭啊,快点回家,妈妈在家等着你。”
(略去3000字,众所周知的原因)
我在同乐搭伴做夫妻,其实,医托里面的夫妻,很多都是假夫妻。他们遇到患者后,就一唱一和,共同编造自己家人有病而在“爱慈医院”治愈的谎言。
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有些对不起同乐,如果她和别人搭伴,可能能赚到一些钱,而和我在一起,我总是故意说些让患者反感的话,让有些心动的患者退避三舍,我不愿欺骗患者,而同乐当然就没法赚钱分红。
我知道同乐对我一直很好,一直默默地喜欢我,可是她不会表达,她经常偷偷地打量着我,一遇到我的眼神,就裂开嘴巴憨憨地笑着,满脸绯红。
有一天黄昏,我坐在房间门口的路灯下看书,其他医托围着院子里的一架黑白电视机津津有味地看着,突然,大家都听到了同乐的叫喊:“李哥,快来接我。”
同乐端着一碗哨子面条,胆颤心惊地走进了旅社大门,面条上飘着一层红红的辣椒油,晃晃悠悠地溢出来,流到了她的手指上,她被烫得吸溜吸溜,眼睛看着面条,小心地迈动着脚步,不知道先把滚烫的面条放在地上。
我跑出去,从她的手中接过面条,她用力甩动着手指,欣慰地笑着说:“李哥,这家面条可好吃了,你赶快趁热吃。”
院子里所有的人都看到了这一幕,他们呵呵笑着,同乐脸上带着幸福的笑容,那种看着我的亲昵的神情,让我既心疼又难堪。
那次过后,有人就故意叫同乐为“李家妹子”,而同乐也大大方方地答应了。她经常会来到我们男人居住的房间里,在别人的哄笑声中拿走我的脏衣服,有时还会把洗脚水端到了我的跟前……
然而,我知道我和她没有结果,我故意对她很冷淡,我说:“你再不要对我这样好。”她笑着说:“没事,我喜欢给你干活。”
我们的关系就连最迟钝木讷的聋子都看出来了。有一次,聋子神情庄重地告诉我:“你有福气啊,你看那女娃子屁股大,以后能给你生小子。女娃子对你实在是太好了,你以后什么都不用干。”
我说:“我不愿意结婚。”
聋子疑惑地问我:“你吃饭后结婚?”他又神色凝重地说:“年轻人啊,说风就是雨,今晚就想结婚?怎么,等不及了?”
我和聋子说话总是说不到一块,我们没有共同语言。
看到苏黎世的笑话,也想起了一个笑话——
教育局长来学校听课,那节课上的是地理课。课间十分钟,教育局长拦住一个学生问:“地球仪为什么是歪斜的?”那个小学吓坏了,赶紧说:“不是我搞坏的。”
教育局长很生气,就把这个学生的话讲给地理老师听,地理老师郑重其事地说:“我作证,那是一个好学生,真的不是他弄歪地球仪的。”
教育局长又把这些话讲给校长听,校长伤心地说:“唉,都怪我们学校没钱,买个地球仪,还是次品。”小旅社里,每天都能看到精彩的闹剧。小旅社是一个社会小舞台,每天都有不同的人在这里表演。在这里,你能够看到各行各业的缩影。
每到周末,小旅社的房间就早早订满了,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附近大学的学生情侣。学生没有多少钱,只能选择这种价格便宜的小旅社。而每到这个时候,小旅社就显得欲望荡漾,激情澎湃,连空气中也充满了勃发的肉欲的气味。每对走进来的大学生都显得蠢蠢欲动,莫名兴奋,却又要极力装出不动声色。他们走进房间后,就关紧房门,很快地,一个个房间的窗缝门缝里,挤出了女孩青春的呻吟声,让听到的每个人都意乱神迷,难以自持。
那几年,钟点房刚刚出现,据说生意一度很火爆,小旅社顺应潮流,也推出了钟点房。和宾馆酒店不同的是,小旅社的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