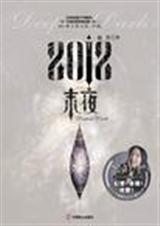暗访十年2-第2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天下曲。”
苏东坡的妹妹苏小妹马上也说了一个谜面:“我有一只船,一人摇橹一人牵。去时拉纤去,归来摇橹还。”
这三个谜语的谜底都是墨斗。
墨斗是什么?墨斗是木匠使用的一种重要的工具,据说是鲁班发明的。而鲁班生活的年代,远在春秋战国。
此后,我给自己的孩子再说这个谜语的时候,再说谜底是墨斗的时候,孩子会不会问我:“什么是墨斗?”
消逝的老行当,承载着我们这代人太多太多温暖的记忆。消逝的老行当,又会留给我太多太多的感伤。
那时候,我们放学后,总喜欢围在铁匠的身边,看着炉火熊熊,铁锤叮当,看着一片毫无形状的废铁在叮叮当当声中变成铁锨,变成锄头,变成一枚铁钉。还有的时候,村口会有爆米花的叫声响起,我们看着爆米花的老人转动着密封的圆锅,一声闷响,雪白铮亮的爆米花滚落出来,我们欢叫着捡拾落在远处的,几粒爆米花就能够让我们高兴很多天。我们最盼望的还是货郎担子的到来,货郎带来的,不仅有我们平常见不到的针头线脑橡皮筋铅笔刀,还有令我们惊讶不已的外界消息。还有修钢笔的,他总会在校园的梧桐树下摆出一串串钢笔配件,我们一下课就会围着他,叽叽喳喳地问这问那,他的口袋里通常会别着三支以上的钢笔,我们的老师就编了一首顺口溜:“别一个钢笔,中学生;别两个钢笔,大学生;别三个钢笔,要么是修钢笔的,要么就是贼娃子。”
而现在,我们再也找不到他们的踪迹。
如今,机器的批量生产代替了传统工艺的精雕细凿,无论是在喧嚣城市的高楼中,还是在偏远乡村的小路上,都再也听不到抑扬顿挫的叫卖声。那些曾经辉煌的老行当,已经走上没落,我们只能在记忆深处,打捞他们模煳的身影;在发黄的照片中,寻觅他们远去的踪迹;在那些岁月磨砺后的沧桑文字中,想象他们曾经的岁月。
长河落日,古道西风,岁月的风尘淹没了那一段历史。若干年后,人们会不会想到,这个世界上曾有过这样一些职业,他们顽强而卑贱地生活着,生活了很多年,终于倒在了工业文明到来前的暗夜里。
工业文明是历史发展趋势,我无意贬低。但是,老行当的岁月挽歌,总让人惆怅万分。
此后,世间再无老艺人。
纺线织布,现在也行将消逝。
母亲说,从棉花到土布,中间要经过很多过程。
棉花成熟后,会开出一朵朵白色的花,将棉花摘下来的过程叫“拾花”。庄户人为了提高速度,通常会将棉花与花瓣一起摘下来,回到家后再将棉花与花瓣一一分离。拾花的时候,每个人的腰间缠着一个大袋子,通常是用编织袋缝成,上面还有诸如“尿素”、“碳铵”的字样。摘下的棉花塞进编织袋里,远远望去,每个人都像身怀六甲一样臃肿不堪,行动迟缓。小时候唱一首歌叫做《劳动最快乐》,我在拾花收麦的时候,感觉不到任何快乐,只感到痛苦。那些说“劳动快乐”的人都是坐在办公室里闭门造车的书呆子,他们从来就没有经历过真正的劳动。
棉花里有棉籽,要让棉花变成土布,先要“拧花”,将棉籽脱离出来。棉籽很油,小时候曾有几个同学因为太饿了,就偷吃棉籽,结果中毒了。
取出了棉籽的棉花,一坨一坨的,像烂羊毛一样,很难看。接着就要“弹花”。弹花是一个很享受的过程,我曾经见过弹花的人,戴着口罩和袖套,拿着长长的弓,弓弦一下一下击打在棉花上,发出镗镗的颤音。粉尘四溅,棉絮飞舞,弹花人置身其中,自得其乐。
弹过的棉花像云朵一样蓬松洁白。这样的棉花就要搓成捻子,拿来一根高粱杆,筷子一样粗细,但比筷子长些,抓一把棉花,裹住高粱杆,放在案板上,一滚动,就成了一条尺多长的长条,抽出高粱杆,这就是捻子了。
接下来就要用到纺车,纺车由木架、锭子、绳轮和手柄4部分组成。小时候,我记得有一幅著名的国画作品叫《周总理的纺车》,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人记得这幅国画。纺车的声音嘤嘤嗡嗡很好听,像夏夜的声音。纺线的时候,左手拿着捻子,右手摇动纺车,捻子一根接一根,纺出的线绵绵不断,粗细均匀。在那时候的农村,纺线是每个女人的必备功课,就像现在的城市女人会涂口红一样。
小时候,如果谁家姑娘纺线好,那就会十里八乡传扬,会成为女孩子的羡慕对象,成为男孩子的追逐对象。那时候,纺线技艺好的姑娘,就像今天的歌星一样。
纺出的线成为圆锥体,叫做“对子”。对子又连成一圈一圈的线团,绵软的线团放在面汤锅里蒸煮,这叫“浆线”,从面汤锅里出来的线很坚韧,这就可以织布了。
织布前还有一个染布的过程,如果不染,就只能织出白颜色的布,这样的布做衣服,只有做孝布,就是“埋人”的时候才能穿出去的衣服,白衣白裤。染布就需要给面汤锅里添加染料,染料可以分为好几种颜色,一般最多的是蓝色和黑色、红色。染料需要购买,我记得那时候的染料都是一小包一小包,外面印着一个手持镰刀怀抱小麦的青年女子,一副“战天斗地”的神情。我不知道,在更遥远的年代,没有“战天斗地”出售,人们依靠什么染布?
因为加了染料,线圈就成为了各种颜色,这样织出来的衣服就是彩色的,女孩子一般穿这样的衣服,我们那里叫“格子布”,花花绿绿的,很好看。而男孩子要么穿蓝色的,要么穿黑色的。我小时候因为经常穿着黑颜色的粗布衣服,被人家叫“黑老汉”。
要把线圈变成布匹,需要用到织布机。织布机是一个很繁复的工具。纺车人人家中会有,而织布机只有那些大户人家才会有。母亲那时候就经常借人家的织布机来织布。织布机很大,比一个成年男子还高,结构也很复杂。织布的人坐在织布机的前面,梭子左右回旋,一忽儿左手,一忽儿在右手,梭子是空心的,里面放着线团,那线团的线头就从梭子的一头的小孔里穿出来,每穿过去一次,就用另外一个没有拿梭子的手把那横着的一个带线的挡板“哗啦”一下往自己的怀里拉一下,梭子左右回旋,挡板前后推挡,脚下还要踩踏着琴键一样的踏板,双手配合,手脚互动,不断地重复着这个单调而很有难度的动作。梭子吐出的是经线,挡板穿过的是纬线,这样经线和纬线交织在一起就能织成布匹了。
织布机纺线机只有女人才会使用,而犁地播种只有男人才能掌握。几千前来,男耕女织的农耕文明就是这样一步步走到了21世纪,走过了几千年。而现在,我们只能望到它苍凉的背影。
犁耧耙耱,纺线织布,碾盘磨盘,皮影风箱,木匠瓦匠……他们贯穿在我们童年生活中,让我们的童年变得古朴而精彩,他们与青山绿水紧密相连,与童话梦幻息息相关,而现在,他们远去了,他们消逝了,从我们的生活中消逝了,不留任何痕迹。我们伸出手去,想挽留他们,然而手中握住的,只有冰凉的记忆。
我之所以大段大段不厌其烦地描写这些消逝的时光,是因为自我之后,描写他们的人肯定愈来愈少,很有可能我是最后一批描写他们的人,或者是最后一个如此详细描写他们的人。生活在现代工业文明社会中的人们,将会渐渐遗忘他们。这些染着头发满嘴英文的少年人,连文革浩劫都能遗忘,更何况这些粉尘一般飘渺的记忆和忧伤。
回家后的第三天,我来到了曾经工作过的县城,办理相关证件。我没有想到,我在这里居然遇到了传销。
因为我的户口还在这个县城的城关镇,我便来到城关镇的某个部门办事处来办理相关证件。办理证件的是一个30多岁的男子,满脸横肉,已经有了双下巴,一副肠肥脑满的贪官形象。他的神情很倨傲,带着那种小地方工作人员不知道天高地厚唯我独尊的骄横和自鸣得意。
我的前面还有几个人在等待办理证件,一个女孩子排在最前面,估计也是和我一样的背井离乡的打工者,她怯生生地看着双下巴。双下巴斜睨了她一眼,头也不抬地说:“交钱,120元。”
女孩子小声问:“怎么就这么多钱?”
双下巴轻蔑地说:“你交不起钱就不要办,下一个。”
女孩子赶紧说:“我办啊,给你钱。”
女孩子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零钱,数了数,交给了双下巴,双下巴把证件填写好后,扔给了女孩子,连收据发票都没有开。
接下来的几个人也都是交了120元,才给了这样一个小小的只有几页纸的证件。他们也同样没有拿到收款收据之类的证明。
快要轮到我的时候,门外突然走进了一个女人。她叫着双下巴的小名,显得很熟稔。她插在我的前面,连我看也没有看,就把一张一寸照片交给双下巴,双下巴熟练地填写盖章,将证件交给了她,她递给了双下巴20元钱。
这一切我都看在眼中,但是我没有吭声。
女人出去后,双下巴把手臂放在了柜台上说:“交钱。”
我问:“多少钱?”
他冷冰冰地说:“120元。”
我问:“凭什么要收120元?你们的收费标准让我看看。”
双下巴显然很惊讶,他没有想到会有人这样对他说话,前来办理相关证件的都是出门去南方城市的打工者,而那些打工者都是这个北方县域的农村人,一贯忍受种种不平和欺压而不敢吭声,他没有想到会有人敢于这样对他说话。他显然很震怒,他梗着脖子说:“我就这样收费了,怎么了,你爱办理就办理,不爱办理就滚一边去。”
我非常气愤,但是表面上还很平静,我说:“我看到刚才有人办理证件,你只收取了20元,凭什么我就要交120元?”
双下巴显然激动了,他脸红脖子粗地说:“她是我的熟人,对待熟人,我想收多少就是多少。”
小县城小乡镇办事,确实相当一部分都是依靠熟人,没有熟人,什么事情都很难办理,我在小县城当过几年的公务员,我有深切的体会。想起有一年,我刚刚大学毕业,遇到交警在街上戒严,而我当时着急去上班,看到有人骑着自行车从大街上穿过了,也跟在后面想穿过,却被交警一把抓住了,我问:“为什么那个人就能走,我就不能走?”交警横眉冷对地说:“那是我的熟人。”然后将我一把推到了街边。那名交警还洋洋得意地对另外一名交警说:“笑话,居然问我这样幼稚的问题。”我至今还能记得那名交警的容貌,肤黑如炭,瘦如蚂蚱,面目异常狰狞,鼻孔下是肮脏的鼻毛。
然而,今天老子偏就不信这个邪,老子在南方闯荡了两年,什么人没见过?比他官职大过很多倍的人都见过,那些人都态度和蔼,能够与我平等对话,那些人说话都有理有据,合情合理,从来不会仗势欺人。今天,老子就要和这个肠肥脑满的家伙斗争到底。我心平气和地说:“你们收费,是要有物价局颁布的收费标准,请你拿出来。”
双下巴蛮横地说:“你算老几?你说拿出来就拿出来?我凭什么给你看?”
我当时很错愕,如果不是亲眼看到,我实在不敢相信,居然还有这样的工作人员。我一下子火冒三丈,我拍着柜台,指着他的鼻子说:“我算老几?老子没有离开县城的时候,级别比你高,贡献比你大,你去县委政府大院打听打听,问问老子是谁。老子现在离开了,照样比你级别高,比你贡献更大。我们政府的形象就是败坏在像你这样的败类手中。你等等,会有人来找你的。”
我看到双下巴激动地站了起来,神情尴尬地问:“你……你是谁?”
我没有回答,我摔门而出,在所有人惊愕的目光中,拦住了一辆出租车,我对司机说:“去政府大院。”
那时候,我经常来政府大院办事,所以对政府大院的布局结构非常熟悉,我径直来到了县长办公室,两名政府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没有来得及阻拦,他们站在县长办公室门口,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
我以前就认识县长,不过他不会认识我。我在离开的时候,县长刚刚从外地调来一个月。我给县长说了我刚才遇到的情况,县长神情很惊讶,他打电话叫来了局长。局长局促不安,在县长的面前连坐也不敢坐。这个局长我没有见过,后来听说是从乡镇刚刚提拔上来的。
局长说:“这个事情我还不知道,我一定去查一下,多收的钱,也会尽快退还。”
我跟着局长离开了县长的办公室,上楼梯的时候,我看到局长在偷偷地抹去额头上的汗珠。
坐在局长办公室里,门来走进了一位办事的工作人员,他看到我很兴奋,热情地问这问那,然后给局长介绍说:“这是咱这里的笔杆子,以前是XX局副局长,也是我们县的拔尖人才,马上就要成‘转正’了,前年却辞职不干了。”
局长也感到很意外,他非常热情地拿出香烟让我抽,一再向我道歉,然后喊来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让打电话把双下巴立即喊过来。
十几分钟后,双下巴来了,面如土色,两股战战,汗出如浆,局长一阵咆哮,像训斥儿子一样。双下巴再也不敢神情倨傲了,他答应以最快的速度给我办理。
十几分钟后,双下巴收取了20元钱,给我办理了相关证件。
后来,我听人说,双下巴受到了处罚,调离了这个工作岗位。
那天下午,就在我回家的车上,突然接到了一个传唿,传唿上是一个陌生的电话号码,我用自己的手机拨打过去,居然是刘芸。刘芸说,她在南方一座海边城市里,正做大生意,和别人合伙开发一座位于内蒙古的大型山林,邀请我加入。
我简单地询问了几句。刘芸说,他们的山林已经在国家有关部门备案,马上就要开发,目前缺少的是资金,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