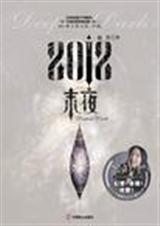暗访十年2-第2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还有我们记忆中的童年。田园牧歌,鸟语花香,流水潺潺,绿草如茵,还有泥土的芳香,燕子的剪影,野花点缀的旷野,日之夕矣,牛羊下山……以后,我们只能在那些古典诗歌中才能寻找到它们的足迹。
我们生活在工业文明中,工业文明中充斥着冷冰冰的机器,冷冰冰的机器拒绝浪漫和温情谢谢关心我的朋友,你们实在是对我太好了。
前两天签了出版合同,在签合同的前夕,犹豫了好多天,该不该签,敢不敢签?后来想,既然是让大家看的,让大家防骗的,就不怕什么了。签!
我就不信那些坏蛋敢来找我,我就不信他们能够找到我。
书籍出版的时候,用李幺傻的名字,书籍中不出现我的真实姓名。书籍出版后,不接受任何一家媒体采访(如果真的会有人想采访的话),不会向任何一个人透露这本书是我写的。
截至现在,知道这个帖子是我写的,只有我的妻子。母亲不知道,弟弟妹妹不知道,同事更是没有一个人知道。我担心家人担心,也担心同事会泄露出去。
我生活很好,每天上班之余,看看书,写写文字,大街上散步,日子很悠闲自在。
谢谢关心我的所有朋友们。匣中剑0003,您好。
西北农村很多地方安葬死者的时候,都会请龟兹。龟兹里有吹唢呐的、敲小鼓的、拍击跋的。他们一路吹吹打打,从死者家中一直到坟地里,那种凄凉的音乐让人心颤。
这些人都是固定的几个人,有出殡的时候,就出去,挣点零花钱;没有出殡的时候,就各回各家,耕种田地。
唢呐的声音高亢刺耳,声如裂帛,平时是不能吹的,否则会带来灾祸。所以,学习吹唢呐的人,都会躲在深山里吹,还不能被人听到,听到的人会有灾祸。
龟兹这两个字我一直不知道怎么写,也是后来才从书本里看到,龟兹是从唐朝的西域引进的,历史真可谓古老啊。
我还听说唐朝西域有一个名叫龟兹的地方,这种音乐就是因地而名,不知道对不对。
中华民族发展这么多年,很多古老的习俗传播到了中原江南就发生了变异,只有在偏远的西北还保存了下来。西北五省广为流传的秦腔,据说是苏武牧羊的时候,心生悲愤,嘶声呐喊,后来演变成了秦腔。陇东皮影可以追溯到秦二世。陕西最有名的面条岐山臊子面,据说当时是周文王周武王的军粮,为姜子牙所发明。而西北著名的锅盔,可以上溯到韩信的楚汉相争时代。手有馀香兄弟,谢谢你对这个帖子如此偏爱。看到你的文字,我感觉鼻子算算的。这个帖子是我们大家的孩子。
不管出版不出版,我都会把帖子一直写下去。说真的,出版了,除过我的妻子知道这书是我写的,再不会有人知道,咱不图名。出版了,就那么一点稿费,对咱来说,也多不了什么。咱写这书图什么?图的是给自己这些年一个交代,一个总结;再图什么,图的是认识了这么多的好朋友,好弟兄,每天都能在这里看到;图的是让更多人不要上当受骗。
所以,帖子会一直写下去。
我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是午后,母亲在院子里织布,村中另外两个姨娘在纺线。现在,在南方,早就进入了机器化大生产,衣服成批量生产,每个制衣工厂成千上万,谁还会要这些土布衣服?
母亲她们三个人边干着手中的活,边唠着家常,还动不动就会唱起歌曲来,都是在教堂里学会的歌曲。歌声缓慢悠长,绵绵不绝,让人听了很忧伤。
我问母亲:“织这么多布干什么?”
母亲说:“有的人家中困难,买不起床单被罩,教友们就织布做好,送给他们。”
母亲又说:“神父让帮主穷苦人,有钱的出钱,咱几家没有钱,就织些布送过去。”姨娘们看着我,都善良地笑着。
奉献是快乐的。我从母亲和姨娘身上看到了。
走进房屋,我看到了父亲的照片悬挂在桌子上方。那是父亲此生唯一的一张照片。这张照片,还是我带着父亲去省城治病的时候,父亲、母亲和我一起拍摄的。
父亲唯一的一张照片,当时加洗了几张,我们兄妹三人一人一张。我一直珍藏着父亲这张照片。我无论走到哪里工作,都会带在身上。
后来,我有了女朋友,女朋友第一次看到父亲的时候,惊叹道:“老爸真帅啊。”
父亲身高一米八,身材魁梧,五官端正,充满力感。多年的体力劳动,给予了父亲一副健壮的体魄。
父亲确实是很帅,我记得小时候跟着父母去看老戏。西北农村极度缺乏文化生活,焦苦的生活让人们食不果腹,衣不御寒,哪里有心思考虑什么精神享受。每年麦子收割入仓,庄稼人能够闲下来几天,这时候就有戏班子来到。戏班子并不唱戏,而是皮影。那时候也没有人敢登台唱戏,登台唱戏属于封资修,是会像福海妈所说的“无产阶级的铁拳砸碎你”。皮影戏一来,万人空巷,整村整村的人都会来到戏台下观看。皮影戏的内容也都脱胎于“八个样板戏”,什么《红灯记》呀,《龙江颂》呀。皮影这种古老的艺术形式,现在也消失了,它只在像《活着》这样的电影里才会出现,而最后一代皮影老艺人,都在文革中个文革后先后辞世。
皮影是一些人物道具,表演的时候,灯光照在皮影上,皮影的影子映照在白布上,表演的人手持皮影,口中吟唱,手指翻动,皮影就会在二胡笛子和锣鼓的节拍中,亮相登场。皮影忽而在台上扭捏作态,忽而在台上打打杀杀,台下观众如痴如醉,连声叫好。而皮影所有的动作,都在皮影艺人十个手指的掌握中。那时候,电影只有有限的几种,《苦菜花》、《铁道游击队》、《渡江侦察记》等等,一年难得遇到一次。倒是皮影每年麦收后会准时出现,而皮影来临之日,就是全村农民欢声雷动之时。
父亲说过,皮影有两种,一种是举在手中的,一种是吊在手中的。前一种叫“州葫芦”,后一种叫“吊葫芦”。读音是这样,但是字不是这样写。字到底怎么写,估计现在没有人知道了。
记得有一次,皮影结束后,我们走在回家的路上,母亲爱恋地对父亲说:“戏台子下,只有你最好看。”还有一次,父亲看戏的时候,和几个插队知青站在一起,那几个从城市里来的女知青悄悄地说:“这个大个子真英俊啊。”我问父亲:“什么是英俊?”父亲笑笑没有说话。父亲的那张照片是58岁的时候拍摄的,他58岁的模样,还让我的女朋友如此惊叹。
父亲离开太早了,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父亲得了重病,无钱医治,离开了我。在我生活好转起来,想对父亲尽孝的时候,却与父亲生死相隔。
听母亲说,父亲有过多次跳出农门的机会,可是,他自己要么放弃了,要么被人整治了。所以,他就一直当农民。而母亲的这些话,又是从爷爷那里听到的。我很小的时候,爷爷就去世了,印象中的爷爷很高大,却又很精瘦,他饿得肋骨根根凸起,两颊塌陷,他终于在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前去世了,他终于没有能够吃上一顿饱饭。爷爷去世的时候,父亲哭得很伤心。那是我今生见到的父亲唯一的一次哭泣。
那时候父亲和母亲还没有结婚。有一年,父亲赶集的时候,看到公社门口围了很多人,一打听,原来是炼油厂在招工。父亲回去后,就在大队报名了。那时候还没有现在这么多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父亲家庭成分贫农,又老实勤恳,公社也批准了,炼油厂也录取了。就在父亲准备去当工人的时候,堂弟找到了父亲,缠着要让父亲把这个名额让给他。父亲的堂弟上过两天学,脑子比父亲灵光得多,他早就看出了当工人后的优越地位。那时候有口号说:“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是毛主席说的。那时候毛主席“一句话顶一万句”,毛主席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于是,几百万城市青年就去了农村,把农村搅得鸡飞狗跳,而他们自己也成了“被耽搁的一代”。那时候,从上到下,全凭领导人一句话,领导人说是什么就是什么,别人根本就不能插嘴,一插嘴就成了反革命。农民给地里种什么也要听革委会主任的,而革委会主任都是些白面书生,根本就没有种过地。革委会主任说:“今年平地种包谷,坡地种豌豆”,你如果平地种豌豆,坡地种包谷,你就是反革命,你就是破坏农业生产。村里人曾经说过:“那些年为什么那么穷?一是大锅饭,干瞎干好一个样;一是瞎指挥,没种过地的指挥种地能手。这样的日子能过好,太阳就从西边出来了。”
那时候有一句话是说姑娘择偶的:“一工二干三教员,宁死不嫁庄稼汉。”工人排在第一位,干部第二位,而农民则是最后,人家宁肯上吊也不嫁给你。
那时候,叔叔姑姑们都还小,挣不了工分,挣不了工分,全家就分不到粮食。父亲最后就放弃了,让堂弟去了炼油厂上班。现在,炼油厂不叫炼油厂,叫“中石化”,中石化是中国最有钱的国有企业。父亲的堂弟在中石化退休的时候,工资拿到了好几千。
还有一次,是征兵,那时候叔叔姑姑们都能够下地干活,能够当一个壮劳力使用了,父亲又去应征,顺利过关。第二天就要去公社报道了,父亲前一天下午去生产队告别,队长就说:“站好社会主义农村最后一班岗。”安排父亲在打麦场站岗,查看是否有人偷麦子。那时候的人都非常穷,除过福海妈这样的干部,全村人都吃不饱肚子。每年小麦收割回来,放在打麦场,统一碾场,夜晚,把麦粒堆放成上小下大的矩形,盖上木印,防止偷盗。偷盗盖上了大印的小麦,是要被判刑枪毙的,谁也没有这个胆量,但是社员们有别的办法,一些人走进打麦场的时候,就会穿着比较大的鞋子,在麦粒还没有盖印的时候,他们边干活边把双脚踩在麦粒堆上,这样,鞋子里就会灌上一些麦粒,顺着脚面滑到脚底。然后,他们踩着装着麦粒的布鞋,忍受着硌脚的痛苦,面容上还要装着很平静地走回家去。回到家后,将鞋子里的麦粒倒出来,会有半斤重,而这半斤麦粒,可以蒸两个馒头。
父亲在站岗的时候,看到有人走路的姿势不自然,神色也不自然,父亲知道他们的鞋子里肯定有麦粒,但是父亲没有声张,那时候的社员都穷得叮当响,父亲不忍心当场抓住他们。这几个社员走过去后,突然,福海妈不知道从什么地方闪出来了,福海妈像猛兽一样扑过去,从他们的脚上摘下鞋子,每个鞋子里都有麦粒。
福海妈举着这样的鞋子,像举着一面面胜利的旗帜,她义正词严又歇斯底里地质问父亲:“这是什么?你是怎么站岗的?你这样的人能当解放军吗?让你给社会主义站岗,你能把美帝国主义,把苏联修正主义全部放进来。多亏我抓住了你,不然,你就会颠覆我们社会主义国家。”
这件事情的结果是,父亲不但没有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而成为了农村的专政对象,每逢开会的时候,父亲就会和那几个偷了麦子的人站在台子上,作为反面教材遭受批判。
此后,父亲只能老老实实在家做农民。
那一年,我们这里的军人都去当汽车兵。全大队去了两个人,一个留在了部队里,做汽车教员;一个转业回来了,在一个政府部门开小车。
母亲在房檐下织布,织布机噼啪响着;姨娘们在织布机边纺线,纺车嗡嗡地叫着,这声音曾经非常熟悉,让我仿佛回到了童年。那时候,我夜晚临睡前,总能看到母亲在摇动纺车,母亲的身影被昏暗的煤油灯光照在墙壁上,显得非常高大。母亲右手摇动着纺车,左手抽动着捻子,仿佛在舞蹈一样。经常地,我夜半醒来,还能看到母亲在纺线。而天亮后,我背着书包去上学,母亲扛着锄头去下地。
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母亲和姨娘们织布纺线,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这种温馨而古老的劳动场景。来自南方服装厂的成衣异常便宜,春夏秋冬,款式新颖,合体漂亮,尽管有些衣服可能就是带着各种病菌,从沿海运来的洋垃圾,但是,西北农民并不知道这些,他们只知道这些衣服很便宜,而便宜是他们选择衣服的最重要的标准。
土布衣服,被人们遗忘在历史的深处。
我曾经专门问过母亲土布是如何制作的,母亲这一辈人,是至今还掌握着土布工艺技术的最后一批人。这些年,多少老行当唱着凄凉的挽歌,在无人问津中无奈消失:铁匠、木匠、瓦匠、泥水匠、裱煳匠、箍桶匠、补锅匠、剃头匠、磨刀匠……还有陶工、修钢笔的、货郎担子、弹棉花的、卖爆米花的、流动照相的……
“拉大锯,扯大锯,姥姥家里唱大戏。接姑娘,请女婿,就是不让冬冬去。不让去,也得去,骑着小车赶上去。”这首儿歌名字叫做《拉大锯》,还有一个外表黄色的谜语也是说拉大锯的:“两人对着干,围着一条线,干得满头汗,脱了衣服干。”后来的儿童们,再也听不到这首儿歌了,即使听到了,也会懵懂不知,莫名其妙。
“张打铁,李打铁,打把剪刀送姐姐,姐姐留我歇,我不歇,我要回去打毛铁。”这首儿歌说的是“铁匠”。后来的孩子一定会问,剪刀怎么就能打出来?什么叫做毛铁?
“陶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十指不沾泥,鳞鳞居大厦。”阅读到这首古诗的孩子们,不知道描写的是陶工,知道了是陶工,又不会知道陶工是干什么的。
很小的时候,做木匠的伯伯就给我讲过这样一个传说。宋朝的时候,有一个人叫秦少游,他出一个谜语给大诗人苏东坡猜。谜面是:“我有一间房,半间租与转轮王,要是射出一条线,天下邪魔不敢挡。”
苏东坡心中有数,却装猜不着,另作一谜让秦少游猜。谜面是:“我有一张琴,琴弦藏在腹。凭君马上弹,弹尽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