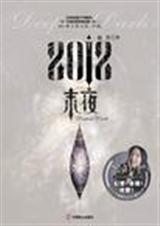暗访十年2-第2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道,可是,她总是颠三倒四,要么幸子走进了霍元甲里,要么许文强和赵倩男结婚了……
那几年里,村里家家有余粮,很多人家盖起了砖瓦房,可是福海妈一家人总是吃不饱穿不暖,青黄不接。
又过了几年,福海妈开始给人说媒了,她依靠着文革中练就的嘴皮子,走东家串西家,也能混个肚儿圆。
但是福海和海燕都三十好几的人了,还是没有媳妇。
我考上大学参加工作后,就很少回家,所有关于村里人的消息,都来自同村人的转述。
妮子说,福海曾经有过一个媳妇,被福海妈打跑了。
有一年,福海在山沟里砍柴,听到一个黑窟窿里传出微弱的唿救声。是个女人的声音。
西北干旱少雨,可是夏天却常常有暴雨,几场暴雨就把一年的雨水都下完了,所以,西北农村家家有水窖,水窖就是为了储存雨水,以备全年人畜饮用。暴雨把西北农村冲刷得千疮百孔,沟壑纵横,沟壑间留不住草木,即使有草木,也会被暴雨冲刷干净,或者被漫长的干旱旱死。中国最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在西海固,西海固在宁夏,宁夏在西北。而西北还有很多和西海固一样的地方,至少我的老家就是这样。
窟窿也是暴雨冲刷的结果。窟窿有深有浅,又长又短,最深的足以与天坑相比。不过,天坑已经引起了地理学家的研究,而窟窿还为外界所不了解。长的窟窿据说可以达到几十里,从这头钻进去,那头出来,就到了邻县的地面了。
窟窿里面是非常恐怖的,因为没有人迹,又加上雨水囤积,所以野草生长茂盛,而郁郁葱葱的野草中,又有着无数的各种各样的多足昆虫。西北农村的人可怜,动物昆虫也可怜,哪里有野草树木,它们就聚居在哪里。
小时候,我们非常调皮,但是从来没有人敢于溜进窟窿里探险,窟窿里是一个阴暗阴森的恐怖世界。
而这样的窟窿里怎么就会有女人的声音?
当时,福海站在窟窿上问:“你是谁?”
窟窿里的女人声音微弱地说:“我是逃难的,救救我。”
福海喊道:“救你可以,但你要做我的媳妇。”
处于困境中的女人答应了。
接着,福海放下绳子,让女人捉住,吊她上来。可是,连续几天的饥饿,让女人没有了力气。
于是,福海跑回村庄,喊来了几个小伙子,人们拿来了更长的粗绳,还有水和蒸馍。落入窟窿中的女人终于得救了。
女人实践了自己的诺言,嫁给了福海,还给福海生了一个女儿。
听村里人说,那个女子是逃婚迷路掉进了深窟窿里。她没有想到,从深窟窿里出来了,却掉进了另一个窟窿里。
福海妈对这个天上掉下来的媳妇非常不好,动不动就拳脚相加,有时候还用撅头把打,撅头把都打断了好几根。媳妇遭到殴打的原因只是,没有生下儿子。
村里人愤愤不平,每次福海妈打媳妇的时候,人们就涌进门去,阻拦福海妈。
后来,福海妈打媳妇的时候,就脱下臭袜子,堵住媳妇的嘴巴,然后死命地打,福海和海燕脑子都不灵光,居然帮着他妈打。媳妇的身上经常有伤,还不敢给村里人说。
再后来,媳妇趁去地里干活的时机,偷偷地跑了。他们没有领结婚证,也不知道媳妇家在哪里,跑到了哪里。村里人都说:“这一家人,该啊。”
我参加工作后,有一天回家,看到村口挂着挽障,挽障下放着一个方桌,放桌上放着一颗猪头,这种仪式只有在埋人的时候才会有。我一打听,原来是福海妈死了。
西北农村埋人的时候,一般都会请“龟兹”——就是一群吹吹打打的人。可是那天村里出奇地冷清,听不到唢呐声。村人说,福海妈死了,他们两兄弟没有钱埋人,是村子里的人凑钱埋了他妈。
福海妈死了,福海和海燕日子过得更是一天不如一天。
后来,听说这一对老兄弟还有了小偷小摸的毛病,他们不好好伺弄自己家的土地,却打上了别人家土地的主意。谁家地里的蔬菜长势喜人,第二天早晨必定会少几颗;谁家的红薯快要挖了,第二天肯定少了几窝。这事,不用问,就是这老兄弟两个干的。但是,村里人看到他们生活恓惶,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知道了装着不知道,看到了装作没看到。
然而,谁能想到,他们居然变本加厉,偷起了药材。
我们那里的人,种庄稼之余,也搞点副业:挖药材、勾槐米、逮蝎子。
挖药材,要走遍沟壑山峁。西北草木极少,药材更少。
勾槐米,就是勾下槐树上的槐树籽,趁着快要开花的时候勾下来,可做药材,开花则就不能用了。槐树只生长在西北几个省,西北主要生长白杨树——茅盾曾经写过《白杨礼赞》,泡桐树,榆树等等一些耐旱的树木,槐树很少。
逮蝎子,就是夜晚在埝畔沟底转悠,提着马灯或者矿灯,看到蝎子就用镊子夹进罐头瓶子里。野生蝎子也是中药材。南方人还喜欢煲蝎子汤,据说食后活血化瘀,强壮筋骨。蝎子也是很少,只有在年代久远的崖头上、土缝里才有。
每隔一段时间,就有骑着自行车或者摩托车的外地人来到村子里,收取药材。他们以极低的价格收取,以很高的价格倒卖。而村里人由于信息不畅,并不知道这些药物的真实价格。
为了保持药材的新鲜,村里有人挖到药材后,就放在红薯窖里,红薯窖阴凉潮湿,可能会增加一点重量。而海燕就盯上人家的药材,从红薯窖里偷取。
这事传出去,人家就开始防备这贼娃子,也没有再同情他们了。此后,村里人只把一些自己孩子穿剩下的衣服鞋子送给福海家的女子,而对懒惰的他们,置之不理。
人活到了这种份上,早就超脱了,这老兄弟不在乎村人怎么看他们,他们依然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贫穷而快乐着。
我看到了福海和海燕,心生悲哀,就把一包刚拆开的红塔山香烟给了他们,还把身上的几十元零钱给了他们。他们理直气壮地接过东西,连一句感激的话也没有,好像这一切都是理所应当的。
我想,当时在村子里叱咤风云的福海妈,看到自己这两个晒太阳的儿子,不知道将会做何感想。
这次回家,我的感触很深,我总是在兴致勃勃地描写自己家乡的故事。家乡的每一件哪怕是最微小的事情,也能拨动着我的心弦。我对家乡充满了感情。
其实,尽管我考上了大学,尽管我在城市里找到了工作,尽管我坐在高档写字楼里上班,然而,我感到自己骨子里还是一个农民,我对农民有着异常深厚的感情,对农村有着异常深厚的感情,对土地有着异常深厚的感情。
我走在村外的小路上,看到有架子车迎面走来,架子车上套着牛,一个十岁左右的孩子牵着牛,牛木讷地走着,走得很缓慢,似乎很不愿意,牛的后面走着一个老人,老人头发胡子都白了,驾着车辕。他们在拉粪。
我想起了我小时候的生活,那时候每年放暑假寒假,我就在不停地拉粪,一车又一车地把牛圈里搅拌着黄土的粪便拉到田地里。我们家的田地都很远,而且全是沟坡地,路很不好走。妹妹牵着牛,我驾着车辕,我们一个上午拉三架子车,下午拉三架子车。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的胳膊因为长时间提着车辕,已经不能动了。那时候父亲和母亲在离家十多里的粮站里缝补麻袋,一天能赚十元钱。回家的时候,就已经很晚了。缝补麻袋,也只有靠关系才能进去做。
有一次夜晚拉粪,还遇到了狼。那时候弟弟很小,夜晚一个人不敢在家里呆,我就把他放在架子车的车厢里,拉着他走。那天晚上,弟弟突然说:“哥,埝畔上有个狗。”我一看,头皮发麻,头发根根竖起,那分明是只狼,夜晚的山沟里怎么会有狗?月光照在狼身上,狼的耳朵竖起很高。距离我们只有几十米远。那时候的农村很少有狼狗,都是笨狗。笨狗的耳朵耷拉下来,而狼的耳朵竖起来。我心中惶极了,怕极了,可是身边还有未成年的妹妹和弟弟,我不能表现出害怕的样子。我悄悄给弟弟说:“你下来,走在牛的套绳中间,也就是牛与架子车连接的两条绳子中间,这样,前面有牛,后面有我,狼就没有可乘之机。弟弟很听话,走进了套绳中间。我从车上拿下铁锨,铁锨是用来将车上的粪扒下来的,现在成为了我对付狼的工具。牛也发现了狼,它唿唿地喘着粗气,两个犄角高高竖起,我让妹妹抓住牛鼻绳,就是穿过牛鼻子的细绳,这样牛就不会逃窜。妹妹的手中拿着鞭子,鞭干有两尺多长,这是她对付狼的工具。我悄悄对妹妹说:”把牛抓紧,往回走。〃
我们慢慢地走离了地头,狼在后面悄悄跟着。我一手架着车辕,一手抓着铁锨。我不敢回头看,听妈妈说,狼很聪明,你如果一直看着它,它就知道你胆小,就会扑过来。我们走出了几十米,狼在后面跟了几十米。弟弟抓着牛尾巴,妹妹抓着牛鼻绳,牛也很听话,一路都在配合着我们。我紧张极了,浑身汗水,能听到自己剧烈的心跳声。就这样,我们一路胆战心惊地走着。后来,快走到村口的时候,遇到来找我们的父母,我一下子瘫倒在了地上,妹妹和弟弟放声大哭,狼一溜烟地跑进了庄稼地里。
那一年,我上初二,妹妹上小学四年级,弟弟还没有上学。
那些年里,我在农村学会了做各种农活,如果我现在是一个农民,一定是一个好农民,就像父亲那样,是一个做庄稼的行家里手。
粪拉到了地里后,用铁锨一掀一掀地撒匀,然后就开始犁地。犁地的时候,就要用到犂。前面牛或者马拉着,后面走着庄稼人,一手扶着犂把,一手拿着鞭子。鞭子一声脆响,牛或者马就欢快地走起来。西北农村马很少,种庄稼全靠牛。所以,农民和牛的感情很深。我们家那头老牛死的时候,父亲让人抬着埋在了地里,自己整天没有吃饭。他把牛当成了自己家中的一口人。
犁地的时候,犂的后面往往走着孩子,孩子的手中拿着小笼。沉睡了一冬的土地,在犂片的两边,像波浪一样翻卷,也会把小蒜或者深埋的红薯翻卷出来,小蒜很像小葱,但是味道辛辣,个体更小,是很多庄户人家的蔬菜。而红薯则是前一年冬天没有挖净,还深埋在冻土里。有时候,冻土层里还能翻挖出冬眠的田鼠,孩子们就放下笼,欢天喜地地追赶。然而,田鼠狡兔三窟,孩子们往往空手而归。
犂完地后,就开始耙地,亮光闪闪的耙齿会把大的土疙瘩切割成小块,因为大的土疙瘩会压住种子,影响庄稼生长。耙地结束后,还要耱地,将土地磨得平整干净。小时候,我们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坐在耙上或者耱上,让牛拉着在田地里转来转去。农村的孩子没有机会坐汽车,只能把耙和耱当成交通工具。
土地平整后,就要开始播种,春天播种玉米、高粱、谷子,秋天播种小麦。播种的时候,要用到一种叫做耧(念lou)的农具,现在,这个工具也行将消逝。
摇耧是农村里最讲究技术的活路,一个村子里也只有几个人能做这个。耧的外形像架子车,只是没有轱辘,下面是四个像耩子一样的东西,却又比耩子小得多。摇耧播种的时候,前面是几个人,拉着绳子,后面是摇耧的把式,他的手上下摇晃,就将种子撒播在了犂沟里。把式会将种子撒播均匀,而一般人撒播的种子,要么太稠,出苗后庄稼长不开,要么太稀,影响产量。西北农村把不会摇耧的人叫“里巴耧”。
种子撒播后,庄稼人终于能喘口气了,然后就等待收割。收割的时候,是一年最忙碌的季节,那简直比飞夺泸定桥还要紧张激烈。每年夏季,我最害怕的就是收割,手持镰刀,走进麦地里,头上烈日炎炎,能够晒得身上起皮;脚下是望不到头的麦子,一行行,一垄垄,总也割不完。镰刀钝了,腰杆直不起来了,嘴唇干裂了,而太阳还没有落下去,一张张被汗水浸泡的脸抬起来,喃喃地叫着:“水,水……”
田地里,麦子打成捆,装在架子车上,走在狭窄崎岖的山路上,一车一车拉到打麦场里,然后堆成垛。等到麦子基本上都收割了,就开始“碾场”。将麦子摊放在平整坚硬的地上,牛拉着碌础,一圈一圈地走着,人牵着绳子,站在圆心。麦粒被碾出来了,开始“起场”,将压扁的麦秆堆成蘑菇样的麦秸垛,将麦粒装进麻袋里,储藏起来,交过公粮后,剩下的就是自己一家全年的口
粮。
麦粒要变成面粉,还有一个过程。
将麦粒徐徐倒进磨盘的眼中,两扇磨盘叠加,上面的转动,下面的不转,上面的磨盘中间插着一根棍子,人推着,就会慢慢转起来。麦粒进入两扇磨盘的中间,在挤压中变成齑粉,用笤帚慢慢扫,慢慢分离,外面破碎的表皮,就是麸子,一般用来喂牲口,困难时期,也有很多人吃这个;里面的粉末状的,就是面粉。
与磨盘相对的是碾盘。碾盘是用来碾红薯片的。红薯挖出来后,用“叉子”——一种刀片插在木片中的工具——切割成薄片,晒干,堆在碾盘下,碾盘滚动,红薯片就会被碾为齑粉,这就是红薯面,可以用来做成粉条,也可以用来蒸馒头。这样的馒头很难吃,吃在嘴巴里,就像嚼着沙子。困难时期,人们都是依靠这种恶劣的红薯馍来充饥。
现在,这些用来制作粮食的农具都消逝了。而那些耕种的农具,也即将消逝。
消逝的不仅仅是农具,还有农耕文明,还有一段承载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苦难历史。
还有我们记忆中的童年。田园牧歌,鸟语花香,流水潺潺,绿草如茵,还有泥土的芳香,燕子的剪影,野花点缀的旷野,日之夕矣,牛羊下山……以后,我们只能在那些古典诗歌中才能寻找到它们的足迹。
我们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