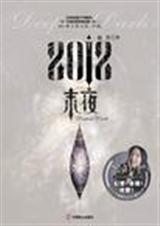暗访十年2-第1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是……”她的脸上挂着与她的年龄极不相称的故意做出来的严肃,她说话的时候故意不看你的眼睛,而看着你头顶上的某一个地方,这是为了显示自己的老练和成熟。这样年龄的女孩子,应该坐在大学校园的湖边读着弗洛伊德或者琼瑶的书籍,应该拿着饭盒走在通往食堂的林阴道上,应该奔跑在女生宿舍楼道里,而现在,这个女孩子居然对着能够做她姨妈的阿香发号司令,对着能够做她大哥的我颐指气使。她的眼中,她的脸上都是轻薄和傲慢。她对我们视而不见。
她说:“我们医院只和报纸合作,这座城市里的报纸每周都会登载我们医院的广告,报纸发行量大,效果好。你们这些小公司,靠诈骗过日子,我们是不考虑的。”
阿香可怜巴巴地说:“没有诈骗啊,我们收了钱,就会让你们公司的名字出现在电视上,我们是正规电视台的。”
女子很不屑地用鼻子哼了一声,她丝毫也没有考虑到我们的感受,她直截了当地说:“什么电视台?你们不就是收了人家的钱,送给电视台,让在电视上露个面吗?这点伎俩还能瞒过我?”
阿香小声说说:“我们不是电视台的,我们是电话直销公司,但是只要交了钱,就能让你的名字出现在电视……”
阿香还没有说完,女子又用鼻子哼了一声,她斜睨着我们说:“也只有低智商的人才干这个,你们这些伎俩也只能骗骗傻子和白痴。”
她自己好像很伟大,她自己好像从事的是阳光职业。
女人的神情像一块铁石一样冰冷。她至始至终都没有正眼看我们一眼。
我当时有一种受辱的感觉,这个神情倨傲的女人,让我实在无法忍受,我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我想跳起来,把这个女人的衣服剥光,然后喊所有人进来,让大家看看这个女人裙子下包裹的利器,而她正是依靠这个利器才坐在了这间办公室的这张椅子上的。她的利器一定很独特,法力无边。
这笔生意没有谈成。
走在回去的路上,阿香说,她也是经过黑中介介绍来到这里的,现在她来到这里已经一个月了,还没有谈成一笔生意,没有一分钱进账,这个月她每天上班,却都是劳而无功。这个公司没有底薪。
阿香神情很沮丧,她说她和老公离婚了,自己独自带着孩子,孩子在上高中,母女俩没有任何存款,她说,明天她就离开这里,去大街上捡拾矿泉水瓶子。
我问:“你当初给职介所交了多少钱?”阿香说:“500元……火车站旁边的中介所都是黑心中介。”阿香说完后,眼泪就流了下来。
我不忍心看她红红的眼睛,我担心自己的眼泪会掉下来。
其实,这家电话直销公司的很多人都和阿香一样,每天忙忙碌碌,却一无所获。他们不停地打电话,可怜巴巴,低声下气;不停地在外面跑,顶着烈日,冒着严寒,却没有一分钱进账。公司是没有底薪的。
几十号人,一个月下来,只谈成了三笔生意,这是我在墙上的黑板上看到的。谈成这三笔生意的,只是一个人,一个高大丰满的漂亮女孩子;而所谈成的这三家单位,两家是村办工厂,一家是村委会。阿香偷偷告诉我说,这个女孩子出卖色相,又许对方以巨额回扣,才谈成功的。而只要谈成一笔生意,就能维持公司的正常运转。
公司每天都弥漫着失望和失败的情绪,每个人都垂头丧气,每天有人进,每天又有人出,每天都能见到新面孔。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会争着抢着往这个袋子里钻?难道就因为这是电话直销——是一种外面宣传的新兴产业吗?
这么多人没有收入,他们如何生活?公司为什么不给底薪?
我决定找老板谈谈。
老板单独有一间办公室。他坐在一张并不宽敞的办公桌后,桌子上摆放着好几本武侠小说。上班时间沉浸在刀光剑影中,这就是他所有的工作。
老板20多岁,肥头大耳,体态臃肿,一副养尊处优的模样。他有严重的口吃,一说话后面就是一连串省略号。一说话他就神情激动,面红耳赤。
我走进他的办公室,他将双脚从办公桌上取下来,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放下正读得津津有味的武侠小说,恢复了一副老板的模样,他故作威严冷峻地问我:“你……你……”
我说:“我有事。”
他马上站起来迫不及待地问:“什么哦……哦……”
我替他说:“你是想问什么事?”
他马上长出了一口气,如释重负地坐回了沙发。
我说:“大家这么辛苦,你应该发点底薪。”
他马上又激动地站起来:“不……不……”
我又替他回答说:“是不是不可能?”
他轻松地坐了回去:“是……是……”他就是说不出那个“的”字。
他“是”了半天,憋得脸红脖子粗,既然不愿意给大家发底薪,既然这么贪婪,我才不会再管他了。我转身走出去,让他一个人在房间里一路磕磕绊绊地“是”下去。
回到卧室后,看到一张张垂头丧气的脸,我说:“你们为什么要来这里?什么工作不能干?我们有双手,难道还怕饿死了?你们在这里呆了一天又一天,能有什么结果?电话直销,说白了,就是骗人的,骗那些老板的。你们想想,能够做老板的人,都是人精,谁会那么好骗?”一个又瘦又高的男子说:“我早就想走了,可是出去后还是找不到工作。”
我说:“你整天呆在这里不去找,工作就会来找你?”
另一名男子不服气地说:“可是,我们这里就有人拉到业务了。”
我看着他那张长满粉刺的脸问道:“你是女人吗?你有……”后面的话我觉得不合适,就再也没有说。
老板大概听到了我的说话声,他左摇右摆地艰苦卓绝地走出来,指着我说:“你……”
我说:“我怎么了?”
他从口袋里摸出电话,拨打了一串号码,然后说:“这……这……”
我估计他是找人打我,凭他一个人,我一拳就能打他一个跟头,让他骨碌碌滚到门外,可是他要找人,我就害怕了。
我一步跨到了门外,他缓慢地转过身,晃晃悠悠地伸直手臂,想拦住我,没有拦住。他继续对着电话说:“这……这……”
我沿着楼梯跑下去,等到他“这”出来的时候,我已经跑到了一楼大堂。
我没有再去那家尖尖鼻子工作的职介所,我担心尖尖鼻子会给我冷脸色,她那张漫长的脸让我恐惧。
我游荡在火车站前的一条大街上,这条大街上的店铺除了色情发廊就是职介所。白天,职介所的门口人头攒动;夜晚,发廊的门口鬼鬼祟祟,所以这条大街上一天到晚都是人群,都是怀揣着不同目的和动机的人群。
这里充斥着小偷、妓女、骗子、逃犯、乞丐,还有地痞流氓,这里危机四伏,所以我特别小心。
有一天,我在一家职介所里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她正在看着悬挂在墙上的招聘职位,她还是穿着那条蓝色的裤子,那件粉红色的上衣,头发略显杂乱地披在脑后。她是阿香。
阿香看到了我,也感到很意外,她问:“你也在找工作?”
我含煳地回答了她,然后说:“我们一起出去吃饭吧。”
那时候已经快到黄昏了,也是火车站和周边地区人流最多的时候。阿香紧紧地跟在我的身后,过马路的时候就小心地拉着我的衣袖。我感觉她就像个孩子一样。
我们一路走着,远离了火车站,来到了一个广场边。此刻,华灯初上,广场里是悠闲散步的老人,排队轮滑的孩子,呢喃私语的恋人,广场边的马路上,是一辆辆疾驶而过的轿车,轿车里坐着衣着整洁的人们。高空中的楼房里,一家家窗户次第亮起。楼下的店铺里,一家家酒吧的彩灯闪闪烁烁……然而,这些和我们都没有关系,这是城市里的生活场景,而我们现在饥肠辘辘,我们是来到这座城市讨生活的乡下人。
我们找到一家卖云南米线的地方,这是这条大街上最便宜的一种饮食。阿香看着那些颜色古朴的桌椅,看着装饰豪华的屋顶和墙上张贴的大幅米线宣传画,犹豫了一会,才跟着我走了进来。
坐在桌子边,她显得很胆怯。可能她平时只是在街边小店吃饭,从来没有进来过这样的饭店,从来没有在饭店里坐着高桌子低板凳吃饭。
米线要先付款后吃饭,阿香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粗糙的钱包,这种钱包一看就是夜晚街边五元一个的地摊货。她要抢着和我付钱。她说她年龄比我大,应该由她来付钱。服务员掩着嘴巴笑了。我偷偷说:“别抢了,人家会笑话的。”她才犹犹豫豫地把钱包塞进口袋里。
米线端上来的时候,我随口问道:“你有多大?”
她说:“33岁。”
我大吃一惊,她皮肤粗糙,额头皱纹密布,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大10岁啊。
吃完了米线,我们来到了广场上。我们坐在花丛边的连椅上,任夜晚习习的凉风吹着额头沁出的汗珠。
阿香说我从那家电话直销公司走后,她也离开了。和她一同离开的还有好几个人。大家在这里上班,没有拉到一件业务,走的时候也不用办理任何手续。
阿香的家乡在东北,她以前在一家国营工厂上班。她独自来到南方已经6年了,6年来,她还没有回过一次家。
阿香向我说着她的过去,身边走过了一个少妇,少妇手中牵着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风吹着少妇的连衣裙和又黑又直的披肩长发,显得风情万种。少妇脸上带着满足的笑容,看起来她的生活很优裕。
我看到阿香望着少妇的眼神很凄凉。
10年前,阿香在那家国营工厂的宣传科工作,她每周的工作就是编写一期不到一千字的新闻简报,登载一些“形势一片大好,工人干劲冲天,车间生龙活虎”之类的废话。
阿香是一名中专毕业生,那时候的中专学生也被认为是天之骄子,那时候的中专学生还分配工作。阿香从这座工厂的子弟学校走出去,又回来在工厂上班。
业余时间里,阿香喜欢写诗歌,她的诗歌曾经登载在那时候很有影响的一本叫做《星星诗刊》的刊物上,也是因为这首十几行的诗歌,阿香被分配在工厂宣传科。
那个年代的文学还很神圣。那时候,因为发表了一篇小说,就能找到一个好媳妇;因为发表了一篇小说,就能调到好工作。那时候的文学青年是万人瞩目的对象,是人们崇拜的偶像,不像现在,文学青年成了迂腐与顽固的代名词。
10年前的阿香应该很漂亮,她说那时候她每天早晨打开办公室的房门,就能看到从门缝塞进来的情书。那时候的情书也都会折叠成鸽子的形状,暗指“鸿雁往来”,而情书的内容也写得如泣如诉,如怨如慕。而现在,情书也已经绝迹了。干瘪无味的手机短信代替了那些诗歌一样的语言。
10年前的阿香有很多梦想,她说她几乎每天下午下班后,都会独自来到工厂后边的草地上,在那里静静地坐着,望着夕阳西下,望着天边的火烧云,还有远处起伏而飘渺的山峦。她在想:山那边的世界是什么样子?有时候,飞机从头上上的云层间穿过,阿香痴痴地望着,看着飞机消失在遥远的天边,阿香总会想:我什么时候才能坐上飞机?
10年过去了,阿香还在做着坐飞机的梦想。
我说,我小时候和她一样,不过我们那里是山区,我也经常站在村口的崖畔上,望着层层叠叠的山峰,想着山那边的世界。我们那里很少有飞机从空中飞过。每次有飞机出现,大人小孩都会追着飞机跑出很远。
那天晚上我们谈了很多,我觉得我很长时间再也没有说过那么多的话,可能由于共同来自外地,共同在这座城市漂泊,一下子让我们之间没有了隔膜,一下子拉近了我们的距离。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外乡人”;我们又有两个相似的名字,一个叫“打工仔”,一个叫“打工妹”。
我们还说起了小时候的生活。那时候我们那里很穷很穷,我小时候好像很少吃饱过,那正是阶级斗争如火如荼的七十年代,孩子们的主食就是红薯和玉米面。上初中的时候,我是住校生,每周只能回家一次,背着一布袋的红薯和玉米面馒头。冬天的时候,玉米面馒头又干又硬,结着一层冰渣,都能把狗砸死,而我们那时候正是长身体的年龄,却连这样恶劣的饭食也吃不饱。后来,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能吃饱饭了,我们也能吃上了麦面馒头,我那一年的夏天个头一下子窜高了十几厘米。那年秋天去外公家的时候,外公抱着我又悲又喜:“我娃以前恓惶的吃不饱,现在吃饱了,个头长这么高了。”
那时候的我是农村户口,阿香是城市户口,那时候的工厂比农村要好很多倍,阿香说那时候她从来没有过挨饿的感觉,她是穿着天蓝色的裙子和白色衬衫,唱着《让我们荡起双桨》的歌声读完小学和中学的。
那时候我们的信仰是 “共产主义社会”。而共产主义社会就是最终消灭“三大差别”,即消灭“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体力与脑力劳动差别”。
上初中的时候,学校里有几个来自几百里外的煤矿上的孩子,他们都穿着料子衣服,吃着白面馒头,说着我们羡慕的普通话。他们几个人是一个小圈子,他们从来不和我们农村孩子在一起,甚至连我们正眼也不多看。他们有着一种强烈的优越感。他们的父母是煤矿工人,我们的父母是农民;他们的家乡在城镇,我们的家乡在农村。巨大的差别让坐在同一间教室里的人,却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
后来,我看了这几年一些优秀的电影:《站台》、《阳光灿烂的日子》、《孔雀》、《青红》……这些电影都在反映那个特殊年代里的城镇年轻人的生活,他们的迷惘,他们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