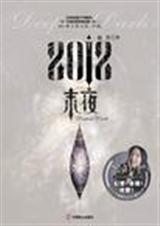暗访十年2-第1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继续歪斜着嘴巴,侧着身子走到了车门口,身后不知道谁踢了一脚,我顺势就跳到了车下。我慢慢地走向小巷,偷眼看到身后跟着地老鼠和那个同样矮小的青年。
我装着没有看到他们,继续慢腾腾走上前去。他们要么是查看我的行踪,要么就是准备在没人的地方打我。我走到了小巷尽头,看到一户人家的门口放着一条矮矮的长凳,可能那家主人下午在门口聊天,现在还没有端回去。我跑前两步,一把操起长凳,抡圆了砸向跟在身后的地老鼠。地老鼠大惊失色,叫声哎呀,扭身就跑。另一个青年也急忙逃遁。小巷黯淡的灯光照着他们四条短腿,四条短腿争先恐后地移动着。我故意大声喊着:“老子今天砸死你们。”他们惊惶万状,呀呀叫着,像两只躲避劁刀的猪崽。那天晚上,我离开了假烟窝点,此后,我再也没有走进过那家位于居民楼五层的假烟窝点。
我知道我的行踪已经暴露,这座城中村的假烟商人都来自闽南同一个村庄,地老鼠会将我的一切告诉他们,他们会防范我,我的安全已经受到了威胁。
我回到出租屋里,我找到了思想家,告诉了他这些天我的暗访经历,我相信思想家会对我的秘密守口如瓶。思想家说,赶快去报案。
第二天,我找到了区烟草公司,他们说,他们已经知道了这座城中村里有着很多假烟窝点,他们很快就会行动,此前,他们已经在城中村里“放蛇”,摸排了好几个假烟窝点。
然而,城中村里棋盘般的道路四通八达,鸽笼般的住房密密麻麻,他们又怎么才能找到假烟窝点,而又能不被眼线发觉?
几天后,我接到了一个传唿,是区政府办公室的,他们让我当天下午去区政府开会。
那几天,我很少出去,一直躲在出租屋里,早晨送完报纸后,我就回到出租屋,下午和夜晚不会迈出出租屋一步,我相信地老鼠和那些打手们一定就在城中村寻找我。
然而,今天又不能不去。
我戴上一顶帽子,帽檐压得很低,袖着双手,佝偻着腰身,冒充成一个病人,我的腰间藏着一截短棍,顺着街角一步步走向村口。我的眼睛警觉地向四周观望,耳朵竖起很高,捕捉着周围的任何一丝声响。我想着,如果见到地老鼠,就先下手为强,抽出短棍砸在他的头上,让他没有出手的机会。
还好,我一路没有见到地老鼠,我顺利地来到了公交车站。
会议是在区政府的会议室举行的,椭圆形的会议桌边,坐满了一个个中年男人,他们有的抽着香烟,有的翻看资料,每个人都显得很安静从容,又成竹在胸。这种场景我非常熟悉,以前在政府上班的时候,经常参加各种会议,在这种场合,大家都不会多说话,免得言多有失。久历官场的人都城府很深,老而弥坚,他们的心思别人是不能猜透的。这种场合的座位排列也是很有学问的,椭圆形面朝门口的那个弧形旁,坐的是官职最大的人,这个座位便于看到有谁走进走出,便于对所有人发号司令。而从这个弧形到另一个弧形的座位,则表示着官职的从大到小。
我知趣地坐在了另一个弧形的位置,这里背对门口,表示这是最末等的位置。
蓦然来到这间会议室,我仿佛又回到了那些年在政府工作的日子,在漫长的难挨的会议中,我总是边听着枯燥乏味的讲话,边想着自己的心思。我手捧着资料,脸上是一副认真听讲的神情,而却早已心猿意马。那时候我非常讨厌开会,那些漫长的味同嚼蜡的会议。我还非常讨厌那种生活,戴着假面具迎来送往委曲求全的虚假生活。然而,经过了这两年曲折艰苦的流浪生活后,我才觉得公务员生活实在太幸福了,没有生活压力,没有工作竞争,却有稳定的薪水,而且旱涝保收。
我想着,如果我当初没有选择离开,现在我也会坐在这张椭圆形桌子的另一边,穿着干干净净的品牌衣服,抽着不用花钱购买的高档香烟,做出一副高深莫测优裕自如的神情,脸庞保养很好,头发一丝不苟,皮鞋一尘不染,走路挺胸凸肚……如果运气好,以后可以科级、处级、厅级……一级一级地升上去。然而,我放弃了这一切,我选择了一条最艰难的路,一条荆棘密布的路,独自前行。现在,我遍体鳞伤,血流如注,可我还在大唿酣斗,至死不退,我一次次跌倒,又一次次爬起。我不能倒下,我倒下就是死亡。
那次会议有区政府的多个部门参加,烟草局、打假办、交通局、公安局、交警大队、城管局、街道办等等,还有这座城市几家报社的记者。这些记者就是我以前写到过的时政记者,他们在前一天的夜晚,就会接到部门的会议通知,第二天和部门一起参加行动。行动结束后,他们一手拿着红包,一手拿着通稿,回到报社,把通稿捏巴捏巴,就变成了一篇新闻稿件。
这就是所谓的跑线记者。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成为像他们一样的记者,我对他们充满了羡慕。那时候我觉得他们能够在这些全国知名的报社做记者,一定水平很高。后来我才知道,他们中的很多人文笔远远不如我,经历也远远不如我,只是他们的运气很好,他们大学一毕业就能进入知名报社,而我年近而立还是报社的发行员。
在这座陌生的城市里,我一切只能靠自己。
那时候我就发誓,一定要做一名记者,一名出色的记者。我要让他们知道,这个坐在最末等座位上的人,他不仅仅是一名发行员,他的能力超过了他们所有人,他还会做一名最好的记者。
而这家清剿假烟窝点的活动,这几家报社的稿件都千篇一律,正是因为他们的懒惰和加工通稿的写作方式,让我有了发挥的空间。他们衣冠楚楚斯斯文文地研究着拳术招式,每一招每一式都引经据典,而我是从山野阡陌间走出的粗莽大汉,胡乱打出的一拳,却能致对方于死地。
在那次会议上,我报告了自己这些天暗访的情况,并告诉了那家假烟窝点的准确地点。我看到那些记者抽着免费提供的香烟,散漫的眼神望着我,他们可能关心的只是这次红包给多少,并不关心我这些用辛苦和鲜血换来的新闻素材。
坐在椭圆形桌面弧形位置上,与我相对的是一个胖胖的中年男子,他宣布当晚就开始清剿假烟窝点。后来我才知道他是这个区的副区长。
那天晚上,数百个来自不同单位的人在城中村附近的一座小学里集合,十多辆中巴车停靠在道路两旁。学校门口围着很多中老年妇女,她们用警惕地眼神望着这些穿着不同颜色不同式样制服的人,然后低下头去窃窃私语。我走到校门口,这些被挡在校门口铁栅栏门外的妇女们用闽南腔的普通话问我:“今晚这么多人干什么?”我笑着说:“今晚去扫黄啊,卖淫的全部抓。”副区长那天晚上是打击假烟窝点行动的总指挥,他手持对讲机,遥控联系三路打假人马,砖头一样功率强大的对讲机握在他熊掌一样厚重的手中,显得举重若轻。他身躯伟岸,中部隆起,脑门光秃,油光可鉴,每跨出一步都力量感十足,很像战场上指挥千军万马的大将军。
然而,我在对讲机中听到了另外两路人马的抱怨声,他们不知道为了什么问题和副区长争吵起来,副区长的音量增加,他们也声音加大,我感到不明白,在等级森严的官场,这些执法部门的下级怎么敢于向副区长发难。
后来,副区长在电话中声色俱厉:“跑了人,我撤你们的职。”对方说了一句什么,副区长说:“告诉你,明天我们在区长办公室见。”副区长从耳朵边放下对讲机后恶狠狠得自言自语:“街道办都是狗娘养的。”
街道办是区政府的直属下级,为什么对副区长如此不敬,我想不明白。
那天晚上,我是以“神秘嘉宾”的身份参加那场清剿假烟行动的。我在把副区长带到了指定地点后,就趁着夜色偷偷溜走了。我离开了那支行动的队伍,我跟在队伍的后面,混迹在一大群围观的人群中,这里的每个人都怀着不同的心思观察着行动的每一个细节,有人惴惴不安,有人心怀侥幸,有人期盼惊喜,有人忧心忡忡,没有人会察觉到他们身边这个戴着口罩冒充病人的男子,是行动小组的眼线。
那路行动小组来到了一幢楼房门前,这幢楼房的五层就是我卧底打工的假烟窝点。然而,此刻整幢大楼一片黑暗,铁栅栏门上悬挂着一把巨大的铁锁。楼门边的店铺也关门了,那个功夫茶的鉴定专家,我的老板,此刻不知道藏在了哪里。我无法断定这幢楼房里是否有人,整幢楼房一片静寂,一片黑暗,像一个巨大的坟墓。远处的路灯光透过树丛照射过来,让楼门前显得鬼影重重,阴森恐怖。
突然,远处响起了一声尖利的唿哨,城中村的灯光突然全部熄灭了,四周一片黑暗,伸手不见五指。行动小组事先已经考虑到了这个突变,他们一起摁亮了手电筒,突然,黑暗中口哨声大作,无数的砖块和石子从四面八方砸向手电亮光,有人呻吟着倒下了,有人大声疾唿,接着,手电光线一致对外,照见很多男人仓皇逃窜的矮小背影。
我听见副区长在黑暗中大声吆喝:“公安的,枪上膛,谁敢扔砖头就鸣枪。”行动小组迅速摆出了阵型,最外面的是手持盾牌的城管,接着是公安,最里面的是烟草和工商、交通等部门。
砖头没有了,可是却有石子,有人躲在黑暗中,可能是树后,可能是对面的楼层里,可能是草丛中,偷偷地用弹弓发射石子,石子打在城管的有机玻璃盾牌上,当当作响,声势惊人。不断有人中弹,不断有人发出呻吟声,有警察对空放了两枪,石子终于吓跑了。
铁栅栏门终于被启开了,行动小组立即登上五楼,又有十几个城管和警察站在门口,防止有人暗中混上楼去。我在楼下看到五楼的的窗口有手电光在晃动,接着,有人扛着假烟下楼来,我数了数,一共有20箱。
我长出了一口气。
后来听说,那天晚上的三路行动小组一共清剿了上百箱假烟。其中有一路查缴了几十箱假烟后,在小巷遇到假烟贩子的疯狂抢夺,双方激战片刻,公安赶到,假烟商贩们才丢下假烟落荒而逃。“这算一场不小的胜利。”事后,区烟草局的负责人说。
也是在后来,我才听说,负责当晚行动的副区长,其实不是副区长,他的行政级别尽管和副区长同级,但职务只是一名副处级调研员。怪不得当晚街道办把他的话不当一回事,在官场,一个副处级调研员的讲话力度,常常不如一名正科级,甚至不如一名手握实权的副科级。官场似海,深不可测。
那天晚上没有在现场抓住一个假烟商人,我怀疑是街道办的人通风报信了,或者是城中村的保安事先知道了消息,让假烟商人藏匿起来。那天晚上停驶在城中村的车辆也很少,在有限的车辆里也没有检查到一箱假烟,这很不正常。
第二天,全城的报纸都报道了前一天晚上的假烟清剿活动,但所有的稿件都只有四五百字,都内容相同,都来自于烟草系统的通稿。多少个部门多少人联合行动,查获了多少件假烟,对假烟商贩起到了怎样震慑的效果,人民群众又怎么拍手称快。这是一篇干巴巴的毫无生气的新闻稿件。一个小学二年级的,能识字上前的学生都能写出这样干瘪的稿件。
假烟是怎么制造的?制造假烟的都是些什么人?假烟的利润空间有多大?假烟销往哪里?假烟对人体有什么危害?这些才是读者最为关心的,然而这些稿件只字未提。这些拿着红包的部门“御用记者”压根就不想深究下去。
他们的懒惰和失职给我提供了可乘之机。
我觉得我比他们的水平要高好几个档次,只是命运让他们坐在写字楼里做了记者,让我骑着自行车奔走在太阳下做了发行员。我觉得我应该主动出击,世间有很多千里马,却只有一个伯乐,当伯乐没有看到千里马的时候,千里马应该叫几声引起伯乐的注意。多年以后,当我有机会和这家报业集团的总编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的时候,他总会说起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情景,他戏谑地说那时候的我是一个愣头青,身上透着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
那时候的我身无分文,胸怀坦荡,心中燃烧着强烈的渴望,所以无所畏惧。
这些年我一直会想起那天见到总编的情景。总编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也许正因为他有这样的人格魅力,才让全国各地的一流人才聚集在了他的麾下。
在见到总编前的一个晚上,我趴在出租屋的床上,用钢笔字书写了一份简历。和刚出道时不一样,这个时候的我已经知道了一份简历对一个人的求职成功会有多重要。我在简历中书写了自己这两年的暗访经历,并在简历的最后很煽情地引用了阿基米德的一句话:“如果给我一根杠杆,我就能撬动地球。”现在想起来,我那时候真是穷酸迂腐得让人牙疼。
然后,我在城中村外的一家打字复印店把这份简历变成了一份铅字。打字店老板收了我五元钱,让我一直心疼到半夜。
第二天天刚亮,我就起身了,穿着自己仅有的一套像样的衣服,对着钉在墙上的镜片把衣领捏了又捏,让破旧的衣领出现原来的棱角来,然后又蘸着水把头发梳成一个三七分的发型,骑着自行车出门了。
那天阳光灿烂,和风宜人,我骑着自行车,腰身挺得笔直,目视前方,我的心中充满了必胜的信念,我一定要做这家报社的记者,我一定能够成为这家报社的记者。我像一个信心爆棚的拳击手一样,提着双拳走上拳台,像提着两把亮光闪闪的大刀,一出手就会将对方斩落马下。
我对自己说:如果这家报社不要我做记者,那就是他们的损失。想起来那时候的我真是狂妄到了极点,不知道天高地厚。也正是因为拥有这种狂妄,我才有胆量见到报业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