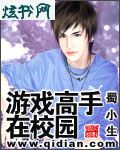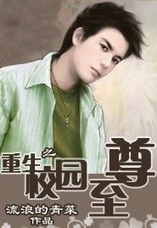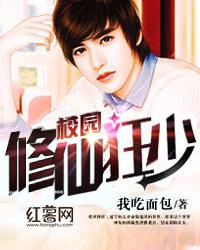春草园-第7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是从左青石回来,我家的祖坟在那里——去年,伯父领我去过,他说今年再来,”华玉忍不住哭了,“我一大早便来那里等着,可伯父没来...他不会来了。”
“他已经走远了!”彭石贤的心情同样沉重,“别老呆在这儿,让我们一块回家好么?”
两人一前一后,一声未吭,向小镇走去,石贤还随华玉一块进了张家,但没落座,因为张炳卿不在,跟华玉也不知该说什么好。
回到自己家里,母亲以为儿子跟公家人去给军属拜年了,问过几句便让他歇着。彭石贤爬上顶楼,躺到床上,拿出主任给他写通讯报道的材料来翻着,他看了主任写的那个开头便丢了开去,禁不住嚷出了声:“热火朝天。。。 简直昧了良心!”
“骂谁呀,石贤?”张炳卿爬上楼来。
彭石贤坐了起来,拧着眉头。
“别老不高兴的,你怎么没有给军属去拜年?”张炳卿了解到彭石贤去了学慈的坟地,“有些事不要老是去想,想结了,想成了团反而不好。”
彭石贤显然不接受这说法,瞪了张炳卿一眼:“华玉去找她伯,恐怕永远找不回来了——这些你也能够不想!”
张炳卿哑口了。伯父的失踪使他悲痛,可又无可奈何,实在说,他内心深处的隐痛绝对不会比别人来得轻:
“大跃进”越来越离谱,弄得*人怨,简直是疯劲发作。张仁茂与偶尔回家的干部侄儿谈起,更是揪心。以前,两人对农村政策与农民疾苦有过讨论,有过争执,还发生过冲突。后来,伯侄俩显得心气平和了些。张仁茂体谅到侄儿办事的难处,说话时只是叹息身边一些人的生活景况,少有评判,侄儿不问,他便不答;张炳卿则少了许多“干部腔”,实际上,他对上头的某些政策也产生了怀疑,对伯父多取劝解态度,有时还表示一定程度的认可。但前一次,张炳卿随检查组回到小镇,晚上回家,却特意找伯父谈了一次话,看那样子还很认真:“伯,你往后说话得小心呢!这形势你一点也见不到么?”张仁茂睁大眼睛:“我见不到,你是见到了死鬼吃活人,还是活人吃死鬼?”接着,张炳卿说出了事情的由来。白天,听过龚淑瑶关于“深耕密植”的工作汇报,散会出门,姜信和招呼张炳卿走到一块,说:仁茂伯拿自己当你部长的老太爷,把什么人都不放在眼里,还常讲怪话,咒骂大跃进,我们听着没事,不计较,可别把影响弄大了,一旦惹上麻烦,到时,就怕我们还难以向你部长作个交代呢!
张仁茂低头听着,待吸完了几袋旱烟,他用烟斗重重地敲了几下木板壁,说:“姜信和是替龚淑瑶传话,那婆娘太鬼怪了!”张炳卿见伯父这么说话,也有些生气地说:“您别老怨着人家吧,伯!您就不该为侄儿想想?我这干部快当不下去了呢,让您忍着点,您怎么就偏是不行呀!”
张仁茂望着侄儿,看他那样子,有埋怨,也有困苦,便不吭声,也就没有说出这件事情的原委来。那是几个月前的事。“大跃进”离不开检查评比、现场批斗,各类名目的检查团如车水马龙似地转,迎来送去少不得要扎彩门,这事很快攀比成风,于是,老篾匠张仁茂派上了用场,白天黑夜,风里雨里,他不能不听差遣,但心里不舒坦,也就作不来慢喊急到,有时还不免出现急喊慢到的情形。上回,小镇的彩门数目少,架势小,装饰没气概,在大检查大评比中落了后,于是镇政府决定要在门前扎出个“卫星彩门”来。当时,天正下着瓢泼似的大雨,抽调的几十个人由姜信和指挥着上山砍树、拖竹、折松枝去了,只有张仁茂留在现场开竹剖篾。龚淑瑶很重视这事,也亲临现场督战。她戴着个斗笠站在雨地里,设想着这彩门该如何搭才能出色,见张仁茂坐在廊檐下低头剖篾,便招呼他:“仁茂伯,你过来看看——”张仁茂抬起头来望了一眼,见龚淑瑶正掉头与一个过路的干部说起了彩门的事,便没去答理她,又低头忙手上的活计了,那干部一走,龚淑瑶再次朝张仁茂喊:“仁茂伯,我让你来,你就过来看看呀!”张仁茂仍未起身:“你让我看什么?我看这天色早着呢!”一听这话,龚淑瑶感到张仁茂是怪她少了点客气,便带笑走过去:“我说伯呀,搭彩门的事,您是行家,就学个老黄忠吧,大家都跃进了,您能不跃进?”她还让张仁茂负责技术指导,说这是给干部家属带个头,也是为张部长争光。张仁茂见镇长说话的态度热乎了,在推却之间带出句玩笑话:“嗨,什么跃进呢,一只老蛤蟆还能跃到哪儿去?再一跃就会跃进到坟墓里去了!”龚淑瑶听了一顿,但只说:“伯,您说笑得远了,幸亏只让我听到,要不,可麻烦呢!”
张仁茂早没有了按捺不住的豪气。他那话的意思不过是说他自己这“老蛤蟆”快进坟墓了,如果不是有意曲解也扯不上咒骂大跃进,几个月过去,龚淑瑶并没有生出什么事来,前不久,在一次布置迎接检查的干部会上,她却突然放出了这样的话:“谁挡着任务完不成就搬谁的石头,你们下面有人敢不听使唤,就拉出来批斗!有我在,不管是什么人,哪怕是部长省长的祖宗也无例外!”这讲话的腔板腔调是从上面学来的,而特别提到部长的祖宗(省长祖宗作陪)却是龚淑瑶的意思。吴国芬听了,想,真是有谁反映了伯父的什么情况么?伯对许多事不情愿,不积极,可伯怎么也不会拿侄子的头衔去压别人的,龚淑瑶的话哪种说法不行,怎么就非得如此旁敲侧击不可?真说,她也没这个必要呀!
国芬婉转地劝过伯父往后说话得留点意。张仁茂也连连点头:“是,是,伯这嘴该缝合了,可你也别把镇长那话看重了,她只是让我带个头,给我们家里当部长的争点面子,你就让她高兴怎么说就怎么说吧。”可是,这争得来什么面子呢?吴国芬以为是自己转弯抹角没把话说清楚,但既然伯父说了往后会小心在意,她也就没必要把张炳卿最近在县里给插了两次“白旗”,还挨了两场辩论的事告诉伯父。
这一次,张炳卿来小镇检查虽说仍然是部长,但另外安排了领队,这可能是他的接替者,所有这些,侄儿也没有告诉伯父。此时,张仁茂与侄子更为隔膜,与侄子的是非之争倒在其次,他只觉得自己已经是多余的人了,便长叹一声:“唉,伯这脾性改不掉啦,也真是人不死不得安宁,你就放心当你的部长吧,伯不会让你操心了!”张炳卿听着,以为伯父生了气,便不再说什么。第二天,他一早赶回县里去,见伯父睡着未起,也就没去惊扰他,想不到的是,这次谈话竟成了两人的诀别。
张炳卿不能向外人讲这话,敢说是谁逼死了伯父?他也不便跟家里人讲,那只能加重他们心里的悲伤。他把这痛苦与悔恨永远地留在了自己的心底里!
“石贤,哥真有事特意来找你,你可不能与任何人乱讲啊!”张炳卿不打算与彭石贤正面讨论伯父的死,他可真是有件要紧的事,说着,从口袋里取出十几张材料纸来递给了彭石贤。
彭石贤接过那叠材料纸认真地看着。看的时候,好几次抬起头来望了望面前的炳哥,却始终无法开口说话。这是一封越级向上反映情况的信,彭石贤又从头仔细看了一遍。信里面列举了大量事例来说明农村工作中的问题,主要讲了三个方面:一是欺上瞒下,虚报浮夸;二是强迫命令,打人骂人;三是瞎指挥,劳命伤财。所有这些,张炳卿认为主要是农村基层干部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造成的,当然,他也提出了希望上级领导应加强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的请求。张炳卿问彭石贤:“你说这会不会被打成右派?”彭石贤摇头:“我不知道,这怎么说得准?”张炳卿表示,他不是右派,党员应该向组织讲真话,不然,还谈什么为人民服务?他告诉彭石贤,他不怕打成右派,他已经挨过了两次辩论,他这“部长”帽子有可能给摘下来,可那也没办法,他不能对不起老百姓!彭石贤听着,他的眼睛发潮,内心深处被强烈地震撼。那信中提到的也正是他见到的事实,母亲、仁茂伯以及许多的乡亲在背地里就悲叹过,议论过,怨恨过。而反映这些情况,却要冒撤职与打成右派的危险,这是怎么回事呢!他之所以提不出意见来,原因在于他还不止于像张炳卿一样看问题,难道这“大跃进”仅是个主观主义或者再加点别的什么就了得?不,现在是民不聊生!但他感到很难说话,也似乎不宜向炳哥透露,他一时还没有那个胆识呢!
在彭石贤沉思不语的时候,张炳卿一边等待他的意见,一边翻着堆放在书桌上的一些闲书杂纸,一本旧课本的底页上,有一首诗,张炳卿认得出来,那是彭石贤的手笔:
昨夜狂风吹屋去,
今朝暴雨毁园田,
高高在上多为祸,
不会作天枉作天!
诗的旁边还有两个字:“骂天”。这也许就是诗的题目。张炳卿把诗推到彭石贤面前:“你这是什么意思?”
彭石贤只得一笑,随即把诗从旧课本上撕下来:“上次山洪暴发时写的,没什么意思——这不就没事了。”
“你还写下了些什么?可全都得毁了,”张炳卿说得很严肃,“骂天骂地干什么?太不懂事!”
彭石贤点头,表示完全接受,写这些东西确实没用,却有危险,他只不过是忍耐不住情绪的发泄,而张炳卿的信,不管有用无用,虽然也有危险,但总算在为老百姓说话,是一件实在的事。于是,彭石贤再次拿起那封信来,与炳哥商量着如何选择词语,如何修改句式,如何增删事例,尽可能地不去触犯权威,就因这“为民请命”,兄弟俩还真有点诚惶诚恐的 ,上午过了,饭后,张炳卿又与彭石贤讨论了一会才定下稿来。但他们决定向家里人隐瞒这件事,没必要大家都担惊受怕。
正月初二,张炳卿便回县里去了。走前,他又反复向彭石贤强调了不要胡来,特别是乱写不得,并透露说,那个猴头的事远没有结束,县公安局已立案侦查。彭石贤也意识到了这事的严重性。于是,他便用一个上午把以前乱写乱丢的一些诗稿进行了清理,但舍不得销毁,而是抄录在另一个本子上,这些诗是他的血泪凝结,丢了它,似乎有一种背叛的感觉。开始,他用一块旧油布将本子包扎好塞在房檐下的墙洞里,一看,不行,那墙洞太浅,另找了几个地方也都不合适,他便把纸包交给了母亲:“这东西别给任何人见到,真遇着了事,你便给烧了。”母亲很担忧:“是什么东西?你现在便烧了呀!”儿子好一阵不回话,最后还是答应了:“那你就拿它生火吧!”并随手把纸包扔到了堆柴的角落里。
这时,镇上办公室主任在门口叫彭石贤,黄大香邀他进屋,他客气地推却了,只与石贤说了几句话,彭石贤坦率地承认那报道他写不来,主任倒是没有催逼,反倒放宽了期限:“你一定能写好,慢两天交也不要紧,到时再说好了。”
看来,这件事情还推脱不掉,彭石贤只得又爬上阁楼,可翻来覆去,就是下不了笔,头脑里什么话也出不来,思想无法集中,这任务完成不了,他终于决定,得上左青石去。
正月初三,彭石贤一早就收拾了行李,那也简单:被子加箢箕扁担。母亲想留住他:“主任不是给你放假了吗?你就别急着走呀!”石贤告诉母亲:“妈,那材料我实在没法写,你向他说,这几天我头疼得很——不上山烧炭更不好交代呢!”
彭石贤走了。母亲只得由了儿子,可她猜不透这件事。前天,张炳卿找儿子说了那么多话,都说是商量如何写好主任这材料,昨天石贤又在阁楼上呆了大半天,怎么会写不出来?母亲心里忧虑重重,她想到儿子扔在柴堆里的那个纸包,便去找了来,打开一看,是个本子,她不识字,但儿子说不能给人看,那就定会是件麻烦事,可也会是件要紧的东西,说烧了吧,儿子那神情其实并不甘心乐意。母亲呆坐了许久,最后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却把那个纸包塞在了自己的被褥底下。
吃晚饭的时候,国芬端着一小碗腊鱼过香婶家来了:“怎么就吃几片煮萝卜片?是人不舒服么?”黄大香的神情显得萎靡疲惫,面前一碗萝卜汤泡锅巴饭,她振作起精神来:“没事,口味淡了点——你又送什么来呢,该留给孩子们。”正在这时,办公室主任来了:“香婶,吃什么好菜?哟,腊鱼!希罕物,久没入口了——怎么,石贤不在?”这主任混名“流浪狗”,大概是指他平时灵透而又随便,还是个嘻皮笑脸的快活人,吴国芬与他也有说笑:“流浪狗,贪吃便上我家去,别在这里‘打劫’。”这一回主任却顾不得回击吴国芬,只问彭石贤的去向,黄大香告诉他上左青石了,主任着急了:“他怎么乱跑!那,那...我得走了!”他出门时,吴国芬顺势使了个绊脚:“别摔倒了——什么事这么慌神?”主任打了两个趔趄才站住:“没什么事——你家部长刚走两天,便急着拉客了么——我这会没心思斗嘴,你不是骂我是狗?那我还得赶快跑腿去呢...”主任什么事慌忙?吴国芬感到有点奚巧:“你妈是好心好意跟你说话,你可别乱咬人啊!”
主任是找石贤要那材料么,怎么不提这事便走了?黄大香的心里也犯疑惑,可这是没由来的瞎猜,国芬宽慰说:“你吃饭吧,现在屁大的事也弄得鬼鬼怪怪,别放在心上好了。”
吴国芬的话虽这么说,可在心里留着意。回家的时候,她正巧望到两个人进供销旅社饭店去,从侧面看,那身影像是见过,可想不起来,到了晚上,她睡在床上猛然记起,那是县公安局的人,心一下子紧了,张炳卿走的前一天,对她说过“幸亏石贤退了学,不然,麻烦就大了”的话,莫非...
初四这天一早,吴国芬进了彭家,黄大香的神情却显出几分高兴来,她告诉国芬,昨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