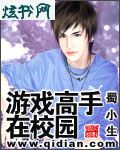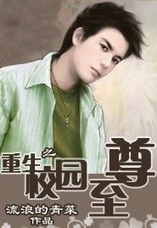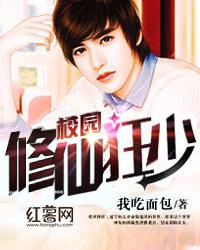春草园-第5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怎么叫偷偷摸摸?”曾明武看了彭石贤一眼,几分认真的,“我见你昨晚没睡好,想让你睡一睡也错了?”
“你帮我干得下脏活重活吗?”猴头插进来说,“昨晚上明武给我家椿糠,今早又赶来出猪栏,叫你来有什么用?”
彭石贤没活说了,出猪栏的粪箕还摆在地坪中间,但这仍不能消除他的猜疑,他们是相互配合着才把话说得这么圆滑的。猴头的哥哥坐在柴角里不说话,脸色蜡黄,全无以前见到时的那种威武气魄,他喝完了粥,把碗搁在灶上,起不来身,是腿给打折了。彭石贤不便询问他什么,怕他感到难堪。
猴头的母亲把最后一碗粥盛给彭石贤,没说话。彭石贤想推辞,猴头说:“吃了吧,待一会好给我家做事。”
彭石贤便接过粥来,粥很涩口,里面掺了好些细糠粉。
开工的时候,彭石贤说:“猴头,我跟你送猪粪下田去。”
猴头不同意:“不行,你在家里给我把猪栏修好吧。”
“留下来给我帮手就行,”曾明武拉过彭石贤,“我来好几天了,也只在家里给他们作些事。”
见彭石贤有些犹疑,猴头的哥哥说,“眼下我们家犯了煞气,别连累你们撞上了才好呢。”
修理猪栏时,彭石贤小声问曾明武:“我参加你们的秘密组织,你说好吗?”
“哪有秘密组织,那是犯死罪的事,你乱嚷些什么!”曾明武极为严肃地说。
“你不是与我说过建立秘密组织的事?”彭石贤十分不满,“我现在明白过来了还不行?什么事让你们不能相信我!”
“你这种动不动就叫喊的脾气实在不好,”曾明武很平静地解释说,“你当时不是没赞成?幸亏没搞!我考虑得太简单了,目前的情形已经十分清楚,你没见抓出许多‘右派’‘反革命’来了?他们还没有搞什么秘密组织呢!”
彭石贤感到失望。曾明武却忙他的活计去了。
彭石贤默默干了一个上午,午饭吃的是红薯杂粮,吃饭时彭石贤闷声不响。猴头哥哥的一句话让他感到有些惊异:“现在有许多事情很难弄明白。有人想出来弄个明白,弄丢了性命的人算是过了,可那些还没弄丢性命的人就惨了,我们泥脚杆是算不上数,可政府与读书人的怨结却是再也无法解开了呢!”
下午,曾明武与彭石贤一块回学校去时说:“你别去跟人说我们来过猴头家,肯定有人操这个心的!”
彭石贤表示他明白其中的利害,但是,在路上他向曾明武谈到申学慈、龙连贵和仇老师的事时,又越说越激动,越说越愤慨,简直如烫如燎,末了,不觉冒出一句:“如果这样搞下去,政府能不民心丧尽么!”
曾明武听着,一直没有表露出附和或反对的情绪来,最后才说:“石贤,有些事说来容易作来难,还是小心──为──好!”
“我不怕死!”彭石贤感到了这种所谓的反右只是一场精神恐怖,一种思想阉割,一次蓄谋诱杀!
曾明武看了彭石贤一眼,只当他说笑:“死得起吗?你与我不一样呢。。。 ”
“什么不一样!难道你比我伟大?”彭石贤不服地说。
“我是两个肩膀一张嘴,无牵无挂,那阵子在朝鲜战场上死了就死了,干净!可你这诗人才子就不同,”曾明武停住脚步,“这话不是说笑,我说你是根独苗,你炳哥就曾经跟我说过,你妈特别地疼着你。。。 ”
是的,如果真遇不测,在感情上,母亲无疑是受伤害最大最重的人了,彭石贤爱他的母亲,也感受到这母爱的深沉,但是,彭石贤有过的见闻,有过的思考以及他性格发展的必然逻辑不会使他临危退缩,他在心里喊出:请原谅你不孝的儿子吧,母亲!请别牵挂责难我吧,所有关心我的亲人!
彭石贤对曾明武狠下心说:“你死得起我也死得起!”可是,当彭石贤晚上躺在床上,又想起这一切时,还是禁不住流下了眼水,他毕竟是个感情深沉的人。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1 6 0
160
───
第二天,同学们陆续来到学校,曾明武是干部,忙着去接待和安定他们,大家见面都说说笑笑的,显得轻松愉快。彭石贤的心情却添了好几分沉重:从教务处的布告栏里看到,接替仇道民担任班主任的是他最不愿见到的郭洪斌。现在,他正拉开公鸡似的嗓门在寝室走廓上与刚到的学生说话,热心透出虚假与得意,当他的脚步响过来时,彭石贤赶忙出门溜走了。
李超兰一直到晚餐过后才到校,彭石贤在校门外的横道上望见了她,其实,他是特意在这里等着的,只是见到校门口有几个女同学迎上了她,她们正在高高兴兴地交淡,便没有走过去。李超兰正好瞥见了彭石贤,她首先招呼:“彭石贤,你什么时候到的?”彭石贤才走了过去:“我给你把行李提到寝室去吧?”
“不用了,你安排自己的事吧,”李超兰背着她的同伴,朝彭石贤一笑,带着歉意,“我姑妈到这会才放我走。”
彭石贤简直是几分忧伤地说:“我们的班主任换了!”
李超兰似乎已经知道,只问:“明天上课吗?”
“不,继续办报到手续,”彭石贤提出,“到时一块去吧。”
李超兰与那几个女同学嘻嘻哈哈地朝女寝室那边走了。彭石贤在想,她姑妈不是成了右派吗?怎么还管着她的事?
当时,李超兰从小镇赶回青姑妈家里时,那情形很有些凄凉,姑父下乡去了,留下的字条告诉她,姑妈成了右派,在外地一个什么工厂劳动。两个表弟妹年龄还小,把家里弄得一塌稀槽,见着李超兰光知道抹眼泪。她这个寄食者一下子变成了主人,添加了好些的责任。后来姑父从乡下回来,但他的工作很忙,他平时本来就不喜欢多说话,现在更显得沉闷,似乎李超兰便是这个家庭依次递补上来的内当家。幸而,青姑妈终于回来了。那天她推门进来,样子十分疲惫,姑父迎着她。这个家里一向最具权威的人物,此时久久地依偎着她的丈夫,像个柔弱不支的小女孩,他们都没什么话好说,李超兰给青姑妈端过茶去,第一次听到她郑重其事地说:“超兰,谢谢你,让你辛苦了!”
李青霞毕竟是个很坚强的人,她说了成为右派的经过,也说了内心的一些感触,在她与丈夫讨论有关的政治观点时,并不像过去一样避开侄女儿,她把李超兰当作大人看待了。
她对丈夫说:“我的部长职务丢了,党员也当不成,这倒不太可惜,反正我从来没有宣传过自己的思想观点,能给我留下个工作,吃饭不成问题就行。中国的事情不好办,看来,这右派帽子在短时间里大概解脱不了,要终其一生也说不定。这无疑会给你,给整个家庭带来麻烦,你如果不肯丢弃我,就得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这是你的命了。”
丈夫对她说:“既然当年在延安整风时的小组记录,后来的宣传部长都没想过要抛弃我这‘托派’,他今天也不会丢开他的右派夫人──你并没有错。”
李青霞苦笑了:“想不到我会重蹈你的覆辙──我以为我们可以不走斯大林的道路──这一次来得太厉害了,而今而后谁还敢言*?”
“不是今后。”丈夫纠正说,“我们走过的路就不曾有过*,斯大林主义是一种历史现象,大概我们这一代人消除不了它,因为还不具备条件,你的价值也许可以留在你的言论里。”
“这是一个教训,”李青霞转过头来对李超兰说,“不仅我们这一代人不会有*,你们也不会有许多,你得记住。”
“谈*成了罪过,这已经是对历史进程的阻碍了。”姑父告诉李超兰,“除了这些,你青姑妈没有作别的事。”
“那还不是刚才这种谈法,如果你把我们刚才说的话传出去就会是十足的反革命了!”李青霞再次警告侄女儿。
李超兰点了点头,她对这种政治险恶很容易领悟。
这一次,李青霞对侄女去小镇的事几乎没有提及,直到来校的前一天,她跟侄女谈话时提了三个要求,才把这个问题概括了进去:“一、你现在人不小了,你得管好自己,遇事多想一想,今后不是我们什么都能照顾你,而可能是你得照顾我们了;二、你今后该读好书,将来选个医生或教师一类的职业就很不错,绝对不要学我,政治不是好玩的事,特别是女孩子;三、你现在不要谈什么恋爱,不管与什么人都不要谈,现在为时尚早,学生时代谈恋爱的多数成不了事。”
李超兰很容易理解和接受李青霞提出的第一、第二点要求,但对不让她谈恋爱,这领悟就不可能深刻,已经萌发生长的青春情愫很难斩断,好在青姑妈并没有像平时一样,硬逼着她表态。
另一方面,彭石贤正为面临的政治疑团在执着地追寻答案,也还抛弃不了对诗歌的爱好,艺术已经成了牵引他步入险境的一种精神力量。实在,他与李超兰这种思想上和心理上已经开始了的变化,很有可能在他们今后的恋爱关系中形成重大的分歧。但有幸的是,这两个人此时都意识不到这一点。
所以,彭石贤与李超兰现在还可以倾心相爱。在学校青草坪的一角,彭石贤讲了李超兰离开小镇之后发生的所有情形。对申学慈与龙连贵的冤屈,李超兰也颇为叹惜:“真可怜!”她见到彭石贤的眼睛红了,还闪着泪光,又说,“这真是个教训呢,幸亏那时候学社没办成,我们也没有鸣放,不然。。。 ”
“可我们并没有错。。。 ”彭石贤就当自己已经加入了一个什么秘密组织,“大不了一死!”
“我最不愿意听你这种傻话,”李超兰对彭石贤说:“像是没事还一定得去找死似的。”
“你不知道我蠢?”彭石贤生气了,“找不找死是我的事!”
“你这又生什么气?”李超兰平心静气地说,“谁不知道你聪明,但倔过了头,说出来的话就和蠢差不多──这没有什么错不错,我青姑妈就鸣放了反对个人崇拜的事,这是党章上提出过的,可人家说她想闹匈牙利事件,你有什么办法?反正搞政治十分危险──这话我以前说过,可我是为你好呀!”
李超兰从来没有这样清楚明白地表达过自己的政治观点。彭石贤本来想从李超兰这里寻求支持,还有可能向她谈及关于秘密组织的事,现在不用提了。在感受到李超兰的关爱之余也感到了失望,而且,还不能说她讲的不对,彭石贤的脚趾头在草地上掘出了一个很深的小土孔,没有回话,李超兰也把她穿着浅红薄纱袜的小脚杆伸过来,轻轻地踏住了彭石贤那用力掘土的脚趾。
“我不是对你生气,我是生自己的气,难道我想成个流芳百世的大人物?便是当个遗臭万年的反革命我也没那本事,”彭石贤抽回自己的脚来,“我们回学校去吧。”
“急什么,我们还是从这侧门出去,绕个圈子再回学校好了。”李超兰很想说说话,“将来,我看还是当个教师或医生好,那样比较安定,你说呢?”
“我真不知道,”彭石贤站起身来说,“你认为仇老师与你墨姑妈很安定吗?你不是说过要当歌唱家么。。。 ”
“我青姑妈说,现在搞艺术与搞政治一样,不可能搞出成绩来。”他们从围墙的侧门出去,来到了以往散步的田间小路上,李超兰说,“我青姑妈认为没有自由,也繁荣不了艺术。”
“你就什么事情都得听你青姑妈的么?”彭石贤说出了一句指代广泛的话。
“你便当我是个没主见的人?”李超兰沉默了片刻,说,“小镇人都说你妈什么都让着你──那好吧,我也支持你当作家、当诗人好了──朝那边走吧,猴头过来了。”
“那里走!”猴头从围墙那边快步过来,“彭石贤,你让我好找──走,跟我游泳去!”
猴头要拉着彭石贤去河沿,李超兰说中午暑气重,下河容易患病,劝他们别去,但她说不过猴头,只得让彭石贤跟着猴头走了,剩下她一个人没趣地回学校去。
猴头找彭石贤游泳是甩开李超兰的一个借口,他们两人泡在水里时,猴头直捷地提出来一个大问题:“彭石贤,你怕不怕坐牢,怕不怕枪毙,如果不怕的话,我们就成立一个地下组织,就看你究竟敢不敢!”
“什么地下组织?”彭石贤虽然也考虑过这问题,但因为猴头的话来得太突然,却使他感到意外了,“这,你想怎么办。。。 ”
“我们的组织叫人民自由党,就是为人民,为自由而战,你现在不用急着说参不参加,待你想好了我们再谈。”猴头又瞪着眼说,“但你不得出卖我们啊!”
“你们有哪些人?曾明武参加了吗?”彭石贤以前听曾明武提及过建立秘密组织的事,可他前些天不是改变了观点吗?于是,彭石贤说,“如果曾明武不参加我也不参加。”
“曾明武干你什么事?难道你的脑袋长在他身上?”猴头带着几分轻蔑的口气,“胆小鬼!”
“那我就不参加好了,”彭石贤很快做出决定,这是因为他不满猴头说话的口气,这中间无疑也有曾明武和李超兰的影响,使他对秘密组织能不能搞出名堂来产生了疑问。
“为什么?”猴头感到意外,“你,你怎么一下子。。。 其实,我只不过是试试你是不是胆小鬼!”
“这有什么好试探的?”彭石贤更不满猴头的话,“你说我胆小——真是好笑!”
“你不胆小?可你怎么要说‘不’!”猴头有些冲动,并警告说,“谁敢把今天这话传出去,就是出卖朋友,就是杀人,当心我就先宰了他!”
“参加不参加能不由我?你不相信我就别跟我说这些,跟我说了,你就不用吓成这猴仔仔样子,”彭石贤也顶着猴头说,“你才是真正的胆小鬼,如果我要干这种事,也不会跟你一块!”
“你是说我胆小。。。 ”猴头又转过话来,“真要干这种事,就得单线联系才是,你没见过书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