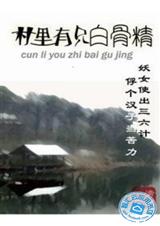村里飘来杏花香-第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第一章
村里飘来杏花香
“新农村三部曲”第一部
第一章
空中雾蒙蒙的,老柳枝佝偻着芽苞,麦苗在苟延残喘,那只以狂叫著称的大黄狗,懒洋洋地摇着长尾巴。“雨水”都过去好些日子了,依然难见雨的影子。该死的鬼天气!该死的县广播站的那个女播音员,四个月前就广播有雨,到现在还是一场空!靠天吃饭的苏行大队的社员们在心里不住地咒骂着。正是拔节的关键时刻啊!但他们束手无策,只得眼睁睁地看着麦苗由青变黄。
苏行大队也叫苏行村,地处江苏省最北部,属淮海市运河县阳山镇管辖。苏行村很小,除了县级地图能找到它,再高一点层次的地图,找起来恐怕就很费劲了。其实,你大可不必花那个时间和精力去找它,一是根本没有必要,第二确实也没有。又不是天下第一村,即使是天下第一村,省级地图和中国地图也没有标注的先例,一旦连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小小村庄也被标注的话,咱泱泱中华,数以百万计的大小村庄,都争着抢着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那还不乱了套。
村子北部二百米处有一口汪塘,占地约一百六十亩,四季常清。汪塘的东半部有一大片芦苇,一百亩左右。夏天,郁郁葱葱,像一个个年轻哨兵辛勤保卫着这块“战略重地”;秋天,起伏跌宕,像无数个年轻舞女舞出一曲曲动人乐章。由于芦苇荡很大很神秘,有人就编造了一段顺口溜,以此吓唬不听话的孩子,半夜三更,孩子们往往被吓得直朝被窝里钻。这段顺口溜是这样的:
红眼绿鼻子
四个猫蹄子
走路啪啪响
爬上咱屋梁
谁要再哭闹
抓到北汪塘
扒掉花衣裳
专吃他心脏
支部书记苏大朝迎来了又一个“春天”。
这一天,苏大朝从公社开会回来时已是傍晚时分。
夕阳的余辉,冷冷地洒在还未成林的杨树行里,几只灰褐色的麻雀,站在光秃秃的枝梢上,挠首弄姿,得意洋洋的样子。一只发情的老麻雀瞅着另一只发情的老麻雀,含情脉脉,别有一番风趣。苏大朝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其余部件皆响的破自行车,发出了“咣当咣当当”的声音,吓得两只老麻雀仰起脖子无助地惊叫起来。少顷,一只老麻雀飞走了,另一只老麻雀也跟着飞走了,只剩下摇摆的干树枝。
路上,他盘算着如何揪出三个“地富反坏右”分子,实施新一轮“思想政治教育攻势”。落实书记指示不走样,贯彻党委精神不过夜,是苏大朝一以贯之的工作作风。
这次,他决心超额完成公社下达的任务指标。
又是一阵“咣当当当咣”的声音,那个堪称大路口上的两三个三四岁的孩童,吓得六神无主,七零八落。苏大朝得意地瞟了他们一眼,迎着不太强烈的西北风,扬长而去。车胎和土路摩擦时的尘土扬了起来,迷住了一个孩子的眼睛。
回到家中,天上的黑影渐渐袭来。
他的一对儿女蹲在门槛上,翘首以盼,他的眼圈红了起来,背过脸去,轻轻地抹了一把,自叹:没有个女人真不行啊!他把盆里泡了不知多久的白菜帮子洗了一遍,切成一个个小条条,炒成了一大盘醋白菜。两个孩子狼吞虎咽起来,没多会,便吃了一个精光。儿子还想吃,可怜巴巴地请求。
“爷,我还饿呢!”
他瞪了儿子一眼,心疼归心疼,严肃劲儿还是丢不得的,这是他一贯的主张。
“吃多了不消化,晚上就少吃点吧。凤儿,赶紧哄你弟弟睡吧。”
他的女儿叫苏凤,儿子叫苏家醒。
几年前,他的媳妇得了重病,县里和市里的几家医院都查不出病因,在家病恹恹地躺了二十几天,看着一双儿女泣不成声。临走的时候,她用瘦得没有一丝肉甚至肉皮的小手指着床前两个孩子,一句话也没说,两眼睁得怒圆。
苏凤和苏家醒上床睡去。
女儿都十三岁了,还和儿子挤在一张小床上,他禁不住抽泣了几声。三十七八岁,正值壮年,他尝尽了没有女人的艰辛。
炒好了一小盘花生米,放在快要翘板的小木桌上,然后从床底下费劲地够出一瓶 “运河香醇”酒,开始喝了起来。借酒浇愁愁更愁,但他基本上没有这样的感觉,他喜欢喝几两,这是有目共睹的,他也不避讳,支部书记怎么了,支部书记也是人,是个男人就有酒瘾。痛快地喝了一口后,他身心深处产生了飘飘然然的感觉,一切的不快,在酒精的化学作用下,仿佛都抛到了九霄云外。二两烧酒下肚,他那方方正正的“大麻子脸”上添了几分生动的色彩,那是一张还算英俊的大脸,如果没有小时候那场几乎要命的“天花”,怎么说,在苏行村也算第一美男子啊!是啊,剔除麻子后,脸膛还是蛮英俊的,他自己这样认为,也有人和他一样的看法。要不是这些麻子,他苏全朝无论如何也不能身居第一位,他有点嫉妒苏全朝,他也恨那些得不偿失的麻子。黄里透红,红中带紫,这时,他塑料盆口大小的脸膛上的那些异物,活像秦始皇陵墓里一个个刚出土的“彩陶”,栩栩如生,活灵活现。
他习惯边喝酒边思考重大问题。
四两老酒下肚,“地富反坏右”几个字眼,在他的脑海里来来回回地乱蹦,发出了“咣咣当当”的声音。究竟谁来担纲“旗手”?这些年来,他十分看重“旗手”的标杆作用,标杆就是榜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确立了榜样,其他的人就好办多了。苏凤朝这个小子不用说了,他是 “地主崽子”,哪次也少不了他,少了他也成不了“大席”,谁叫他是地主成分呢!虽然苏凤朝经历过无数次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洗礼,认识也已经十分接近“贫下中农”的水平,或许比有些“贫下中农”要高得多,但苏大朝没有办法,也别无选择,苏凤朝理所当然要身居“地富反坏右”之首。
其实,对于苏凤朝,苏大朝已经没有往日咬牙切齿般的痛恨,相反,内心深处倒萌生出一些感激之情。自己能够多次荣立战功,受到上级党委的隆重表彰,苏凤朝可是功不可没啊!苏大朝仔细算了一笔账:前前后后,苏凤朝已经被批斗了十七次。但他从来不叫苦叫屈,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你让他低头他就低头,你让他弯腰他就弯腰,你让他检讨他就检讨,甚至,你让他下跪,他也毫不含糊,从来不讨价还价。这么“优秀”的榜样,打着灯笼也难找啊!
苏大朝暗自庆幸。
为确保完成公社下达的光荣任务,这次,也非苏凤朝当先锋打头阵不可。他从来都是主张打有准备的仗,只有把可能发生的一切事情预料到了,准备好了,条件成熟了,他才会重拳出击,而且必须击中要害,让被击者心服口服,无话可说。这是他最大的优点,也是别人望尘莫及的优势。多少年来,谁也不敢怎么他,谁也怎么不了他,原因就是他具备别人所不具备的游刃有余的素质和能力。在苏行村,至今还没有谁敢向他呲牙咧嘴,这一点,他十分自信。
他把一盅小酒慢慢地倒入嘴中,“滋溜”了一声,撇了撇大嘴,然后伸手捏了几粒花生米,贪婪地咀嚼起来。没多会,门“吱嘎”响了一声,闪进来了一个黑影,一屁股坐在他的对面。那个黑影,脸上和身上几乎没有多少肉,一颗呲出来的大黄牙,严格地说,有些发黑,趴在皴裂的下嘴唇上。
那个黑影笑起来不太美观,给人嬉皮笑脸的感觉。
“哥,好久没喝瓶装酒了,多远听到你嘴里‘八嘎八嘎’的,心里怪痒痒的,就进来了。”
“就你这个熊样,还喝瓶装酒!一个小小生产队长,顶多是个大队支委,想跟我平起平坐,什么时候学会做梦了?”
那个黑影叫苏东朝,是他刚当支部书记那会提携起来的支部委员,兼任第一生产队的队长,跟着他“出生入死”,也算是他的“黄埔一期”嫡系。他从身后的抽洞里摸出了一只酒盅,给苏东朝倒了大半盅。苏东朝接过来一饮而尽,嘻嘻哈哈地献起媚来。
“到底是支书的酒好喝!”
“好喝吗?我这还有一瓶,拿去喝吧,看你能喝出什么花样来?难道能跑了我的手心,另立‘中央’不成?”
他瞪了苏东朝一眼,略带轻蔑的口气,让苏东朝不禁打了一个冷颤,精灵灵的小脸上起了好几个小疙瘩,胡乱地排列在他窄小的前额。
“这个肯定不会,想吓死我啊!”
苏东朝又喝掉了一大杯,伸手捏了三、四粒花生米,丢进嘴里一粒,其余迅速地放进了快要掉底的裤兜里。苏东朝揣起那瓶酒,转身想溜。他看不惯苏东朝的作派,有些不耐烦。轻蔑的嘴角蠕动了半天,但又不知从何说起。出门看天,进门看脸,苏东朝耸了耸一高一低的肩膀,只得笑眯眯地重新坐了下来。
“酒瘾过足了,这就要走?那个事情,办得不怎么样,没想到那个娘们还是一个贞洁烈女,什么东西?”
听他旧事重提,苏东朝喷着酒臭的嘴里便不干不净。
“刘成花,不识相的狗东西!都说寡妇门前是非多,你就消消气,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三日内,一定让她服服帖帖,娘个逼。”
他穿过没有关严实的木门,望了望天空,一片浓浓的夜色,三两颗昏暗的星星,不眨眼似的挂在半空。外面没有一点声音,静得让人不寒而栗,一只无人认领的小狗钻了进来,窝住尾巴蹲在门旁,目不转睛地盯着他手里的酒杯。他咋呼了一声,狗日的,又没有肉,把你馋得这样,小狗吓得“汪汪”地挤出门缝跑开了。
“那个娘们,老是在我的脑子里转圈,赶不走,怎么办?不就是年轻嘛,年轻是资本,我也不赖嘛,要不是孩他娘早逝,我操这份闲心干嘛!好了,不说了,什么东西?越说越气,喝酒。”
他一饮而尽,苏东朝也喝个底朝天。不要钱的酒,不喝白不喝,苏东朝捂住嘴,怕酒味跑掉,等了好大一会,才挪开那只仅剩下骨头的手。苏东朝仰着满是沧桑的鬼脸,瞅着那根弯弯的尽是虫眼的老木梁,接连叹了几口气。
“嫂子正值英年啊,日子刚有点起色就撒手而去,侄女和侄子两个孩子还小,一把屎一把尿的,真不容易,你就续一个吧!刘成花,那个娘们,长得水灵灵的,就是带着一个吃奶孩子。”
“别提那个娘们,你想让她给我当小?”
涨得通红的脸上似乎变成了一个小火车站,青筋暴突,好像两根轻轨一般。随着“嗞啦”一声,他便低头不语,盯着撒在地上的花生皮,好大好大一会,两手抱头,蓬乱的头发里冒出几滴稻草沫。看来他好几天没洗头了,痒痒的,不住地挠着。他也仿佛在深思着,弄得苏东朝坐立不安。
他终于抬起头来,刮得光光的嘴唇抽吸了一下,扭头朝窗外望去。一支不算太长的槐树枝,随风摆动着纤细的腰肢,偶尔敲打了几下窗框,但没有多少声响。而他的内心里仿佛进入了冰天雪地,独自一人行走在深山老林,一只老虎拦住了他的去路,反正自己喝了酒,不怕这庞然大物,窜上去学着武松打虎的样子,砰砰砰打了起来。桌上的小盘被震得乱蹦,花生米跑了出来,苏东朝忙着去捡。
他叹了一口长气,端起了酒盅,喝了半小杯,继续望着窗外。两只麻雀扑棱了几声,贴着窗框斜飞了过去,留下了一串“唧唧”声。过了一小会,看都没看苏东朝一眼,从他的牙缝里便挤出了一句话。
“娘的,那双迷人的眼睛,高高的鼻梁,樱桃似的小嘴。还有那对*。好了,不说了,娘的。”
苏东朝最害怕他的深邃,好像一个几千米深的地洞,穿过历史长空,跨越世界隧道,眨眼之间,就会进入一个飘渺而凶狠的世界。葫芦里卖什么药呢?他不敢妄自猜测,想听他直截了当,但左等右等,就是没有明示的意思。看来只有喝酒了,只有在喝酒中,或许才能从中悟出一些什么来。
苏东朝端起酒盅,接连喝了两气。他依旧不说话。苏东朝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苏东朝的头发刚理好,没有什么造型,光秃秃的一小片,这样可以间隔得长久一些,省钱才是最关键的,钱对他来说,只能是一个最高理想,可望不可及,苏东朝没有办法,他也没有办法。能吃上几块烂山芋就不错了,地窖里已经见了底,几块烂得不能再烂的山芋头早被连皮吃掉了,孩子多没办法,苏东朝准备跟邻居借一些。又到了自然灾害时期了吗?不可能吧,但现实就是这样残酷。
“二十四五岁,不正合适吗?洗衣做饭,哪样不行?人又俊俏,夜夜当新郎,打着灯笼也难找!”
“咸吃萝卜淡操心。”
“咱大队不能没有你!她一个女人家,挺不容易的,你也算为人民服务。你的担心是多余的,不会有人说三道四,一个愿娶,一个愿嫁,两厢情愿,天大的好事!”
苏东朝自鸣得意,满以为他能够欢天喜地,没想到他却来了一句。
“她同意,我也不会要她!”
他有些恼火,把酒盅端到了嘴边,但没有立即倒进嘴中,双眼瞅着略有混浊的酒,一声不吭。
莫非他闲刘成花是一个寡妇,怕有损自己的光辉形象?还是害怕她那个克夫命呢?苏东朝想不出个所以然来。苏东朝伸手捏了一粒花生米,拼了老命似的嚼着,嘴里发出了“嘎崩嘎崩”的声音。昔日嚼花生米时多么清脆令人陶醉的响声,此时竟是如此的索然无味。突然,苏东朝的心中豁然开朗起来:难道是当“地下情人”?对,有可能,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地下情人”!
苏东朝随手端起酒盅,喝掉了一大杯,抢到盘子里最后一粒花生米,便咧着大嘴,笑了起来。
“亏你还笑得出来!”
他放下酒杯,点上了一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