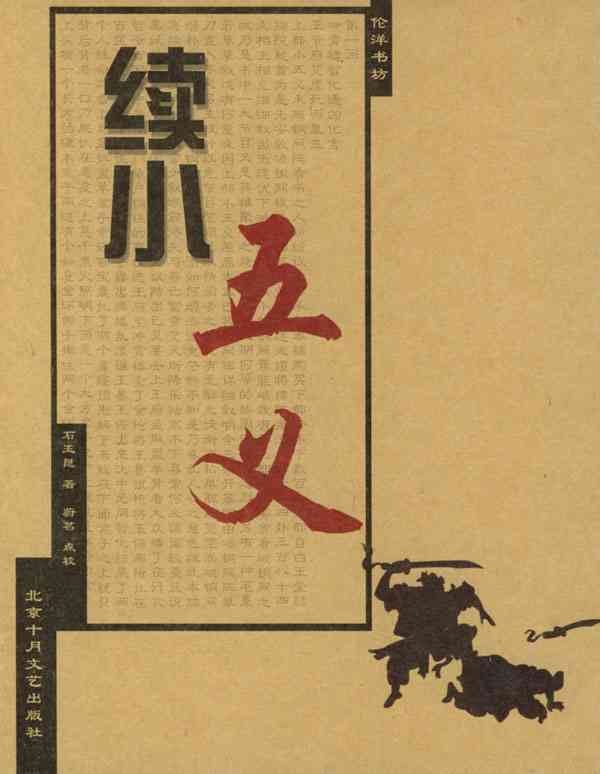秦家小五-第2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仍是王翾最有主见,只探到车外,道,“仔细赶路,莫误了时辰。”
马车动了动,又停了。
“又是怎地了?不过是佳节求签,路也走不得了?”秦雨菱没好气地喊了一句话儿。
“白小姐,可否行个方便,将贵府马车退后些许,不胜感激。”秦玉衍在拱了拱手道,语气十分客气。
过了一会子,白府马夫却道,“我家小姐亦是要走这条道儿。”
如蔓一听,也不禁拧了眉头,秦雨菱正欲发作,却教王翾拦下了,摇头示意她莫要出面儿。
街市除却商铺,路面儿并不宽敞,秦白二府的轩车,皆是十分气派的,断是无法一并通过了。
当下,遂僵持了一会子,终是安子卿打破了僵局,他说,“不如秦兄便让白府先过,想来也不急在这一时三刻的。”
秦玉衍才掉转了马头,硬生生道,“听安兄一言了。”
“凭甚么这样欺负人了?明明是咱们先来的,她反倒有理了!三哥哥何时这样软弱了的。”秦雨菱小手捶了坐毡,啐了一口道。
如蔓拢了拢头,遂挨到她身边儿,道,“就让她先得了这几尺路,也不见得就能占了上风儿去。教人传出去,也会说咱们秦府知那礼数。咱们不争这些,左右不会少块皮肉了,四姐姐莫气了。”
王翾这才附和,掩袖笑道,“五妹妹懂事,却是这个理儿了。”
“怎地不少块皮肉了,你还不是受了伤的?”秦雨菱鼓了鼓腮帮子,又抚了如蔓手臂,也渐渐想通了。
末了,只听沈冰补了一句儿,“想来三哥哥办事,总是妥帖了的。”
“安夫子也是个知礼的,咱们就先等着。”如蔓说起那安子卿,心里头沉甸甸的,很是安稳。
“那便是府上新请来的夫子?倒是一表人才的。”王翾似是想到了甚么,秦雨菱就问,“安家如今没落了,这样的人竟也不得用处了。”
如蔓听她们说起安家的事儿来,心里十分仔细,王翾又道,“并不会这样简单了的,安家祖上世代为官,在京城是很有些根基的,后定居咱们临安城,家业忽而就似败了下来,谁也不知那其中因由了。”
说话间,车子缓缓驶了去,这会子早已将方才那争执抛了开,又对那安子卿的家事来了兴致。
秦雨菱推了推王翾,道,“大嫂子还知道些甚么,快说来听听,那安家到底是怎个回事了?”
沈冰也凑了头倾听,如蔓只得故作镇定地,王翾眉眼一转,就说,“不关咱们的事儿,何必嚼这舌根子了。”
“那安公子是五妹妹的夫子,咱们总该知晓些底细罢?”秦雨菱又拉上如蔓来。
“我亦是道听途说的,并不清楚了。”王翾显然不愿多说,如蔓暗暗生疑。
今儿这样一讲,她隐隐觉得安子卿会在秦府里教书,想来并不是这样简单之事了。
秦老爷到底是看中了他的才华,亦或是看中了那安家的位份?
秦雨菱自然不会想的那样远,毕竟同那安子卿没甚么交情,她就问如蔓,“安公子教的如何?得了空,也好去拜会一番的。”
“夫子学问做得好,书也教得认真。”如蔓说的却是实话儿。
“这样的人,若是只教书,怪可惜的。”沈冰叹了一声儿。
王翾却似有不同见解,遂道,“人各有志,命数天定,日后的事情,谁又做得了主儿?我瞧他在秦府断是权宜之计,自是不能长久了的。”
“听三哥哥说起过,早几年安公子就已过了解试,因着不在京洲,并未通过学馆推荐,如今算作举人了。”秦雨菱好似知了内情,连忙道。
“一年一乡试,三年一省试,明年便要到了的。三弟再过两年,也可参考了。”王翾解释着。
如蔓对着这些个仕途官道儿的,十分生疏了,只知道举人是由乡贡入京的封号,并不知那具体的。
似他这般俊雅之才,可会有那半步青云之日了?念及如此,如蔓情绪不免低落了,不知明年春闱过后,可是就要长别了…
若是进京赶考,归期便遥遥不堪望了。
“行之哥哥可也是举人了?”秦雨菱忽然冒出一句儿来。
王翾皱了皱眉,道,“他哪里是个读书的材料?没落的睁眼瞎罢了,也就算是说生意上有些头脑,断是比不上我那两个哥哥的。”
秦雨菱不服气,只说,“大嫂子严重了,我瞧着行之哥哥仍是…”
“五妹妹,安公子送的药。”秦玉衍掀了帘子,手上拎了药包子。
如蔓腾出手,便说,“并没大碍,替我谢谢夫子。”
秦玉衍点点头,如蔓从缝中瞧去,安子卿上了马,冲她的方向微微颔首,尔后遂掉头奔去。
如蔓暗自有些失落,安夫子似乎刻意同她划清了界限,礼貌得紧,亦疏离得紧。
她回了神,却瞧见面前儿的药铺很是眼熟,仔细一想,原是良婶家的药铺了。
车子朝城外奔去,终是没再起了波折,临走时,如蔓偷偷托付马夫留了几两银子给良婶,算作是尝了她曾经的恩情。
清音观于城郊五里处,一派苍松隐青山,天地广阔,仿佛浓墨染出的画卷一般。
如蔓自是许久不曾出门,禁闭久了,便愈发体会出那自由的好处来。
先由小厮到那观中打点了,待遣散了闲杂人等,清了场面儿,才请出这四位秦府小姐来。
观内檀香袅袅,一如空门,即便不是佛门中人,亦是存了一份敬畏,行事言谈,便也收敛了去。
秦玉衍在正殿外的金鼎前儿站了片刻,端端正正地上了三柱高香。
王翾拦了她们道,“闺阁女眷不可轻易沾了香灰,离得远些。待会只得求上一支签儿,断是不要随意祭拜的。”
秦雨菱和沈冰本欲上前,这会子也不动弹了,只等秦玉衍拜完了,几人才一道儿入了偏殿。
道姑十分面善,素白的僧衣,教人瞧着就很是清静的。
香油钱,自然是十分丰厚的,如秦府这般有头脸的世家,端的是那金镶的皮相,银镶的面儿了。
如蔓不敢随处走动,怕触了甚么忌讳,只抬眼仔细环顾了。
就见高粱上多了几绘素画,摆设布局,皆是同前年的一样了。
“何时能求签儿?”秦雨菱进了殿,收了那大咧的模样,端庄得体。王翾和沈冰一道立着,如蔓也静静凝了那香炉子。
打眼儿一瞧,就知这些女子身边教养不同,端的是好气度了。
道姑福了礼,恭敬道,“诸位女施主这厢请。”
秦玉衍遂在一旁道,“我在偏殿侯了,大嫂子好生招呼着。”
说罢,几人跟在道姑后头,提了裙角,徐徐入了正殿。
小脚跨了一尺高的门槛儿,如蔓抬头,只见巍柱高檐,和着梵音,缭绕似沉沉迷梦。
殿门头上悬了一副阔匾,相传百年前,有位高僧云游至此,遂提了字,是名清音观。进了几步,就见两侧高柱上分别篆刻了字。
富贵五更春梦,功名一片浮云。
鎏金大字映出瑰丽的色泽,徒添了阅尽千帆,沧海桑田之味了。
如蔓细细咀嚼了,亦是满口余香。
王翾先问了,正身跪在蒲团上,捐的是前程签。
待将梵经念完,片刻冥灵之后,抽出来的,是一支中平签儿,解为潜龙在渊。
如蔓见王翾脸色一动,低语了一会儿,遂独自出了殿门,想来不是十分满意了。
而秦雨菱求的是那姻缘签儿,拿来一瞧,竟是上签,解为红娘引线。
沈冰求的亦是那因缘,却只是个中签,解为月老阖眠。
如蔓排在最后头,她娇小的身子跪在蒲团上,将眼闭了,虔诚了默念了几句儿,方才定了决心,仍是求那命数签儿。
“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解签人低吟了一句,便又问她,“小姐年岁轻轻,不求因缘,不问前程,为何独选了这个?”
如蔓坦然而笑,道,“兴趣亦是缘法所至罢。”
“说得很好。”解签人叹了句,不再说话儿。
一柱香的时辰过去,如蔓才从正殿走出,秦玉衍问她求的甚么,她只说分不清楚,只糊涂的求了。
王翾便道,“我瞧着也并不很准,五妹妹不记得也罢。”如蔓并没如实相告,她求来的命数签儿,竟和上次一丝不差的,解为中上签儿。
盛衰福禄定,来去枉自专。
可攀高峰,可坠深渊,因缘际会,天机不可道哉。
几人正说着话儿,就见守门道姑进来通禀,说是有贵客造访,也要清场。
正要走的,却打门外走来一行人。
这一瞧不打紧,断的是十分教人惊讶。
打头走的是位陌生公子,约有二十来岁,锦衣华服,只看料子就知来头不浅。
更奇怪的,竟是他身后跟着的,不是旁人,正是白家大小姐,白瑶。
同白瑶一并进来的,还有两名娇丽少女。
王翾见状,少不得上前寒暄几句儿,白瑶始终盯着如蔓。
而同行二女,亦是赫赫有名的闺秀,薛家二小姐薛紫衣,顾家幺小姐顾眉。
“临安路窄的,到哪里都能瞧见秦府小姐们。”白瑶仍是傲气地模样,说着就朝如蔓走来。
“果然很巧,我们刚求完签儿,便不扰白小姐行事了。”如蔓将绣帕握了,礼貌的回应。
“薛家顾家小姐都在,正应了重阳的好日子了。”王翾又打了一回圆场,就要告辞。
谁知那白瑶忽然叫住如蔓,“秦五小姐,可否将那炉里的高香递与我一柱?”
如蔓没料她有此一问,想到之前王翾嘱咐说女子不可沾香灰,又见秦雨菱摇了头,遂不知如何是好。
秦玉衍便出言道,“不如在下代劳了。”
白瑶微斜了眼角道,“既然五小姐娇躯矜贵,那便作罢,我也不要旁人代替的。”
如蔓心知她有意作难,又见秦玉衍面子上尴尬,当真就亲自端了一柱香,递给那白瑶。
眼见如蔓服了软,白瑶自觉顺了气儿,可并不接手,只道,“我原是忘了的,女子不可沾香灰,五小姐怎地这样不小心了?”
众人皆是望向这二人,却都不知该如何劝解,如蔓静静将头一歪,道,“既进了这道观子,香灰随风儿,虽是手上不沾,却仍是闻了去,如此一想,沾与不沾,到底是一样了的,我仔细将手洗了便是。”
白瑶终是重重拿过高香,不屑道,“不愧是安公子教出来的学生。”
尔后携了薛紫衣和顾眉,一并进去,不再理会她们了。
那陌生公子回头瞧了一眼,带了几许探究,便大步入了偏殿。
☆、30 海花楼,乔装扮
“秦家五小姐请留步。”秦玉衍一行人方出了道观,就被人唤住。
如蔓一听指名道姓儿地叫自家,便停了步子,一名年岁儿稍轻的道姑递了东西过来,如蔓伸手去接,就见一方土色粗布包袱。
“这是为的甚么?”如蔓随手掀了一角,秦雨菱和沈冰也凑过来瞧。
那道姑一拘礼,道,“方才入观的施主托我赠与小姐。”
如蔓心下更起了疑,就问,“那公子可带了话儿?”
“他说这高香既是沾了小姐的手,也便有了佛缘,旁人再烧拜,遂不能灵验了的,原该由小姐收着。”
“这公子奇怪的紧,又和那白小姐一道儿的,想来也是尊贵之人了,五妹妹可受不起他那礼了。”
先前秦雨菱只是不与白瑶亲近,经了当街拦马一事,她遂更对那白大小姐添了些不满。
如蔓将包袱递与小厮,只说,“我当谢他相赠之仪,仅以表意。”
说罢,就各自分别了。
那褪了色的木门缓缓阖上,一行人遂径自登了车,既然心愿达成,就没有多停留的道理了。
秦雨菱仔细替如蔓涂了药膏,抬起眼皮道,“那随行公子又是何人?眼生的紧了,大嫂子可知道?”
王翾道,“咱们身居闺阁的,认识的男子,左右不过父兄夫君的,我哪里见过的。”
秦雨菱又转头问如蔓,“五妹可是从前相识了,他怎地送你东西?”
“想来也是顺手赠的,并不见得有心意了,我不知因由。”如蔓歪了身子,靠在车壁上道。
秦雨菱见说不出个究竟来,停了一会子,又想了旁的,便道,“那顾家幺小姐好兴致,竟是从金陵赶来了,清音观当真是个好风水的。”
“顾家是那商宦世家,官不离商的,如今顾家三位公子都在朝廷捐了官职,顾大公子更是担那翰林院大学士之名,和两江总督府上多有来往,实属寻常的。”王翾绾了绾发,就解释道。
“仍是咱们秦府好,正经做买卖,也不必攀附权贵的。”秦雨菱兀自点头叹了。
“也不尽然若此,这偌大的家业怎会仅凭生意来头就能兴旺了的?太太打理这一家子都颇劳心神的,况论这大江南北的买卖了。”王翾细细说了几句儿。
毕竟是闺阁小姐,对这些个弯绕的并没兴趣,左右是男人们操持的了。那话题很快就转了,一会子说西府街凝翠坊的胭脂水粉最是雅致,一会子又道城南瑶铺的首饰最是花俏。
“海花楼的淮南菜最赋盛名儿,去年我同大哥去过一回,那粉蒸水晶团子和香酥鸭珍端的是好味道了,真真教我难忘。”秦雨菱一手抚着肚腹,还没等众人接话儿,她便自顾自的又说,“不如咱们今儿就到哪海花楼一品,如何了?”
“咱们府里甚么山珍海味没有的,还缺这些了?”王翾葱指在她脑门儿上一戳。
“断是不能相同的了。”秦雨菱驳道。
沈冰听她那样说来,自然是动了心。
如蔓这会子肚子饿了,虽说不上赞同,到底也想在府外多逛一会子,下次出府,就不知何年何月了的。
王翾将帘子掀了,微微一瞥道,“也罢,刚过了午时,赶回府里少则仍需一个时辰的光景儿,先用了饭也未尝不可的。”
秦玉衍起先并不大愿意,后禁不住秦雨菱央求,又见几人皆是有意到那海花楼品菜,遂仔细吩咐了小厮,打点妥当了,才从后院儿入厅。
海花楼在烟波江东岸,三层木石朱漆阁楼,张灯结彩,金匾银字,一脉繁华兴旺。
秦玉衍包下了三层一间儿靠窗子的雅舍,避了喧嚣的人群,视野也十分豁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