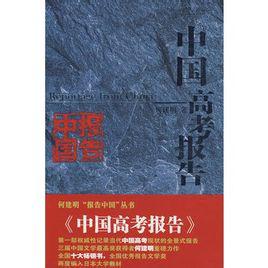公式献给高考-第1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可是二姐呢,她仍在广东啊!”字为十分懊恼。
“都是因为我!”飞快地旋起扫帚,幻想通过高强度的劳动,来发泄心中的郁积。快而有力的,抽打着楼梯,瞬忽间,便已是灰尘四溢了。
“还不是因为我还在上学,或者考试好点,她们就能早日脱离苦海,从中解脱出来了!我为什么这么的没用咧?为什么不能好好地争口气咧?为什么没有能够考上重点呢?为什么……”脆弱而敏感地神经再度紧张起来,简直像山洪一般地爆发了。
他气愤至极,痛恨着,自己,别人,所有的一切!
狠狠地一拳,砸向楼梯,那凸起的水泥碴子挤进肉里面去了。早已经没有了任何感觉,仿佛拳头还不是在自己的手上,有与没有,都是一样的效果,没事人似的。只是仿佛有无数个“轰”的声响,震荡在耳畔,心头仿佛被什么东西,给用力的敲击过似的,又仿佛有什么东西坍塌了……
刘师傅赶紧抬起头,看了看上面,发现没什么东西倒塌下来,便又继续晃着锤子,有气无力的敲打着。
血,红色的,潺潺流出。
两眼呛满了泪水……
那是些怎样的回忆呢?他开始把问题引向另一个焦点,那是尘封的历史。就为了一个与自己所处的身份不相宜的事情,而几乎荒废了学业。一再地强迫自己必须忘记一些事,一些人,却反而繁复无常地纠葛了起来。就因为一个顷刻的意念,他把自己给搅拌了。还记得那首最初的情诗,
芙蓉香
像一只婷然的鹤
卓立于清池的南隅
微风之晨
灼热的午夏
或者在夕霞,点缀水面的晚昏
一眸嫣然初颦开
鱼儿忘了嬉游,风也忘了愁忧
涟漪迷醉,似乎梦中酥香的温柔
甚至那不屈砥砺,因为
守望亿万年的雏形
而在缨水浸卧了千年的丑石
也愿意聆听……
一直都在偷偷地聆听
默默地,是丑石不敢倾诉的初衷
却一再地苦恼;哪怕芙蓉不经意的一个微笑
那颔首时的顾影,也定会在丑石炙火的心中
撩开“在河之洲”的歌喉
漾皱了涟涟的清水
是丑石不小心流露的问候
063
那仿佛是一个诅咒,从高一起,自己就再也没有能够超拔出来。明明是被拒绝了,却仍然作着年少痴狂的努力,与妄想。直到伤痕累累了,直到筋疲力尽了,三年的时光,仿佛只那么一瞬,就到了高考的跟前。期间多少的辛酸,总是苦水自咽,真正到了想要放下的时候,才发现竟是回天乏术,沉湎在自己的痛苦中也渐成堕习,像一个巨大的钳子攫取了自己。
多少次,独自一个人游荡在水库的大坝上,望着那6000立方浩如烟的库水,面对朝旭,或者夕落,竟再也没有多余的话,那是一个倾诉与倾听的好去所,看浪花飞溅,听潮起潮落,便如心声。从高一一直到高三,慢慢地品尝了一番。扑倒在路旁的草丛里,哭得悲悲戚戚,又笑得痛痛快快。那是些迷乱的日子,不知道为什么,直把自己沉浸在一种固有的心境里面,是积蓄后的挥霍,是落魄时的嘲讽,是多情必自伤的罪过,是无情的忠告,是最强烈的颤音,是最孤独的寻觅与坚守,是激烈的迸射,是冰冷的复归,是千年的一次焦灼的等待,是一瞬间的毁灭,是一个人的全部心事,是对一个人的执着,是铸定了的自己的一生的承担,是遭遗弃的一生的自己,是一个无法诉说的悲剧,是悲剧里诉说不尽的哀惋,是对明天的绝望,是对造成绝望的今天永无尽头的遭受煎熬与反抗煎熬的一次虔诚的洗礼,是注定了的,是人为的,是自己的迂,是自己的痴心妄想,是自己一生一世的绵绵无绝期的赎罪,痛恨着,并且忏悔着。给以主的悲悯,又怀有求赎之心,从来都是在自救与自责的旋涡里失去重心,被悬置着。
上帝已经惮怕了,他独自彷徨着,被遗漏在人间的一粒种子,是最后一个罪人,也是最后一个情人。只是一直回忆不起,却又遗忘不了,于是常常有些神经质地痛骂一声,并即又伤心枯寂地退守到心灵的空间里去。
他是被迫遗弃的孩子吗?像最后的一只秋蝉,隐隐地遁去,在自己的寂静里,也在自己的燥鸣中,空自留下曾经栖息过的枝头,与秋风共舞,蜕下的壳,盛接满腹冬寒,把晶莹的雪,挂在枝上。
但那却只是一个结果。被谁遗弃已经无足轻重了,并且还得寻觅;只是,还有寻觅的必要吗?放弃一种坚持并不难,当一个人决定老去时,或者重获新欢后,他就可以放言归居了。然而,坚持这样的一种放弃呢?就像彻底地忘记一个人一样。
他始终迷惘着,过去仍然是一个恶梦,白天黑夜的纠缠着,折磨着,啃噬着,腐化着。
他的反抗是一种徒劳,仍然是一个对影子的告别,仍然只是,只是一声对明天的允诺!只是,对于一个囚居于昨天,连今天都不忍步入的人,明天又是什么呢?是神话,是时空隧道里的骑士,还是已经无法寄言的死亡?自觉这许多年以来,自己真是一个活死人,是一具分文不值的木莱伊。
到最后,要反抗的是什么已经不知道了,却仍旧要执意于反抗,要追往的是什么也早已忘了,却似乎仍执着于追往,要面对的是什么更是不知为何,却依然执迷于一己的内心,要控诉的呢,要轿正的呢,要改造的呢?却似乎仍执绋怨恨!
捐弃了结果后,连反抗的过程都需要要反抗了,反抗已经拘陷于反抗自身。一切都归寂于内心的丑与恶,善与美,埋葬了自己,又要拯救自己,与遥远的东西对话,永远弥留于昨天之际。把内心的沉痛与悯怀,遮饰在一些日常的琐碎中,掩而不得,哭而不得,笑亦不是,咒亦不是。以最敏感的心来体会人间的冷暖,却反以最冷漠的表情来回避,来应付,因而是常常脆弱的,但又似乎最是坚强。然而灵魂的不安,又何止于涌动呢?在一些看似零散的生活中,却承孕着不屈的精神内质,什么是放弃,又什么叫坚守,没有人看得出来,没有人认真去面对,没有人笑,没有人哭,不是因为没有人,仅仅是一些无所谓的生活,而终究是没有人值得相与倾诉,终究是没有值得相与抚慰,没有人值得相与搀扶!
064
靠精神的自持强打起精神,苦撑于废弃的国土里生活,却又十分万分不幸地,在试图的努力中被一再地废弃,精神的危机并且精神的自救,全部暴乱于灵魂的绝望与反抗中,欲罢不能的尴尬既打击着人,又激怒着自己,累累的伤痕却只能在那些零散的琐碎中,避风躲雨,或者苟延,或者挣扎,却无一不在矛盾中,在走出矛盾之前,终日反复着历经并被磨难。
然而又时常痛苦地感觉到,正是那种欲罢不能的尴尬,才正是一个人的生命最本质的状态。只是可惜,却并没有获得严峻与严肃的认同,甚至连思考都被滤去,剩下脑满与肠肥。
谁能相信这是真的?
谁也不能相信这是真的,或者只是不敢。
在黑的夜,披一袭星辉,将一声无法抗拒的悲歌,低沉的放声……
“猪头!快点搞,不然一会儿就没你的料了!”亦书似乎有些疲劳,躺在板子上一动不动的。他在充分地享受着这片刻的休息,刚刚下楼来,去洗脸也是漫不经心的,左额上还有一些细小的沙子。
字为两耳像浇了水泥,压根就没有听见亦书在说些什么。一上午以来,心情老是疙疙瘩瘩的,也因为转移发泄的方式,致使劳动强度更大了。整个人就像个泄了气的皮球。既疲软,又极为不痛快,病怏怏地,下楼的时候都蜗牛兮兮的。工具早都不想拿了,全部都扔在了上面。手上不说,用肥皂一搓就好了,关键是鼻孔里,塞满了灰尘,仿佛永远也抠不尽似的,黑黢黢地,看着满满的一指甲,自己都觉得恶心。没法了,只好认真地洗起来,肚子再饿也得忍着。俯下身去,双手捧起一把水,把鼻孔直接插进去,略微地吸一下,再空出手来,拇指和食指用力地夹紧,猛地一擤,才感觉不那么拥挤了,反复地搞了几下,渐渐空荡了许多。然而仍然有些不放心,并用手指抠出来,觉得没那么脏了,这才算作罢。
“我要打电话回家了!”像个孩子,拖着哭腔嚷嚷着,嘴巴噘起个老高,海拔有点滑稽的样子。
“先吃饭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啊,还得首先响应中央,解决温饱问题吧!”亦书扭了起来,双手支在背后撑着,还不忘皱起嘴巴来笑笑,把两个牙洞对准着人,像那碉堡里的机枪口,“呼呼”地响着,呼出两股气流。
这工地上的活,也委实不是他们干的,为难人了,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尚且耐不下吃不消,叫两个刚出校门的小家伙,又如何折腾得起呢?字为那活还是较为简单的,可以快点,也可以慢点,虽然他自己养成了这“自虐”的恶习,手还一直隐隐地作痛咧。但总也没人紧催,由着性情来,倒也不是很累,只是灰尘太大,脏。发丝上早就布满了灰,一巴掌过去,便如同冬天里雪松针上的雪沫,沸沸扬扬地落下来。
亦书可就不行了,两个小工同时伺候四个大工。光和灰解水泥,就够人受的了。还要负责提灰,在地上还好,要是搭起了楠竹排板,通常是架在半人多高的铁凳上,那就更难了,不仅要拎灰桶,而且还得使用臂力,把它给提上去。虽说泥桶不大,可自己没手套,那铁丝做的把手,硬是勒得细嫩的双手几乎要脱皮了。然而师傅们又都要催着,搞得人毛心火辣地,尽有破裂的灼痛感觉。
065
再说这鞋子也不适合,一脚下去,就像踏入了泥沼当中,水泥灰立马形成合围之势。师傅没说,有经验的工友却也只是半字不提,书本上的那点知识何曾管用?事后那些德性的人才笑着说出原因,但早已被这水泥灰给咬伤了好几处。比长了牙齿还厉害,钻心的疼痛。
他开始没有发现,催得紧了,也顾不得,只是后来觉得不对,脚后跟怎么老是隐隐地会痛起来。仿佛那地方的肉,正好被人偷着挖走了似的。再后来就越来越难受了,一会儿是脚背,一会儿又是脚指头,最后是整个的,一起痛起来,要得了命的。
他便赶快癫向一边,脱鞋时才发现,袜子已经渗进肉里面去了,粘着,如同捆在树上的绳子,经年之后,没有烂掉也没有解开,竟长到一块儿去了,被树含着,夹在里面,嵌进树干里去。而袜子外面,却只有鸟屎那么大的一点水泥,团团地转着,呲牙裂嘴的,撕掉了袜子,脚下却同时少了三四块皮。全都粘在袜子上了,还有血痕,露出细小的,分布得如同蜘蛛网状的血丝来。
可恨的是,作为工友的小方,竟咧开嘴笑了。并且还一个劲地催着,说他一个人搞不过来。狗日的,良心被狗叼进厕所里去了吧!小方是本地人,读书没混出个名堂,却壮如牛,也因为只有些力气好使,现在也只得沦落到工地上来,尽搞些零活干干。三四十岁的家伙了,到现还没个正经样,要不是因为在小巷子里有两间祖传的小老屋,说不定到现在还没有媳妇咧。老婆在家里守着门面,卖些水果,他则时不时地出来转一下,挣两个灵活钱。
四个师傅也丝毫没有半点同情,甚至视而不见,只一个劲地喊着要灰。一个比一个催得紧,一个比一个催得急,比之于索命的无常老鬼都毫不愧疚,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把个可怜的亦书,折磨得死去活来的,下班前还提醒着,要亦书下午时提前过来和灰,免得下午又要拖住后腿,否则就要求老板换人了。
人们都很迅速地走下楼去了,他们两人才不得不也都有了些行动。字为痿靡不振的,手背上还有未洗掉的血痕。亦书也好不容易地爬起来了,却还只是耷拉着脑袋,一瘸一拐地跟在后面,再也没有刚才的那股活泛劲了。扶着楼梯里面的墙壁,一步三歪地摸下去。
“大学生,大学生怎么啦?”一个右手拿着啤酒瓶子,乱灌一气的家伙,左手抱着个大盘子,斜过眼来,很得意地奚落着,“哈哈”地敞开怀来大笑道。嗓门粗得像那大象的屁眼,让人受不了,竟而又引来了无数的好奇者。眼睛齐刷刷地扫来,要杀人似的,瞅着,又好比那面对古董时的神情,专心,却又毫无见识。字为只好勉强振作一点,打起精神来略视一番。
“你又不是不晓得,脚正痛着咧。”亦书没好气地回敬一句,“师傅,厕所在那儿知道吧?突然想要拉肚子了,唉哟……”
066
字为被这一句给逗乐了,按照句意来分析,这可至少有两层含意。但亦书他肯定知道具体在哪儿,并且他现在一定不想去上什么厕所。而这近似请教的问题,却是在大家都在来往食堂的路上,自然就别具意味了,拐着弯骂人的意义就在此,痛痛快快地骂出去了,对方却无知无觉。亦书故意捂着肚子,却又并不去,也不要求他回答,单是拿着屁股,调过去,像要放炮似的,对着那个大钵子。
字为忍不住笑了,凑过去小声地咕哝着,乐着两人嘻嘻哈哈地,一路径直往食堂走去,却终究捂不住嘴,单是笑个不停。
那家伙好像也听出了那话有点玄,不过也不十分明白的样子。继续喝着他的酒,动作很慢,似乎若有所思,但一会儿放下瓶子去,又猛烈地往嘴里赶了几筷子饭菜。
“要是再灌一点毛狗尿,可能就好了!”亦书骂不择口,指着伤口说道。似乎已经是在说自己的脚了,又要撇过头去。
“妈的,一上午几个人合伙整老子一个!气死我了……”
字为心里头猛地一惊,难道他们欺生?“为什么呢?”
“鬼才知道!不想再和他们一起干了。”
字为默想着,看着亦书这走路的样子,心里不免一阵阵的难过。这些人是麻木的,也是辛苦的,然而肉体的劳作,最后又全都归之于肉体的消费与满足当中。惟一的生活情趣在于获悉别人的痛,与伤,在远甚于自己的痛苦之后所激起的得意,或者在能够有效地掠取别人的苟笑或悲戚后,来化解自己生活中的苦闷与累赘。浸染自己的干涸灵魂的,是掠夺后自我满足式的陶醉,哪怕这需要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也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