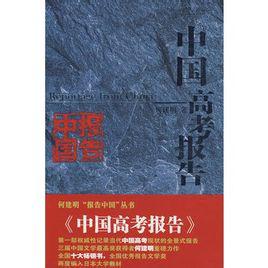公式献给高考-第1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牛的痕迹来。“没吃过猪肉,总见过猪跑”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那是对穷人的嘲讽,或者同情,还有些许的悯农情怀。然而现在,似乎也确实是倒转了过来,“没见过牛,但总吃过牛肉”吧,才是时代的主旋律,是文明的进程,也是富裕得浅薄的表现。早些年,不是有农业大学的学生,误认为麦子就是韭菜了吗?但即使如此,大概还有不认识牛的人吧。
“狗日娘养的,下班了不成?怎么什么都没有。”猫爹转回去,“你们先等一下,我送盘子回去,转过来再带你们一起到外面去。”
就在大道的对面,不过穿过这车水马龙的大路,倒真挺费劲的。照猫爹的意思,这面条份量足,价格便宜。1块5毛钱就是填一大肚子,不过不管饿,晚上倒是可以来吃的。所以中午的一餐,一定要在食堂里呆着,或者到外面去吃盒饭。反正都是3块钱,虽然难跑,但菜多好挑选,容易对准胃口。
“什么都可以将就,但在媳妇和饭菜方面,最好要好好地照顾自己。”猫爹说着。
大街是一眼望不到头的,整齐而漂亮的房子,全然地排列在两边。高大的法国梧桐,一字溜儿的排开去。然而多被锯了,空有肥大的树杆,比断臂的雕塑更残缺,只是并没有维纳斯那般艺术化,强壮,而又显出病态的绿化。
小面馆并不大,然而人多得很。叫好了要吃的,猫爹就坐过去了。按照猫爹指的,字为单是愣着墙上的面谱,挑了一圈,觉得还是素粉要便宜点,于是才要碗粉。
“宽的还是细的?”
“啊?”字为刚转过去,却被老板叫住了。
“是要粗的,还是要细的?”老板只得重复着,擦了把额前的汗。
“随便……哦,那就粗的吧。”
“荤的还是素的?”老板望着他。
“素的。”字为觉得别人都在看着他了,赶紧回过头去,这才松了口气。
“大碗的还是小碗的?”老板已经确认他是新来的了,也不知是因为真诚,还是故意,偏偏要追问着。
“小的!”他低着头,只动了下嘴,冒着几个字来。
亦书也开始笑了,他懒着说,只要了份同猫爹一样的。
猫爹吃得特快,连一点汤水都没有给剩下,毫不客气地,全给倒进了肚子,又坐过去,迎着大风扇狂吹起来,一屋子的汗味。
字为刚吃完一半时,猫爹擦过嘴巴。笑道,“小××日的,工地上要粗,做活得脸皮厚。否则会被瞧不起的,吃快×点!”
043
“还坐着搞么咧,个人快点去料库找板子,不搭铺的话叫你们晚上睡个××!”猫爹打着哈欠,歪着身子侧躺在床里头,反手拧开了电风扇,像一条蜷曲的狗,手足全拢并着,搭到了一块去。
“唉!我日个娘卖×的,连这风都是热的啊!狗日养的个天道,这样还叫人么样活,也不晓得屋的(家里)搞得么样了?”
亦书只得再向边上挪了挪,一只手压住肚子,另一只手抓在床沿上,以防滚落了下去。紧接着,猫爹就又朝外边磨了一屁股。平躺着,睡意更浓了。然而却并没有睡着,又说起了话来。
“要不是下午要上班,我倒还可以给你们仙人指路,别的好说,作铺的板子可是马虎不得的,搁屁股、歇脚、挺腰杆的地方,弄得不好的话,就要影响工作的。”
字为心头一热,这猫爹除了精瘦,倒也还值得信任。只可惜下午有事,不免遗憾。这破地方,连个现成的床都没有,在家里睡觉,只须洗完澡,脱下鞋就可以了,没想到这会儿,却还要自己去先搭铺。
“人多好办事,多些人,总有个相互照应,跟个大人在一起,就没啥好担心的了……”猫爹终于有所释怀的说着。
“你”,田爹仍就是慢慢悠悠的,“有事就去忙,我带着他们俩就行了。”
字为听田爹那近似悟了仙道的声音,心里颇是宽松了些。
“日!怎么一下子多了这么多的人?”一个矮个儿,光着膀子,癫着屁股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紧接着又是一个中年男子,黑的皮肤,胡子拉稀的,再后面就是一个头发谢了顶的小个儿男人,':。。'大概60岁左右的样子。
“新来的,”猫爹眯着眼睛,“搞么×去了咧?怎么到现在才回。”
“肯定是去喂肚子了,日个××养的哦,热死老子了!”先进来的那矮个,努力地提着嗓子叫,很高兴的样子,神情颇为怡然的。将肩上的短衫往床上一扔,如烂泥般,一屁股坍塌到床上,搞得咯吱咯吱地响着。就那样地躺下去,腾起屁股来,敏捷地去掉了外面的裤子,右脚一蹬,把裤子就给踢向了床角,现出红色的裤衩,浑圆的大腿迸发出强健的力量。
“这两个是我们垸的,张田荣,小卵子日的那个,叫亦书,是张用光的。另外一个是栗林的,叫小朱。这个是小董,那是杨伯,”猫爹分别给一一指了一番,“那个是老胡。”
“用光的?他伯(爸)我认得,”谢顶的小个子男人,望着亦书,脸上掠过一丝诧异,“你伯到我的(我家)吃过几餐饭,老早就认得的。我是你们隔壁垸的,要叫我杨大伯。”
“哦!”亦书简短的应承着,眨了眨惺忪的睡眼。而后又是一仰头,就侧过去了。
“他怎么会让你出来呢?又不是缺钱用咧,你要是帮他好好守住那个店子,让你的伯娘两个跑车做生意,比在这儿搞强多了!”杨伯极尽遗憾地问着。
农村人都会打算盘,那是精耕细作的岁月里所养成的习惯。一分钱更是钱,买蛋孵鸡,鸡成群蛋装筐,积蓄起来买牛卖猪,一步步走上致富的道路,是媳妇们都懂的大道理,这种发家的故事,绝不仅仅只是小说中的神话,在农村普遍得很。但也因此,这种在经济大潮冲击下,越来越见拙笨的积习,因为太过注重眼前的利益,就很明显地制约了他们自身的发展,性质随着时代,悄悄地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精打细算竟成了农民自身无法根除的狭隘性。然而这种节约的意识,却是值得提倡的。
044
“还不是没办法,一开学就又是不得了了!日噫,弟弟早就冒读了,小学都还没有毕业。二妹也说读不进去,但她都还没有上完初中;大妹红今年初中才毕业,考进了县二中。我是高中毕了业,能不能够继续读还得另说,家里那点玩意,根本就抵不了两个人半年的。”
“你伯可是个能人啊,车子、店子、场子(田地),又是一大家人的肚子。不过,做是做得,但也的确是做得苦啊,小小年纪,搞得比老子都苦!”杨伯深有感触的说着。
“我还以为应该喊你大哥呢,这么年轻的一个伯伯,看起来比我伯还……”亦书嬉皮笑脸地劲又来了,顺势演绎下去,想气他一下,封住他那婆婆妈妈的嘴,但不想一句没完,就被杨伯给骂回来了。
“狗日养的东西,你个苕儿(你是个傻瓜)!瞎说乱嚼的,亏你的个××儿,还高中毕业!”杨伯哼哼地叫骂着,“你读书读到牛胯马裆里去了是不?说话冒大冒小,骚气腾腾的!”
“瞎××说,你的伯看起来比杨伯要老吗?读书的伢,一个比一个乱缠,也不晓得在学校尽学了些么××东西。”猫爹也有些愤然了。
小董只是笑笑,调过头来看着。
“那算个××!论起辈份来,说不定他要真要叫你哥呢!”小董说着,“我跟我们垸的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家伙叫哥,他的儿今年也六十多了,我还是跟他叫哥,他的孙比我还要大一点,但仍然是叫哥。日噫,一屋祖辈三个,都是哥,哈哈哈,要是他的曾孙出来了,却得管我叫姥姥……”
“我日,那你的辈份不是好高啊?”亦书有点故意地问着了,支到另一边去了。
“那是,尽是瞎××搞……呃啾!呃啾,呃……我日,么样搞的,哪个××日的在骂我老子了?”小董搓了一把嘴巴,不再说什么了。
杨伯一脸的不快,却也不再说什么,单等他们去热闹。
田爹撑了个缝似的,打开了下眼睛。身子像一滩软泥,牢牢地贴在墙上,头又歪向一边,乌红厚实的嘴唇,显出憨性的模样来。接着,那迷迷的缝也缝上了,连鼻孔都没有动一下。
“么样咧?高中毕业,是今年啊……日,××大点的的伢就高中搞完了。考得么样咧?”杨伯在他们都骂过之后,忽然又来了兴趣似的,关心地问着。
“狗屁!400大××点分,不上不下,不痛不痒的。不读还真有点舍不得,毕竟有那么些;读起来又不够线,还差那么个一码子咧。”亦书羞愧着,却终于还是有些愤然地说了。
字为隐隐地有些不自觉起来,于是勾下头去。瞑目小憩似的。
“那一个呢?”杨伯指着字为问道,“你的同学?”
字为终于感受到了焦虑的重量,顿时觉得又有无数的怀疑的目光,同时集中地投攒到了自己的身上,身心有即将迸裂的危机。却觉得假寐更其冗长,但又怕被他们发现自己还醒着。便微微的动了下,协调了一下全身的不自在,作出刚睡不久的困苦,仿佛那讨厌的苍蝇又来骚扰了。
“嗯!是隔壁镇上的。”
“也考得么样了咧?”小董也忍不住要问了。
“兄弟,差不多。”亦书的语气也有些不足了,悻悻地绕着。他自己的倒无所谓,但对于字为来说,还是有些顾虑。
“也是400多了,那是400几咧?”小董个××人,一直紧咬着,憋到现在,他还非要探个究竟了。
“比我多,你紧问个么××咧。说到你还不是不晓得,睡!”亦书坦然着,却又有些发怒,只是不知道该对谁动气,斥责着小董。
“你放××屁,小×日的,还真是读到牛胯去了!”小董不再说什么了,扭过头去,颇有些愤然了。
“看来都只有走三批了,”杨伯说,“我的女儿去年科大毕业,小儿子今年上大二,在华农咧。”露出一脸的骄傲,像喝多了后,颇有些醉意的样子。
“那肯定都是些好学校了,”亦书压低声音,慌乱着瞥来瞥去的,嘟哝着,却又突然提高音量地大声问着,“那工作么样咧?好学校毕业后,应该有好大几千块吧,怎么你也不晓得在家多享两天福咧?”
“那福我是享受不了啊,生的就是做牛做马的命。”杨伯笑笑,也不再说什么了,倒下去就要睡。
“出来炼下也行,不然就不晓得要么样用心了。开学肯定是要大钱的,好好的搞一段时间。”刚躺下去的杨伯,却又要坐起来,脱下胶鞋,抖了抖里面的沙土。把鞋帮子又狠狠地磕在砖头上,洒下一些结成块的水泥。赤脚上有不少的血痂子,有些已经结了壳,污黑的一坨,是被水泥给咬伤的吧。
“不会吧,几千块的工资了,还要你出去搞个么××咧,那还不如不用去上大学了。你也是的,真是不晓得享个福!要是我伯,现在肯定坐在屋的摇扇子了。”亦书偏要绕来绕去,搞得杨伯也确实有些不好意思了。
“以后有么×不懂的事就问我们吧,在这里还是要干得熟一点的,我们这几个。”愣了半天,杨伯这才摇起蒲扇,很热心的介绍着。
一会儿大家就都睡着了,呼噜一片一片的。
045
闷热的正午,更是疲倦的时节。过道里也时有阵阵的风,不过像热浪,一卷卷地袭过来,磕碰在人身上,就有被火红的烙铁砸中的灼痛感。有什么被吹动起来了,混钝而沉重的声音,使这个无法入眠的午休,更加的烦闷。
田爹坐在地上的断砖上,背靠着墙,迷糊时,把剩下的三粒扣子,慢腾腾地,索性也全给解了。厚重的嘴唇并没有土地那么的贫瘠,翻卷着。这种睡姿,是做田(耕地)时短暂的小憩,却只有庄稼人,才能充分地领略其中的安逸。对于两个学生而言,这下却实在是有些惨。亦书终于被翻身过来的猫爹给挤下来了,半边身子悬挂在床沿。这才只得挪下来,一屁股坐到床边那踏脚石上,头靠着床沿,像一个可笑的不倒翁,左手撑在木板上,右手抓住床沿,在猫爹的铺边左右晃着。字为单是在砖头上铺了张报纸,又将包抵在墙上,垫靠着,头深深地埋在两个膝盖之间,稳稳当当地闷在那儿,像一个油墨泼写而成的“Q”字。
突然一声低沉而冗长的口哨,将两个孩子同时给惊醒了。字为委屈地揉着眼睛,亦书一个劲的骂热。田爹却仍旧死猪一般,背贴着墙,头像被钉在了墙上,或者那墙上,另外还有颗钉子,拦着,把他的一个硕大的脑袋搁住了。享受着憨睡的惬意,一动不动的。
“日他娘的个大块子麻×,才睡了几得下,”猫爹露出些不平,有些抱怨了。
老胡睡得死沉,酣声如旧。小董壮实的胸膛宽而且平,腹肌一排排的,有山上石头的阵容,肚子缓慢而有节奏的起伏着。
“走啊……走啊……”杨伯就像一头即将下田的老黄牛,两手后拉,两腿前拖,膝盖和肘关节同时撑地,屁股拱成一团,渐渐地向高处翘起,弓起一个弧度很大的桥。前额却还搁在床板上时,梦游般地,拼命想睁开眼看看四周的情况,嘴里却早已催着别人了。
猫爹刚起来,亦书就像一根柱子,立起来了,东倒西歪的。却又立马左倾着倒了下去,比蛤蟆跳水还无所顾忌,双手撑着,趴到了床上。眼睛都不再闭上了,像是夏天里,因缺氧而翻亡的那种死鱼,全白着浑浊的眼睛,肿着因腐化而膨胀的肚子,浮在水面。亦书咂巴着的嘴巴,即已发出熟睡的鼻息。
“狗日的,还不快点起来,去找板子搭铺。待一下再睡,不然一下雨你们晚上就睡个狗××。”
“我有闹钟,怕个么×咧,莫吵了!”亦书像那快要断气的公公,垂死地挣扎着,说话有一下没一下,长呼短吁地。
一阵嘈杂过后,一会儿就都走了,字为什么也没有说。但耳边还在回荡着老胡的嘀咕,小董的叫骂,以及杨伯一声不吭地离去的脚步。猫爹早就走了吧,只是没有察觉出来。字为缓缓地爬过去,将包塞到猫爹的床底下。
整个人在一站起来的刹那,突然觉得好像地动山摇了,来回晃着,差点就摔倒在地上。幸亏这房子小,床就在一步之外,他好不容易的双手撑在了小董的床上,再晃了晃,感觉是站稳了的时候,才转过身来,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