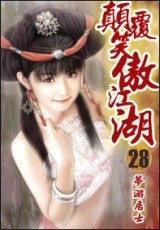狗血江湖-第3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他继续问:那人是不是,脸上有两道横长的疤痕?
怎么回事,他是打算打破砂锅问到底怎么的,无奈点头:是。
他靠在椅背上叹气:于果,我终是没能想到,你会这样对我。
这算什么话,我泪流了满面,将憋了几天的话一古脑道出:我怎么对您了?当时被那人用迷药挟制了欲行猥亵,为了不给您丢人,我瘫软时拼了内力一掌让他致了命。头回杀人,心里真怕得要命,叫天不应叫地不灵,若不是随后尘西来了,我真想死了算了。您怎能这么说?
他却冷了个脸道:莫要扯上尘西,尘西许是不知情。你却难道不知,你杀的那人,原是大内的高手李三,更是在我母后杯中下毒的祸首!
我大惊失色,差点语塞,终是轻轻道了句:我当真不知。
他即便偶尔动怒,全无这般阴冷的笑过,看了这样的笑,心里猛地抽搐。他说出的话也如笑一般阴阳怪气:为了我大哥,你当真是宁愿豁了命不要,也要表这衷心。我竟傻了,那么多年,你们岂会是没半点真情的?
我摆手阻止:大王,如果那个二道疤便是李三,那人确是我杀的,如果您觉得我办的有什么不妥,您要骂便骂。当时情形危急,我又的确不知这人的来路,为了保命拼死一搏,不然您回来,如今就是为我收尸。说句不好听的,若不是我答应了您,危急时刻必然能够脱险,拼上最后那点意志,我被那人先奸后杀,跑不了。求您千万别把罪名越扣越大、越扯越远,当然,您若是想伤感情,您就尽管扣。
我嘴上说得顺溜,心里却像插了把刀似的,他难道父母忽然死了,打击太大,失心疯了,咱们都那般蜜里调油了,忽又说这些胡话。
他沉默望着我,我有些恍惚,仿佛错觉那眼神中透出的全是担忧心疼,不是在琢磨我有没撒谎,然而这当然只是幻觉,他说得有板有眼:于果,你大可不必装,皇兄的那封信你我都见了,现如今,你还同我谈什么感情?
我急急问:什么信?你说那封无字书?我们一起瞧完,之后都忘扔哪了,他葫芦里卖什么药我哪里知道,不能凭这么一封没有字的信,诬赖我罢。
他冷哼一声,从桌上拿起一封信递我,正是那封无字书。
我一拍信,叹气,气有点短:您倒仔细,您且说罢,我是怎样表这衷心的?
这一天戏文听得多了点,竟是一场比一场更让我心惊。他取了信,拿了那白纸在烛火上烤,慢慢地,居然真现出几行字迹来,脸上的笑愈发凄厉,摆摆头,倒似在嘲讽他自个儿。他又递给我,我拿起来,读得瞠目结舌。我认得,那果然是项莫远的字迹,写的却是:夜半借卿卿玉手即成大事,远字。
就这么几个破字,我目不转睛上上下下读了好几遍,木呆呆瞧着那些字迹淡去,又成了张白纸。妈的,项莫远,你祸害老子忒煞费苦心了,谋划这么一出,真真比直接要了我的命还伤脑筋。我的罪过,不过是当年对您老人家不够上心,可那年头我除了等着嫁你,几时也没动过旁的歪念头。
我脑子再不够使,平生再不爱辩白,这个时候不和师父辩明,我就万劫不复了:我说我没烤过这破纸,估计您现在说什么都不会信。我只问您,项莫远他要杀这人做甚?
师父的声音越来越清冷,瞧着我,已是瞧着杀母仇人的恨意:他忧心我母后的手中握有改立储君的遗诏,着李三杀了人,自然要神不知鬼不觉地宫外灭口。
我有些绝望地冷笑:灭口?您得了吧,我差点就被这李三灭了。您对我怎么想的,我现在恐怕没资格说了,我一个被栽赃的有什么资格,您必定恨我恨得不行。可我还是想问问您,这么多年,我不信您对我的了解那么肤浅?我心里就算没有您,但凭这点师徒情份,我也干不了这龌龊事。更别说我这心里头,向来就只有您一个,没别人。您觉得,就算我读了这封倒霉的信中信,我凭什么要答应了他?
他别开眼去:于果,那个李三的功夫,我是领教过的,别说那刻是中了迷药,你纵是有半点马虎和差池,便决计不是他的对手。铁证如山,教我如何信你?从今往后,你再不必对我说那情字。
这末一句说出来,竟是不带丝毫烟火气,他那里糊里糊涂心冰冰凉了,却不想想我这里是如何的肝肠寸断。他怎么会信不过我,那咱们这一路从甘凉回来时的相濡以沫又算什么。难道他不是用了心悟情,而是拿个戏本子写了桥段过日子。
我抹了把泪,竟想不到说啥,一时气极,递了桌上他的剑抛在他手里,见他不慌不忙接了,我吞了混入口中的泪,哽咽着说:您倒还记得我是您教的,您却不晓得为了谁我才肯拼上这命。您既不信我,不如赶紧捅我一剑完事,我死了不打紧,您好好扒开我那心细瞧瞧是正理。瞧完了您要是觉得冤枉我了,别忘缝上了,给我添口好棺材。往后逢什么清明冬至的,记得给我烧点纸钱。我的命本来是您捡的,您几时愿取了去,我是绝无怨言。
我还想多说一句,您可记得,坟冢上立块木牌子,记得写上项门于氏之墓,省得我到了阴曹地府都没个名姓。可这话,哪里还说得出,泪想是愈发止不住,噎得我只有吸气的份儿。
他握了剑重新搁桌上,却不屑再瞧我,只幽幽道:于果,你明知道我下不去这手,我虽错看了人,却不及你狠心。你犯不着对我使这招。
我基本绝望了,话痨白当的,什么叫百口莫辩?瞧瞧我这会儿混成啥样。师父死都难信我,亲娘被人毒杀了,口我亲手灭的。换了我,我会信他么?
我会,所以我更绝望。吕佳音白天说的话慢慢浮现起来,我脑中闪回她说的每一句,直到见着师父,直到师父现在告诉我,他看错了人。
下一次还会失算么?吕佳音走的时候我瞅着她那身姿,还嘀咕着,这一趟,一切终于在我掌握了,以为天上掉馅饼,今年轮我家,想着他的时候,笑便从心底涌出来。
没有下一次。等着他来料理,我不如紧着问一声:您不杀也不剐,接着打算怎么料理我?
但凡他下得去手,哪怕整得我生不如死,我还真就认了。
他这晚上一回来,可是都盘算好了的,道具备得挺
54、休书 。。。
齐全,一样不带耽误工夫的,又打桌上递过张纸来:原本,我虽当不成那孝子,却也不能不追究。可为着顾念这场情分,你我从此就当,恩断义绝了罢。
顾念情分?师徒,还是夫妻?我拿着那张轻飘飘的纸,那是纸休书。
这些年,不管我每回再怎么被他提拉到更高处,再摔将下来,我总还是坚信,老子是个皮实孩子,不管遇上什么难事,都能心平气和地抽离。因为至少我还能无所顾忌唤他声师父,哪怕把所有的火都熄灭了藏起来,只要他还在那儿,我便输得起。
我杀李三那晚,被药迷瘫软了的身,比不上这一刻,胸膛这颗了无生机的心,我再无气力奋力一搏。开演的时候我无比兴奋地上妆试行头,说服自己就算登场,我顶多算个玩票的。我全忘了这个茬,入戏太深,就不好谢幕了。
我透过迷离泪眼去瞧他,雾气蒙蒙看过去,竟真的瞧不真切了,这还是那个温润的笑着,眼睛里只装着于果的项莫南么?眼前的决绝是如此的分明,昔日的柔情蜜意反倒成了最可笑的幻梦,来将此刻映衬得生不如死。
作者有话要说:大虐了大虐了
希望大家不要嫌弃
棒棒糖吃了一半,被打落
我的确不是神马好人
所以,肯定还有糖的
55
55、前路 。。。
作者有话要说:要坚强!
把你的影子,加点盐,腌起来,风干,老的时候,下酒…… 《夏宇…甜蜜的复仇》
我傻呆呆的不知站了多久,师父对我再无只言片语,等他似乎厌弃这样的僵持,终于起身往门外而去。我想,这该是我最后的挣扎,他心底该不会这么快就忘了我们在一起时的温情脉脉。我扑过去,想扑到他怀里,贴得更近些,心贴得更牢些,求他细辨原委,我多少盼着他能揉乱我的头发,说一句,于果,我信你,先前不过是逗你玩儿。
师父便是师父,方察觉我这一扑,已轻轻一跃,纵身一丈外。我倒是去得太猛了,没料到他这一退,猛地跌下去,匍匐于地,头离着他的脚不过寸余。
师父没有片刻停顿,估计搀扶我一把的念头根本就没起,谈不上任何犹豫,手掌擦破皮的痛还来不及传到脑子里,他的身影已消失眼前。
我失了嚎啕大哭的力气,只慢慢起身,席地而坐。我头一遭想到,我若是没有喜欢师父,该是件多好的事。
我那颗心,大约早都起了茧子,所以握着那张纸,我还真他妈镇定,直愣愣居然还能走道,泪抹干了便再无一滴,回了当初我那客房。摸了些细软收拾几件衣裳,打了个小包袱,晕晕乎乎出了府。肩上还背了师父送我那柄剑,挺重的。
刚出那道门,我突然想起一码事来,风风火火又潜着回到书房,那烛火,已然全都灭了,我摸到桌上另一张纸还在,赶紧揣怀里藏起。幸得没有撞见师父,不然他兴许会说我销毁证据,老子还得受一番折辱。这样打紧的物证,他竟忘在这里。
大约是魔怔了,我在师父方才那张椅子上,坐了片刻,想尝试体谅他一样绝望的心情。却发现全不能够。浓浓悲伤袭来,令我措手不及,那许多夜畔私语,如今照上心头时,仿若今夜的残月般惨白。
吕佳音竟是对的,我才得了些甜头,便遗忘了师父是什么人,他从小又受了多少委屈,他心中装了这天下,我却失手帮了项莫远,他口中的遗诏不知所踪,便失却了那最后一线生机。亲娘的性命,失之交臂的皇位,教他如何不恨我。
于轼竟是对的,管你愿不愿成为这个圈子里的人,天罗地网,怎样都是个逃不开。不懂得防守假扮超脱,就必得承担一败涂地的恶果。
尘西竟是对的,温水煮蛙,钝刀磨肉,我以为我置身事外心在江湖,便不会当那刀俎上的鱼肉,却浑然不觉,这个地方,何尝不是江湖。
我随便跨上匹马就往宫的方向猛追,我一个路痴,此刻那条路在我眼前却极为清晰。
颠簸里,我忆起方才那次扑空跌倒前,我与师父最后的那番,不算道别的道别。
他分明不愿再与我分说,我却非要争辩个是非曲直,说到后来,竟有些口不择言:照您这么说,我为了心上人,对您还真煞费苦心,极尽勾引之能事。您不是问我过欢喜不欢喜,我一直忘了说,您的身体真不错,我满意得很,徒儿是不是该当跪谢您的盛情款待。您要是觉得不甘,便思量思量,是不是也该怪您自己晚节不保,没能为您的心上人守身到底,让我白白得了这便宜。不过您尽管放心,她今天还来找我来着,她对您一往情深得很,不会因为您失了身,便降罪的。她还心心念念的盼着与您重修旧好。
他望着我不说话,像是皱了皱眉头,当是被我噎得有些无话。
我又说:您就这么放了我,岂不是便宜了我。您如此仗义,我便劝了我那远哥哥,同我双宿双飞,把那皇位拱手还给您可好?不过,他会不会如此俯首贴耳,我倒全无把握了。
对自己也好,对他也罢,我兴许确是一个残忍的人。
他连冷哼都无,无所谓地答道:随你,这同我再无干系,只盼从此,莫要让我再见到你。
果真是恩断义绝,过了相依相偎的昨夜,连见到都觉得厌烦。最后,我喃喃说了句:项莫南,我哪有那么本事。你不过是下不了手,让我为您的娘亲陪葬罢了。
他顿了顿,轻道:你不配。
他最末的话音,在这夏末的空气里,清晰冷冽。
我驾着马不是要与我那远哥哥双宿双飞,我是去找他索命。
我再怎么错,也只是当初对他未曾敞开过心扉,他有没有知觉还未可知。往事再不堪,他在我的脑中,永是那个山路上,带着最澄澈的笑容,与我挥别的少年人。始料未及,有朝一日,他竟成我要伏的魔,要降的妖,宁可同归于尽方不含恨的仇家。
与他同归于尽,于我虽说死得有些不值当,但我此行,若能既成全了师父,又还了我清白,好让他此生追忆我时,记得不是那些惨淡往事,而是我仅存的英勇、残留的爱意,便再无什么不值得。
老天厚待我,项莫远心思好得很,正独自在那书房中秉烛夜读,我随手点翻了两名侍从一名公公,悄无声息,站在他面前。
他抬起头,瞧着我那狼狈样,眼睛里有喜,更有惊。
他不是很老道?如何对我似毫无防备,我立刻动手便能血溅当场,而后自尽,毫无困难地完成一路上所有计划。
然而我没有,见他没有说话,我把那纸无字书烤了火,递给他,而后拔了剑,架着他的脖子。我太想充大侠,我想要他死个明白。
一名宫女端茶进来,见着这一幕,正欲叫喊,被我一手抓起桌上一红木镇纸,扔将过去打了穴,立时昏厥。六月飞了雪,今晚老天看不过,帮了忙,不然准心不能好成这样。
然而项莫远读完,告诉我,这不是他写的。
我凛然瞧着他,松了松剑,仍比着他的喉咙。他没有趁机夺剑,也没有叫人,我无端生出些勇气,我告诉他,那一夜我仓惶间杀死了李三,而李三,正是那刺杀先皇后的凶手。
他脉脉望着我,只说:于果,此信绝非我写,你若信我,便不会只身犯险,来此相问。我无意多辩,二弟不信你,正如同你不信我。你有任何难处,只管寻我来,总有我为你查探冤屈,主持公道,你若只想要我性命,便要细想想,切莫要寻错了仇家。母后虽不曾生我,却也教养我多年,我也是打小就尊她一声母亲。
他没有自称朕,不知究竟是演技了得,还是真的问心无愧,而后他只字不提那天的尴尬事,只一如既往对我诉那个情字,他告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