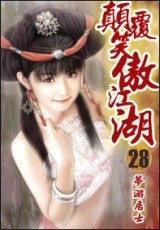狗血江湖-第1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大王不作声。又生气了罢,原来他那个时候就贪玩,是我愣没发现:哎,您以为我不想和您一道下山么。明天我们好好逛,现在别浪费时间,赶紧去吧,我走啦。
说完转头挥了袖子便走,却让他那么一轻触衣袖,瞬间被卷了回来,我只听得风声。我瞧不清楚他的脸,手却被他狠狠地握了一握,听见他低声道:我长那么大,头回夜游,你就请我独自一人逛窑子?
呃……听起来,似乎的确是我不厚道了些。当初约的那一壶花酒,究竟是风流雅致的一桩事情,现在见不得别人对他垂涎,就急急完成任务似的抓他立马去那儿宿夜。只想着伸头一刀缩头一刀,早死早托生。这又是何必,也不想想,他又不是任我摆布的小孩子,即便全天下的女子都垂青于他,他这样坚定的人,在意的终究还是一个人,于我又有什么相干。
听了他说的话又心酸,长到那么大,头一回。我早没了脾气,给自己喜欢的人拉皮条,妈的,自以为苦情,到头来还没落好。怎么办,被驳了面子的人是我,每次要陪小心的人还是我:大王,都怪我疏忽,您想上哪儿,我自然该当一路奉陪。
大王的声音平和了些:那便随便逛逛。
现如今我才理解月季所说的那只小兔子,手被他那么紧握不放,整颗心都欲往外扑腾,若不是走的道有点黑,他一定会看到我整个脸都在充血,要我如何心态平和地随便走。可另一边,心里的恶魔却不肯教我撒手,我想起成婚那一天离家的时候,不也是这般的不由自主,心猿意马。
没了红盖头作遮掩,还幸亏有这么多年的演技打底,总算逮了个桥头小摊,不着痕迹甩了脱手跑去,嚷着给我来半斤,一瞅居然是个成对卖鸳鸯许愿花灯的。
想着糟了,又造了次,这是能乱买的么,不得勾起他的伤心事。却听我家大王说,来一对。
我不好多说什么,只要趁他的心,买的什么又有什么关系,还不都是为了图个新鲜热闹。那个卖花灯的大概见多了两个男的来买灯,也不多言语,只给了纸笔,让写了愿望放河里去,我绞了脑汁也想不出写什么好,大王早早写完,注视得我头皮发麻,我只好写了个:祝我家大王永远安好。我给大王瞧了,大王看完了笑,可还是没给我瞧他写了什么。不瞧就不瞧,就算给我瞧,我还不想看。
我把字条折叠好,正欲塞入那个花灯里边,却发现那个卖花灯的给了我们两只一模一样的鸟。我不乐意:干嘛给我们两只鸳鸳?
卖花灯的笑得暧昧:小公子,大家心知肚明,何必要问呢。
我不依:你懂什么,不行,你得给我换一只,我不要两只鸳鸳。
卖灯的哪里拗得过我,给我换了灯。
我想起那刺虎沙洲,和师父又说起刺虎的那首诗,师父笑得格外开怀,还直夸不错。我惊讶得要死,问哪里不错,师父说自然是你吟诵得不错。又说又笑下桥点了灯,往河里头那么一放,风还好不算大,灯只缓缓地前进。那晚并非什么特殊的节日,往河里放灯的没有其他人,站桥上看着那对鸳鸯灯漂得老远还亮着。我心里头窃窃欢喜,反复暗示自己,不用管他那只灯上写的什么,更别想那吕佳音,只记着今天的这两盏小小灯火,也好。
师父靠桥上问我:你和我大哥也来放过花灯?
我再精细没用,我家大王偏就是那么煞风景的人,只好答:当然没有。小时候在天都,倒是和于轼一块儿去放过。
大王心情轻松的时候居然比我想象的还要八卦,哈哈,我爱这样的大王:刚才那于是庄,别是为的于轼吧。
我笑:可不是?您也看出来了,好笑吧,可于轼还在装蒜。芝芝想让我帮忙,要我怎么帮,哼,就层窗户纸的事,这还用我帮?成日里瞧着他们这双双对对,红裳翠盖并蒂莲,我形单影只一人,她这不是寒碜人是什么?
我家大王指着远处那俩小亮点:形单影只?要不要再去买半斤?
我咯咯傻笑,竟又有些饿了。
31
31、哼 。。。
如果我爱上你的笑容,要怎么收藏,要怎么拥有……《阿信…知足》
我说自己又饿了,其实是因为快被弄疯了。师父又一次的牵起我的手,笑得爽朗,说要带我去找吃的。他究竟想做什么,我实在有些闹不明白。
他指着那对鸳鸯灯,安慰我关于形单影只的愚蠢抱怨;他在飘香院的灯火下牵起我的手长久不曾放开;他告诉我他曾经也想过要和我来这个地方,只为了玩。如果到现在我还是没能猜出他一二分的暗示,那我就是一个白痴。
师父的心里头,一直是有我一个角落的罢,其实去年生日那晚,被他带着踩了风筝在暗夜滑翔,我就该当知道了。我只晓得他从小就格外隐忍、刻苦、冷情、孤傲、出类拔萃,却从未料到有一日会被他的父亲这样的与我送作堆,一起打发到天涯。他的心里或许有着数不尽的委屈和忍耐,也许更有他不曾熄灭的少年英雄梦。然而今夜,夜色温柔,灯火阑珊,他终究只是一个寂寞善感的少年人。
然而在这个世界上,不作白痴,那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我想起我说的泼出去的水,又琢磨琢磨他那只也许只剩下茶渍的茶碗,更忆起那天在太子宫他难得的失态。我总说求仁得仁,如果此刻我求的只是这个眼前人,那兴许,此刻我只需那么轻轻勾一勾小指头,大王便是我的了。而我这么个贪婪自私鬼,总在那里暗自盘算:爱于他而言是什么?是不愿被忆起的回忆,还是最殷切的等待,然而时光不再,中间隔着人,一眼再也望不见他。我也再无法回到当初爱上他的第一眼,回握他。三年,三年,他的那颗心,我究竟可以分得几何?
如若能够中止这理智与心魔的决斗,我倒宁愿从此独自一人上路,翻山越岭也好,披荆斩棘也罢,仿佛为了他做一些什么,就能减少这种煎熬,就可得到圆满。然而又自惭形秽,我哪里做得来什么,哪怕能做什么,也觉得远远不够。
该软弱的时候坚定,该坚定的时候软弱,于果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自己都不甚明了,师父又可曾了解?我偷眼望他,却被被他恰好发现,满腹鬼胎的人无处可躲,只好低下头琢磨,他这笑意如果不是慈祥,那又是什么。然而这样一种说不清的笑容,便教我之前的所有计较都变得无比可笑。
什么人生在世,什么在劫难逃,这样的矫情话我可不屑说。现在我只晓得,既然他觉得这样好,那便这样好了,我回握住他的手,轻抚他因常年握剑而起的茧子,和那断掌的纹路。长久这么磨折下去,我哪里又是个把持得住的人了。我一个得过且过漫无目的人,又何苦受这等煎熬,若哪天我不再能够安慰到他,再抽出手的时候,也绝无半点犹豫和悔意便是。我本就是一介好色之徒,如今做了顺从自己心意的事情,便认为一切都理所当然,更觉师父的手掌除了那剑茧,别处摸起来竟格外绵软,从前怎么就没发现。
师父被我那么一回握一通乱摸,反而僵持了片刻,无甚动静,我再抬眼望他时,他眼中有些欣喜神色,哎,真不矜持,演技也不行,仿佛我给了颗糖吃。其实他不晓得,他才是糖。
他也不开口,我只好说:大王,走快点成不成,我是真饿。
大王只笑着说好,笑得就像一个小孩子。
终于找到那条有许多小吃的夜市,我家大王不挑食,我吃凉粉,他便也吃凉粉;我来份煎饺,他也蹭着吃。总算到了卖糕人的摊子,我正开口想为他要两块萝卜糕,大王笑着指那豌豆糕:尘西都知道我爱吃什么,就你总以为我爱吃萝卜糕。
尘西竟是对的,师父爱吃的,居然是和我一样的豌豆糕,我真心歉意:大王,我对您实在是太马虎,还总自认为孝顺。
大王纵容地笑:没事。
瞧这情形,明早不用练功了罢,我窃喜。
吃完接着逛,又逛到一个书摊,卖的书里倒有那套《花丛宝鉴》,我以为卖书人又是乐正雨,一瞧却是一老头,我问乐正雨可在万年镇,结果人连乐正雨是谁都不认识。切,还是个卖书的,书的作者都不识得。
一气之下正要走,却被书摊对面算卦的唤住:二位公子可要算算姻缘?
我回头望,那人指着的人是师父:这位口含金汤匙出生的公子,少时却是命运多舛,只恐怕这姻缘也是……
我听得他说得有些理,便停下来,师父拽了拽我,见我不动,便使了些力道,把我拽到老远方才停下,害我胳膊被拽得生疼。我不解:大王,我瞧这人不是没有些本事,您难道就不想知道这姻缘事?
师父闭上眼睛摇头:不想。
我还是不放弃:可他说的……
师父恼怒地打断:能不能别再提这个?
我了然地笑笑,姻缘事,想起他未曾等候到的佳音,他至今还在使的那副银鞍,他终于还是有些角落不能被触碰罢,哪怕刚才的手握得那样紧。没关系,别贪心,不能触碰,绕开便了,我虽不是任何时候都坚强,却有强悍的内心。
关于姻缘事,我也没有把握自己是否真的可以接受,若知道了结果,现在又让我如何抉择。也好,他打断了这次冒险,我便顺着他的心意就好。我伸出去握他的手,他没有动,手的温度变得有些冰凉。
我不知说什么才可以缓和气氛,师父也一直沉默着没有说话,这样被我拉着走,我还以为我们会迷路。结果我们没有,家人在客栈门口迎上来。
我正打算进自己屋,却被他叫住:于果。
进了师父的屋子我有些紧张,我猜想也许有什么事要发生,现如今还有什么可抗拒。他让我坐下来,我便坐下来,他对我说:于果,刚才……你知道,我顶不喜欢那些江湖术士。
哦,是的,那些人夺走了他的童年,也改变了他整个人生轨迹,我也该恨死这样的人才是。我不以为意地摆手:大王,我都明白,刚才都是我的错。
师父终于有点笑意:你从小就爱把所有的错兜揽在自己一个人头上,你可知道,听起来真是不诚恳。
我好气又好笑,他说对了,我认错起来,的确不那么诚恳,做人太难,只好诡辩:我是真的,觉得自己又办了桩蠢事。
我又不好说我是心疼他。他不说话了,只颇有深意地望着我,仿佛就要看出我有什么瞒着他没有说,如果是这样,那么他又猜对了。瞧这情形,我得喝点酒才成,不然一定会被逼疯。我满屋子用眼睛搜寻那只酒葫芦,他见我张望着什么,开口问。我告诉他,想找点酒喝。
他温和嘱咐:今天就别喝了,那么晚了快回去睡吧。明早也得练功,你可别借口晚睡又偷懒。
嘿,明明是个妖蛾子,趴窗子上愣把我自己当了那窗花。太把自己当回事,容易走火入魔。可是,就许大王您一热起来差点烧了我的心,想冷的时候又指望把那团火瞬间就能冻成冰?师父啊师父,您难道真以为我是个好脾气的徒弟,装傻充愣我是擅长,可色胆包天以牙还牙才是我本性啊。您怎么就不琢磨琢磨,被撩拨了我怎能服气,手都摸了我还怕个什么劲,您更不能仗着我心疼你,就这么折磨人。我上前抓着我家大王就往他唇上那一通亲,临了还报复性地狠命嘬了一下,他愣着没反应过来,我已经完事从窗子窜了出去,还轻佻地说了声:不错不错,比我想的还要软,大王,晚安。
事儿是您挑的,轻功也是您教的,明天见面功课严厉我不怪您,您要是嘴肿了可也不能怨我,这回我可不认错。我窜回房,见着那个酒葫芦正在桌上,仰头灌了几口,想着刚才那番滋味,躺床上恶狠狠地想:的确挺软。
32
32、我不管 。。。
变成最有趣默剧艺人不怨怼……《林夕…冷战》
我舔着舌头正纳闷这酒怎么有股腥甜味,余悸难平间想起方才最后那生猛一嘬,嘿嘿,倒是回味无穷,没白弄。我真不容易,平日里陪我练过招时,能触及他的衣角便算我赢,想让我师父见血,从来还是一桩登天难事。
睡了个格外满足的好觉,在他跟前头回反客为主本色出演一回,实在爽毙了。神清气爽地起来,一看日头不早,却没见那打发我练功的身影。我心头咯噔一下,觉着丢人躲起来了?又想着不能够吧,照旧虎个脸端住了不就成了?他以往都是怎么往死里罚我的,轮到自个被我小贪了那么一回便宜,就不能接受了?
一边低头喝着粥,我胡思乱想得正欢畅,跟前竟有人出现了。我磨蹭着抬起头,要说我心里头没点忐忑,那还真不是实话,往河里投石子,有动静我怕闹成大动静,若真没一点动静,我也担心不是。可抬头一瞧眼前尘西,好一个白磨蹭。
我们在这儿,不消说定然是月季告诉的尘西,招呼他坐下:师叔怎么起那么早?
尘西要了碗粥:不早了,日头都晒屁股了这还早,我师兄去了哪儿?
我琢磨着该怎么说,说他被我轻薄,所以躲起来了?还是说他去药店买化瘀消肿的敷药去了?他哪儿那么娇嫩。
却听尘西在唤:师兄。
我没磨蹭,再次抬头,对上的正好是师父的双眼,谁说的出了重手调戏过,就可以从此不殷勤不孝顺。蹬鼻子上脸没的好下场,师父终究是师父,人生还是该当找准自己的定位。哪里是我好对人低声下气,谁教那个滋味忘都忘不掉,哎呀,有打有揉,再亲不难:大王,您没什么不'炫'舒'书'服'网'吧,怎么这会才起身?快些用早饭吧,我和师叔都吃上了。
大王被他唇上那抹殷红色的小块点缀得格外可爱。那伤口比我想象的触目些,我原该后怕才是,可此刻我的心中,却只有一种坏事干尽的淋漓快意。学着他一贯的那种似笑非笑,我一眨不眨地等着他说些什么。
师父过会才说:我睡过了。
我也觉得破天荒,尘西大惊失色:你也会睡过头?难道晕妹说的竟是真的?师兄,快给我说说滋味如何。唉,究竟是我师兄啊,晕妹院里新来的那个孤眠,她可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