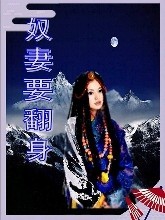鹞子翻身-第4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啊?你不是说闹春荒吗?喏,先给你带二升粳米来,算是应个急,过几天再想办法给你弄。”
其实,唐岭从今天一早就开始盯住梁书记了,见梁书记回乡,便尾随而来。梁书记进了小寡妇的门,他就在门外耐心地等待。
“你来就来了呗,带什么东西嚒!”柴寡妇说着客气话,接过唐岭手里的米袋。
到这时,唐岭装出刚才才发现似的,惊讶地问:“妹子,房间里有人?又是徐雪森来欺负你吧?”
不好!这小子要进来了!如果被堵在房间里,那还不是捉奸成双吗?想抵赖都没门!梁书记用眼四处寻找有没有可以躲藏的地方。可是,除了床底下,别无可藏之处。而且,如果现在钻进去,只怕未等屁股进去,那小子就一头撞进来了!
“不是,是乡里的梁书记!”小寡妇很随意很平淡的声音。
“这该死的死妮子,竟然把我供了出来!”梁书记心头一惊。转而一想,与其被动,不如主动迎上去,便堆着笑容从房间里走出来。“啊,这位是——,是这样的,我刚好路过门口,这位女同志说有冤屈要向我倾诉,这也是关心群众么,举手之劳,也是顺道,就进来听她讲讲,她还没说几句,你就来了。”
梁书记一副处惊不慌的沉着模样。
“啊,是梁书记啊,妨碍你工作了,吾来得不是时候!”唐岭佯装猥琐,弯下腰陪不是,又转身对小寡妇说:“又有什么冤屈了?敢惊动梁书记?”
柴寡妇系好最后一粒纽扣。“还不是做鹞子嚼百蛆的徐雪森!梁书记,您可要为我作主哇!”
“对对,为你作主!”这时的梁书记只能顺着小寡妇,生怕她说漏了嘴把刚才二人发生的事捅了出来。
“梁书记,说到徐雪森,吾可有重大事情要向您汇报。”唐岭觉着水到渠成,可以单刀直入了。
“你说你说!你是——?”梁书记巴不得转移话题,爽快地答应。可是,他压根儿就不认识唐岭。
“吾是西桥合作社的副社长唐岭。”唐岭只得自我介绍。
“噢,唐岭,对对对!西桥合作社的,知道的,不错,是我同意的。本来在你们上任之前想找你们见次面、谈次话、做些交代的,可我忙啊,到县里去开了几天的会,忘了。有什么事到我办公室去谈,走、走吧!“梁书记想着马上离开这个让他可能出丑的地方。
“不不!梁书记,就几句话。”唐岭伸手把他栏住。“妹子,给梁书记泡杯茶来嚒!”
唐岭明白,向书记汇报工作上的事,不能让无关的人在场,否则显现出自己不慎重,因此,故意支开小寡妇。
梁书记一听,觉得刚才的一幕过去了,刚来的唐岭根本没有觉察出什么,就摆摆手,说:“好吧,我听,你讲!”
唐岭就把徐雪森是如何包庇宋树根卖牛的,如何放跑卖地的事,添枝加叶地描绘了一遍,完了说:“梁书记,像徐雪森这种‘三开党’,只认钞票不讲原则的人怎么能当干部呢?而且,还是常务副社长!”
梁书记沉思了一会,像做会议决议似的一字一句说:“唐副社长同志,你反映的问题很重要!说明你有组织纪律观念,我要当面表扬你!关于你反映的徐雪森的问题,的确是个原则问题,你看问题很尖锐,很有政策水平。这样,你马上回去向小刘传达我的指示,立即让徐雪森停职检查,写出一份深刻的检查交给我。”
“梁书记,不是吾不愿意传达您的指示,吾是担心刘站长不会相信吾讲的话,弄得不好还会影响团结,所以还是您亲自对刘站长指示好。”对梁书记的这个决定唐岭很不满意:搞了半天,只是让徐雪森写份检查,并没有把他拉下马,因此,心里很不痛快。
梁书记挥挥手:“你这个同志胆子太小,怕什么?由我这个书记给你撑腰!今后不管遇到什么问题,你可以直接来找我汇报。这样吧,你马上去告诉小刘,让他去我办公室找我,我当面给他说。去吧!这位女同志的话还没有讲完,我听一听就来。”
唐岭听了心里觉得好笑,明白梁书记的好事没干成,要把他赶走。虽然没有一棍子把徐雪森打倒,但只要你梁书记与小寡妇发生了关系,只要你有这个嗜好,就不愁栓不住你,把你捏在手心里那是早晚的事,于是,唐岭很爽快地说:“行,梁书记,这事说急不急,您慢慢听,吾回家吃过晚饭就去通知刘站长。”
唐岭马上离开,顺手带上门。
唐岭一走,梁书记一把把小寡妇抱起,扔到床上,迫不及待地做事。
唐岭并没有马上离开柴寡妇家,而是躲在窗户下偷听,脸上露出狞笑。
'本书首发来自17k,第一时间看正版内容!'
;。。。 ; ;
第五十一章
西邨睁开眼,发觉自己躺在陌生的地方。
屋顶不是他家一眼就能看到房梁和椽子的房子,而是平整的用杂七杂八的纸糊的天花板;床也不是他家的木架子床,而是用石块与泥巴垒筑的平台(北方人叫炕);平台中间还拉着布帘子做隔断,隔断的另一边是堆着锅碗瓢盆的灶台;身上盖着薄薄的气味浓烈露出棉花絮的被褥,却感觉暖烘烘的;墙壁上有个不大的用“高丽纸”糊着的窗户,透着些许光亮。房间里静悄悄。静得让人可怕。
诶?这是什么地方?在梦里吗?怎么会做这样的梦?见鬼了!
“有人吗?”西邨喊了一句,却感觉自己浑身的骨头像散了架似的,酥软、酸痛、乏力,头也昏沉沉的。
没人应答。
他猛然间想起来了——阴沉的天空飘起了毛毛细雨,被寒冷的北风刮来,像一粒粒沙子打在脸上,疼得让他把头缩进衣领,两手伸进衣袖,佝偻着背跑下山去。
一阵眩晕,饥肠辘辘。他这才想起从昨天天黑到现在还没吃东西没喝水呢。嘴巴里苦涩得要命,干得连舌头都赖得伸,嘴唇干裂毛糙,像锉刀一样。
他放下包袱,打开,秦人方秦伯伯的尸骨立马暴露无遗,像无数根钢针戳进他的胸膛。他颤抖着拿出一块烧饼,咬了一口,却怎么也咽不下去。喉咙口像有道门堵住了,既疼又硬。是口渴,得喝点水。可哪来的水?到哪里去找水?
他强撑着站起来朝四处张望,希望看到河沟或者水渠一类有水的地方。
在西村,到处都能看见水,不出一二里地就能见到房子看到炊烟就有人家。这鬼地方一眼望去,几十里地不是山就是灰黄的土岗,连个房子的影子都看不到。
面前不远处有丛绿绿的灌木被风刮得剧烈地抖动,叶子上闪过光亮——毛毛细雨打上去又被刮走了。不管怎么说,叶子是湿润的。
西邨扑过去,采撷叶子,用舌头舔。干涸的口腔喷出**。他干脆把叶子放进嘴里,咀嚼起来。舒服多了,头脑清醒起来,有了吃烧饼的**。
不能在这里久留,说不定野狼白天也会来的,可以把叶子采下来边吃边走吧。西邨把灌木上的叶子几乎全都采下,装进口袋,将着烧饼,一边采一边咀嚼。
呯!口袋快要满的时候,远处,辨不清来自哪个方向,响起了枪声。西邨心想,一定是猎人在打猎,终于有人了,可以喝到水了,自己可以获救了!枪声于耳未绝,正要举头张望,灌木丛“沙啦啦”一阵声响,自己的大腿部一阵钻心的疼。“不好,是朝自己打来的!猎人把自己当野兽了!”
“是吾!不要打!”西邨声嘶力竭地喊,同时立即趴下。
呯!猎人在西邨发出呼喊后不久又打出一枪。
沙啦啦!猎人的霰弹枪的部分子弹打中了灌木,一部分子弹从灌木丛外围飞过。
猎人第一枪的霰弹子弹被密集的灌木丛遮挡住,只有一颗子弹击中西邨大腿。猎人之所以马上打出第二枪,是估计目标在听见第一枪后会跑离灌木丛,因此,瞄准了灌木丛外。
这是经验丰富的高明猎手。可他瞄准的目标不是野兽而是人,而且是西邨。习过武的西邨没有跑,条件反射地立即趴下。如果马上跑,只要一露头,百发百中的猎人打出的第二枪的密集的霰弹子弹一定把西邨的脑袋打成蚂蜂窝。正是趴下不动这个动作,西邨又救了自己的命。
猎人终于听到了人的呼喊声,惊呆了,放下枪,站了起来。“是谁?你是什么人?”
显然,猎人没想到目标是个人,而且没想到居然有人从人迹罕至荒芜人烟的山区翻山过来。
“大叔,是吾!”西邨的声音在荒野的山区显得那么微弱,连他自己都觉得那是多么的苍白无力。
猎人赶了过来,可是,西邨失去了知觉。
西邨怎么也没想到,他从灌木上采撷的叶子是有毒的。到这会儿,到猎人赶过来时,叶子的毒素已经起作用。经受惊吓、恐惧与饥饿袭击的幼小躯体,再也经不起毒素的侵扰。如果不是猎人的到来,即使不被猎人的霰弹枪打死,他只能永远趴在这座山包的山腰上。唯有脱窍的灵魂去追赶升天不久的秦伯,二人留在人间的也唯有累累白骨。
机警的猎人上下检查,除了大腿一处外,身上、头上没有中弹的痕迹,又用手指撑开西邨紧闭的眼,西邨毫无反应;掰开西邨的嘴,嘴里的叶子还没咽下。他立即明白是中毒了。他俯身听西邨的心跳,按住手腕的脉搏,心脏还在跳动,这说明中毒时间不长,还有救。
猎人马上背起西邨,飞奔下山,连忙熬煮草药。
在山里,许多人都有过中毒的经历,譬如因为饥饿,会误食有毒的蘑菇、野菜、野果。因此,山里人也多少懂些如何自救的常识。不仅祖上流传下来一些秘方,自己也累积了一些经验。猎人懂的常识无疑更多些。
解毒的草药熬就,猎人灌进西邨的嘴里。既然中了毒,解毒是需要时间的。
在等待中,猎人褪下西邨的裤子,发觉霰弹枪的子弹打得并不深,没有伤到骨头。他用土烧酒喷在伤口,把镊子在炭盆里烧红,小心地却很迅速地夹出子弹,再在伤口敷上伤药,用土布包扎好。
在做这一切的时候,西邨没有任何反应。这孩子,中毒太深了!这叶子太毒了!如同服了麻醉药。会不会伤了大脑啊?如果麻痹了大脑,这孩子就费了,一生就完了!
但是,猎人所能做的就这些了。把他从鬼门关拖回来,能喘着气回到人间就已经是万幸了。至于活过来以后如何活下去,猎人是无能为力的。
朗朗乾坤,天地可鉴。好在不是自己的子弹打伤造成的,他于心无愧。
到这时,猎人才有闲暇注意到西邨的包袱。看着鼓鼓囊囊且沉甸甸的包袱,猎人很好奇:这么点小的孩子,背这么大个包袱,而且是从山那边的荒野里翻山过来的,他是什么人?去荒野里干什么?背的又是什么?
猎人忍不住打开包袱。这一打不要紧,猎人被包袱里的一堆白骨吓懵了,惊得张开的嘴巴好半天合不拢!
是人的骨头!而且是高大的成年人的骨头!被咬得只剩下半只手掌就是例证。这白骨肯定不是从泥土里挖出来的或者是搁久的,上面还有血迹,还有肉!他凑上去一闻,还有一股呛人的血腥味!这人是被野兽吃了?那这孩子是怎么逃离了虎口活了下来?
离奇!出奇的怪事!
包袱里还有烧饼、牛角刀、小耙子、手电筒,还有他不认识的从未见过不知是派什么用场的罗盘。看样子这孩子是有备而来的。
那么,这孩子是干什么的?是来探险的?年纪也太小了点吧?
猎人想从孩子的身上找出答案。于是,他便在与死人毫无二致的西邨身上翻找。
啊!棉袄里面的口袋里有一沓子钱!小夹袄里还有二爿牛皮不是牛皮纸不像纸的圆盘子,上面还有符号。是什么玩意儿?莫非面前的人是特务?这特务也太小了吧!
奇怪!一连串的问号在猎人脑子里打转。
必须把这孩子救活!等孩子醒过来,才能从他嘴里得到答案。
俯伏在孩子的胸口,听听孩子的心跳,再摸摸孩子的脉搏,猎人深信孩子已经脱离了危险,但完全苏醒还需要时间。
猎人把西邨抱到炕上,盖上被褥,把火炕烧得热烘烘的,关上房门,背上猎枪,再次上山。
如此的情景过去了三天。猎人每天出门前都给西邨灌药、灌小米粥汤。做完这些,猎人与往常一样上山打猎,然后把打到的猎物上集市出售,换回粮食和日用品。
第四天,猎人在集市卖掉山味野货,打上两斤白酒,把预留的半只狍子送往他的老主顾也是多年的老朋友音吉图家。
'本书首发来自17k,第一时间看正版内容!'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