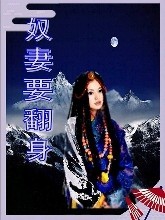鹞子翻身-第1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徐雪森。”徐雪森回答道。
“噢,徐雪森。”余股长搬过一张椅子,坐下。“你觉得冤枉了是吧?不要有怨气!这最近一段时间,全县上上下下在搞肃反运动,清查隐藏的历史反革命。下面的人就检举揭发,报上来送过来一批又一批,我见得多了。检举的人有各种各样,动机各不相同。许多都是莫须有,抓错了。抓错了有什么办法?错了就放了。这样,你填张表格,我马上放你走。”
“行!吾识字不多,写不了几个字。”徐雪森两手一摊。
“姓名年纪总会写吧?其余的,我帮你写。在表格下面签上你的名,就行。”余股长倒很爽快。
“那就谢谢你了!”徐雪森心里一阵轻松。“哎,同志,吾多句嘴,老梁也是冤枉的吧?”
“老梁?哪个老梁?”余股长随口问。
“就是窑山的,好像是合作社的社长吧?”徐雪森心想,如果老梁没问题,他就彻底没问题了。
“噢,昨天我审过了,过两天,报县委肃反办批一下,就放了。”余股长回答他说。
填完表格,余股长真的让徐雪森走了。徐雪森立即赶回窑山,到老马家门口去推他的独轮架子车。老马家的大门关得严严实实。他真想破门冲进去狠狠地揍老马一顿,可是,想想犯不着,他还要买竹子赶回家做鹞子呢。家里人一定等急了。因此,他把满腔的怒火压在心里,去老梁家报了个信。老梁老婆听说老梁过两天就能放回来了,很激动也很高兴,热情地招待徐雪森,又张罗着替他找到一家竹子质量和价钱都很好的人家,还肯欠账,临了,又挽留徐雪森住下来,说,等老梁回到家,哥俩个好好地喝上一夜,驱驱晦气。无奈徐雪森坚辞不肯,连夜离开了。
徐雪森没想到,赶到家,收留他爹的清兵孤寡老汉去世了,他连最后一面都没见着。
“他爹,都过去了,忘了吧!”西邨母亲安慰父亲。“你弄得过那些扛过枪的?都是黑了心没肺的东西!”
“一口恶气咽不下去!”父亲握紧拳头,想砸,却停住了。“忘恩负义的王八蛋!”
“老话说的,大难不死,肯定有后福,说不定这是转机都难说。”说是这样说,其实,母亲是宽慰父亲的。
“爹,等吾长大了,吾替爹去出这口气!”西邨咬紧牙根。
“孩子,大人的事不用掺合,少给娘惹祸!”母亲推了西邨一把。
'本书首发来自17k,第一时间看正版内容!'
;。。。 ; ;
第十八章
无论有多大的怨气,日子还得过下去。对徐雪森来说,要过日子,要还清债务,除了夜以继日做鹞子卖鹞子,别无他法。看来,原本以为住在这块风水宝地立马翻身、飞黄腾达的梦想,不靠劳动是不可能的。
他摆好工具、架好桌凳,锯竹、劈竹、削蔑,裁纸、拉线、调浆糊。门前、屋里恢复了宁静,死一般的安静。
西邨知道,父亲做鹞子的时候专心致志,是不能打扰的,便坐在一旁做他的弹弓。他把买给妹妹跳橡皮筋绳的牛皮筋拆下来,做了个结结实实、弹力很强的弹弓。恰巧,门前枯树上飞来二只麻雀,站在枝丫上摇头摆尾,他捡起一颗小石子,拉开弹弓,“噗!”一只麻雀应声落下。他目测了一下距离,大约二十步远。“离百步穿杨还差得远呢!”
西邨干脆到屋后的荒地上练习。他用父亲做鹞子的线吊起一截竹筒,挂在树上,然后,退后二十步、三十步、五十步、八十步……,一一试射。二十步时,五发四中,打中桌筒后发出的声音清脆响亮;四十步的时候五发三中,声响弱了许多;五十步的时候,五发一中,几乎听不到声音。也许是距离远了听不到?不,是弹弓的弹力不够!正所谓“强弩之末,矢不能穿鲁缟”。要加大弹弓的弹力。妹妹跳绳的牛皮筋不行,弹力不够。用什么替代呢?
他苦思冥想。想起来了,西桥街上瘸子皮匠补雨鞋用的橡胶皮很结实,弹力一定好。他趁着父亲忙于做鹞子无心管他的空隙,拿上一只鹞子去街上找瘸子换。瘸子问清用途,二话不说,送他一大块橡胶皮。西邨喜滋滋地回家做了一个新弹弓,一试,力道果然比橡皮筋的好,不但打得远,命中率也高,打上五十步之外的竹筒发出“当当”的声响。就是它了!
西邨拿着弹弓,找更小的目标练习,找“活”的目标练习。他下决心练出“百步穿杨”的本事,练就“百发百中”的功夫。弹弓好啊,它便于随身携带,而且不碍事、不起眼,遇上有野狗疯狗的、坏人欺负的,也可防身呐。
“西邨,西邨——!”是母亲的喊声。“你到哪儿贪玩啦!”
“娘,吾在这儿呢,啥事?”西邨仍然沉浸在他的喜悦之中。
“你爹问你呢,你把‘诗盘子’放哪儿啦?”母亲问。
西邨把弹弓掖在裤腰里,急急地跑回家。“不是放在房间桌子的抽屉里吗?”
“回来,找给你爹!”母亲说完,忙她的事了。
西邨走进房间,拉开抽屉,抽屉里乱七八糟。“咦?明明白白放在这里面的,怎么不见了?”他怀疑是自己记错了,又拉开另一个抽屉,全是破布、线头、断鞋样,没有“诗盘子”的影子。难道是弟弟妹妹们拿去玩了?不会的,他们从不玩这个。他挠挠后脑勺,没了辙。“会不会——?”
他想起大年初二那天,怀疑是太爷爷入殓那天出的事。那天家里人来人往,随便什么人都可以直进直出,丝丽姐就是从房间里抱着瓮头出来的。难道是丝丽姐顺手牵羊偷走了?会的!很可能会的!她见吾家的鹞子上写着诗词容易卖,还能卖出好价钱,一定眼红!她不是要向吾借“诗盘子”回去抄吗?吾没答应,她就趁乱来偷了。这个可恶杀千刀的势利婆!吾家死了人,她居然趁火打劫。她什么坏事没做过?什么东西没偷过?肯定是她偷走了!这个女贼骨头!
可是,俗话说,捉奸要成双,抓贼要有赃。证据呢?谁看见了?有谁能站出来作证?那天乱哄哄的,来的人太多了,老的少的,男的女的,都有;做鹞子的,眼红他家鹞子的,在西村不止丝丽一家,凭什么就单单怀疑是丝丽?可是,能明火执仗到家里来偷的,除了丝丽,西村好像没有那么大胆子的人了。
“你在磨蹭啥呢,让你找的‘诗盘子’哪?”父亲徐雪森在前屋喊道。
“爹爹,‘诗盘子’找不见了!”西邨愣愣地走过去。
“就这么巴掌大的地方,能放到哪里去?不会是放在你的书包里了吧?去找找看。”父亲说。
“没有,爹,吾从不放书包里的!”西邨傻傻地站在父亲身旁。“爹爹,吾怀疑是太爷爷入殓的年初二,被丝丽浑水摸鱼偷走了!”
“啊?被偷掉了?”徐雪森抬头看了一眼西邨,表情有些吃惊,但不愤怒。
“肯定被偷掉了,吾把抽屉都翻了几遍了。”父亲没有责骂他,他紧张的心情稍微松弛了一些。“爹,吾去找丝丽要回来!”
“天真!你个毛头小子!你凭什么说是她偷的?你去要她就给你了?就算是她偷的,她会老老实实还给你?那不等于她承认是贼骨头了!”徐雪森仿佛并不着急。“算了,家里少的东西何止这个‘诗盘子’?米啊,面啊,钱啊,都光了,好像来了一帮强盗,洗劫一空。嗨,没把床呀、坛坛罐罐的都搬走就是手下留情了!”
“就这样便宜她了?”西邨依然很气愤。
“不便宜她又能怎么样?你奈何她不得!你还能到她家里去抄家不成?”徐雪森何尝不恨,内心真不知是啥滋味。
“爹爹,有办法的!”西邨突然想到,丝丽偷他家的“诗盘子”无非是学着把“诗盘子”上的诗抄下来写到鹞子上去,只要她在抄、她在写,他就有机会发现。“爹,吾可以躲在她们家门口看,丝丽抄呀写的时候,吾就冲进去,不就抓到把柄了吗?就不怕她赖得了!”
“做贼的没那么笨,孩子。”徐雪森很平静地说。“她会让你站在她家门口?被她发现了还不打起来?她比你高出一大头,你打得过她?别去吃眼前亏了。好在那个‘诗盘子’上的句子你都能背下来了,用处也不大了,去,你现在就凭记性写下来,晚上要用的,去写吧。”
“噢。哎,爹,吾想起来了,”西邨突然想起在小凤家的事,蹲到父亲的旁边。“爹爹,小凤父亲也有一个跟吾家‘诗盘子’一样大小、一样颜色和材料的圆盘子,但那上面没有孔,也没有字——”
“什么小凤?哪家的小凤?”徐雪森奇怪地瞪了西邨一眼。
“是,是东青西面一点的孤村,叫什么‘太平府’的孤村独户,周围全是坟地。对了,她家姓秦,她父亲叫秦人方,他说认识爹的。”西邨一股脑儿解释说。
“噢,秦铁匠。”徐雪森疑惑地看着儿子:“你怎么认识他的?你去他家了?”
西邨把那天的事说给父亲听。“听秦伯伯说话的意思,他家的那个圆盘子与吾家的‘诗盘子’好像是一对,他很感兴趣。对了,爹,秦伯说过了正月十五他要来见你呢!”
“秦铁匠要来西村,要见吾?什么事说了吗?”徐雪森似乎不相信西邨说的话。
“是的,爹,他说得明明白白,是说过了元宵节就来,还说是有大事相商。至于是啥事么,肯定是来看‘诗盘子’的。”西邨说。
“大事相商?看‘诗盘子’那叫商量大事呀?秦铁匠不打铁要学着做诗了?诗能当饭吃还是能当下酒菜?你听错了吧孩子?”父亲徐雪森仍不相信儿子说的话。
“真的,爹,这是秦伯的原话,吾没说错!他是说来见你,商量大事的。”西邨觉得受了委屈,争辩道。
“好吧,等他来了就知道了。”徐雪森埋头做他的鹞子,不睬儿子了。
西邨悻悻地离开父亲,从书包里拿出纸笔,凭借记性默写“诗盘子”上的诗句。
背着,写着,西邨越想越火冒。“天杀的势利婆!贼心不改的丝丽姐!偷汉子,害了子良哥哥!偷互助组的粮食不算,还偷到东青去,死不要脸,现在又来偷吾家的‘诗盘子’!不能轻饶她!对,要把‘诗盘子’要回来!否则,小凤爹来看‘诗盘子’拿什么给他看?还会以为吾爹不肯拿出来呢!去要回来。”
想着,西邨满腔的怒火在心中喷发,再也坐不住了,拔腿跑去丝丽家。
“丝丽,你出来!”西邨跑到丝丽家门口,手叉腰,怒目圆睁。
屋里没有回答。
越没有回答,西邨越加冒火:“贼骨头丝丽,好汉做事好汉当!别做缩头乌龟,有种你出来!”
“是谁敢到吾家来破口大骂呀,啊!”丝丽的父亲宋树根从后房走出来,手里提着菜刀,厉声责问道。
“吾找你家丝丽讲话!”西邨理直气壮地说。
“‘丝丽’、‘丝丽’!‘丝丽’也是你叫的吗?不懂规矩的野种!”宋树根气势汹汹,面目可恨。
“吾不叫她丝丽叫丝瓜啊?”西邨冷笑着说。
“她的名字也是你叫的吗?叫阿姨!你没有那个辈份!”宋树根朝西邨狠狠地瞪上一眼,转身就要走。
“不叫丝丽就喊她势利婆!”西邨气鼓鼓地不服气。“你把她叫出来,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
“滚远点,你个野种!敢到吾家门前来撒野,小心剁了你的舌头!”宋树根挥挥手里的菜刀。
“你才是野种!野蛮坯子!你来呀,来剁呀,你敢!你要是动一动,小心夜里吾来放一把火,把你的狗窝烧个火光冲天!你来,你试试?”西邨对宋树根历来没有好感,心里憋着一肚子气,听他如此威胁,突然冒出这么一句来对付,还向前走了几步。
宋树根听他这么一说,心头不禁一惊。俗话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讨饭的不怕发财的。如果把这个犟头穷光蛋惹恼了,他真的在夜里来放把火,几十年心血堆砌起来的四间大瓦房毁于一旦,找谁去?他家只有二间破茅屋,又是外乡人,搞不好卷起铺盖远走他乡都有可能,反正他们就是这样来的,流浪惯了,吾宋家可是祖祖辈辈、世世代代在西村安身立命的人家。“吵架的怕拼命的”。千万不能激怒了他。
“西邨,你个小赤佬,你知道不知道,自古以来放火都是犯法的,弄不好是要杀头的?”宋树根威胁道。
“是你家丝丽先犯法,哼,要杀先杀你家丝丽的头!”西邨毫不退让。
“给你说,孩子,你爷爷与吾平辈,你该喊丝丽阿姨,懂不懂?”宋树根的话虽不客气,但语气却平和了不少。
“阿姨?呸!她不配!她到处做贼偷东西,还有脸当阿姨?连婆家都找不到的贼婆子,还要让吾喊她阿姨,呸,做梦!”西邨愤怒地啐了一口吐沫。
“你个小赤佬别往吾家扣屎盆!她啥时候偷你家东西了?啊?你血口喷人是要遭天打雷劈的!”宋树根被缠住了,想脱身却走不了。
“她偷得还少啊?整个西村谁不知道?你装聋作哑就瞒得了吗?吾们老师说的,这叫‘掩耳盗铃’,你懂不懂?把吾家的‘诗盘子’还给吾,这件事就算拉倒。否则,哼,别想赖!”西邨依然不罢休。
“什么‘屎盆子’?你嘴里放干净点!”宋树根不想跟一个孩子一般见识,却被不依不饶的西邨步步紧逼,反而走到门口,厉声问道。
“吾家的‘诗盘子’!吾太爷爷入殓的那天,吾亲眼看见丝丽从吾家房间里出来的,肯定是她顺手牵羊偷走了,还要赖!”西邨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