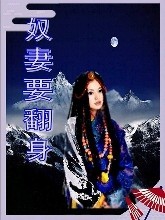鹞子翻身-第1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儿子有了正经的名字不能当饭吃啊!吃的、穿的、用的、住的,全靠十个手指头去掱、去抓、去做!西邨爷爷说过:就算是大河里漂来一大捆绑钞票,如果去晚了,也被别人捞走了!什么都要起早,什么都要勤快!勤劳才能致富。何况是荒地啊,你不种,只会长草。
西邨的父亲和母亲除了要把儿女们拉扯大以外,最重要的心愿是将茅草屋翻盖成砖瓦房,好让西邨和他的弟弟不再像他们在窝棚里成亲那样,能在砖瓦房里娶妻完婚,生儿育女,重兴徐家的风光,重续徐家的血脉,光宗耀祖。
“衣是人的装,房是家的脸。没有房子还叫家?什么鸟都知道为了繁衍后代要衔枝寻草在树叉上筑个窝呢!没窝没家那不成了叫花子、流浪汉了?人活一世还有何脸面?树靠一层皮,人活一张脸。没有像样的房子,儿子能讨上老婆?谁家的女子肯嫁给叫花子、流浪汉?天底下像吾这样不图你房子、愿意在窝棚里成亲的女人有几个?”西邨的娘总是在丈夫耳边唠叨,述说着自己的心愿。
“吾知道,心里明白着呢!可是,也得慢慢来不是?”西邨父亲总这样回答妻子。
“孩子一天比一天大,现在是两个光郎头,两个小辫子,四个孩子挤在一张铺上,大了怎么办?大的脚都伸到小的鼻子呀嘴巴上了!”西邨娘说到眼前的光景,总流露出不安与哀愁。
“吾怎么不懂?明白着呢!可是,有啥好办法?这年月一只鹞子只能赚二分多钱,要赚三分、四分,就很难卖。家家都很穷,买鹞子的人是越来越少了。你再想想,造一间砖瓦房要多少块砖、多少片瓦?告诉你,吾上窑场问过了,一块砖要二分八厘,一片瓦也要九厘,便宜一厘都不肯!你算算,造一间房吾要做多少只鹞子?”西邨爹开口就是算账。对于妻子的操心,他没有别的话可说。
“一间房怎么够?怎么住?自从吾嫁给你,吾娘家来过人没有?为什么?你就没有想过?吾爹来了,你还强留他住下来过夜,你让他睡在哪?你以为吾爹就那么傻?他看不出来你是嘴上的礼貌?就这么巴掌大的地儿,一人放个屁,全家人要臭大半天!他不知道你是嘴上客气客气的?所以,要造起码就得造四间!”女人的算盘历来是最具体最实际的。
西邨父亲闷着头,不敢回嘴。
“他爹,吾翻来覆去地想过了,吾们有二个儿子,二个女儿。女儿是帮别人家养的,早晚是要嫁出去的,不会留在家里占地方。二个儿子一人一间就得二间,吾们老两口还不得一间?这样就要三间。总要留间客房吧?还有,粮食放在哪儿?柴草堆在哪里?灶间按在哪?吃饭的桌子放在哪?西邨喂的羊总要给它砌个羊圈吧?这样算下来,起码要造四间大屋,再造一个厨房、一个猪圈和羊圈。”
听她的话,西邨爹知道妻子是早有盘算。女人嚒,她们的想法都是很现实的,对家的概念比较具体,对生活方面的考虑要比男人精明得多。
“西邨娘,你没有看到土改那年东村桥庄的黄老郎中家的房子被分掉了?就是他的房子太多,太高,又是楼房,才被分掉的,到头来自己住到他以前的牛棚里。再说了,那些打劫的强盗找谁?专找房子高、房子大的人家!在他的脑子里,高房子、大房子一定是有钱人,他才不管你高房子里面住的是什么人呢,先破了门再说!你安稳吗?所以呀,房子是要有的,但不能砌得太高,更不能太多。否则,树大招风,有人会眼红的。”
也难怪西邨娘有那么些想法,都是受了丈夫的影响。早先几年,西邨的爹就在妻子面前许诺,一定遵照他父亲的遗愿,不但把茅草房翻盖成砖瓦房,而且肯定要造高出西村所有人家的房子。他的目标是瞄准了东村桥庄黄甲祺黄老郎中用糯米浆掺石灰再加纸筋砌的红门百叶窗的高楼,数量上他是有自知之明的,他比不上黄老郎中,造四到五间就够了。
他也算过一本账,只要他坚持不懈地开荒种地,把屋后三十多亩的荒地全开垦出来,种满了北瓜、山芋、荞麦、黄豆、绿豆、赤豆、芝麻,对,再多种些芝麻!老辈的人都说:“若要发,种芝麻”。芝麻收益高,卖得出价钱。这样,一家老小的吃、穿、用就不用愁了。与此同时,再坚持不懈地做鹞子、扎花灯,用不了多少年,攒够了钱就能造房子了。
可是,土改那年,他目睹黄老郎中的房子全部被分了个精光,自己落得住进牛棚的下场,他的心冷了。他想,朝代变了,孙大炮孙文首创的“平均地权”政策到了**手里变成了“均田地、均贫富”的口号,变得更彻底更现实,谁都别想多占土地、多造房子。即便你节衣缩食、挖空心思花上几代人的心血造起了高楼,到头来还是一场空,回到贫穷的原点。何苦呢?还是古人说的好:房子不在多够住就好(其实,他把古人的话记错了,他也没那个文化理解原话。原话是:“室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
不知不觉中,西邨父亲违背了他父亲的遗嘱,也把自己造房子的计划悄悄修改了,变成现在对妻子说的那一番话。
如果非要问他真的就是怕房子造高了、造大了会与黄老郎中一样被人分掉?也不是的。他也想住宽大高敞的楼房。平心而论,他觉得要实现计划,实现他父亲的遗愿,谈何容易!
“你这是给自己的无能找理由!要造就造砖瓦房。你看吾们现在住的茅草房,四面透分,那扇大门连手指头都能伸得进。又矮,你们男人进门都得弯腰低头;又闷,总觉得上面的屋顶要压下来一样,让人透不过气来!宋树根走过去的时候那种眼神就是瞧不起的样子,就是笑话吾们无能,吾看了像是有把刀子插到了吾的胸口。砖瓦房就不同了,不透风,地上干净,高大敞亮,透气,透光,别说自己住着舒心,就是村里的人,像树根这种势利眼的人,还敢小看你?人活得要体面,就要争口气。吃的上面能省,吃大米也是度日,吃北瓜也饿不死,省下钱多买几块砖,把房子砌高一点;穿的上面也要省,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大的改了给小的,小的穿破了改尿布、纳鞋底,这钱不是又省了?你再辛苦几年,多做些鹞子,让西邨帮你出去卖,砖瓦房不就早日造起来了?”
“娘子真是好计算!吾不是不要房子,只是说不要造得像黄老郎中家那么高。好,就听你的。跟你说,要造就用糯米浆掺石灰加纸筋砌的砖瓦房,那墙壁可就结实喽,千年万代都不会倒塌的!”西邨父亲不想扫妻子的兴,更不想伤害她,说着鼓励的话。
“先不要做这样的梦!用糯米砌墙?一年到头你见过几粒糯米?在外面嚼百蛆,嚼死尸,在吾面前也来吹!没个正经!”
“嚼百蛆”,有人写作“嚼百趣”或者是“嚼白蛆”,是西村一带的方言,意为带有诙谐性海阔天空地调侃和吹牛皮,含褒贬二义。
西邨娘用手指戳了丈夫一下,继续说:“你先把茅草房盖起来,攒够了钱再翻盖成砖瓦房,你给孩子们造了四间砖瓦房就算你功德无量了!现在要紧的是攒钱、买砖瓦。屋基是不成问题,茅屋后面的荒地任吾们选。”
从此,二人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做了许许多多的鹞子;鹞子卖了,马上去买回砖,堆在茅草房西山墙下,都有半人多高的一堆了。可是,有一年的春天,西邨爹向西村的一户唐姓借了条牛回来开荒耕地,到第六天的早晨起来一看,栓在屋后的牛不见了。
“都是吾不好,睡得太死!后半夜吾是听到牛叫声的,被你折腾了半个时辰,身子软绵绵的怕动,腰就是挺不起来,还以为是哪家的野猫跑过来吓着它才叫的。要知道是有人来偷牛,吾是无论如何爬也要爬出去跟他拼命的!”西邨娘有点责备丈夫又有点懊悔。
“唠叨有啥用?要是有用,你就打吾一顿!”西邨父亲抱着头闷坐在矮凳上。
为了赔牛,西邨爹只得把已经买回来的几千块砖再低价卖出去。但是,在那时,一条牛抵得上二间砖瓦房,堆在西山墙根的砖还不够造半间房子的,还债远远不够。牛债还没有还清,当年的夏天,一阵龙卷风刮来,把盖起来没几年的茅草房的屋顶卷走了,干打垒的墙壁也倒塌了。真是祸不单行!西邨一家是雪上加霜,几乎就要绝望。
总不能住在露天吧?流浪乞讨?一大家子呀!没办法,只能举债先把茅草房重新盖起来,砖瓦房的期望只好无限期地往后推了。
西邨父亲与母亲比以前起得更早,睡得更晚。白天开荒种地,不到天黑看不见自己的五指不收工,草草吃过北瓜或者是山芋、山芋加荞麦面的晚饭,马上点上油盏灯(一种在碗底样的铁盆里注进豆油,放上一根灯草的灯),二人在火苗只有黄豆大小的灯下削竹、劈篾、搓麻线、裁纸、打样、调浆糊——做鹞子。
后来,西邨长大了,长到了七八岁的光景,看着没日没夜的爹娘,总想替把手,帮点忙,以便爹娘能早几分钟上床睡觉,就帮着爹娘打下手。再后来,他试着外出卖鹞子。起初是在西桥的街市上,后来就跑出三里地、五里地,到现在,他走三十里都不觉得远了。卖鹞子的路是越走越远,吃过的苦是不计其数,遇见的人是各式各样。
可是,今天,西邨的鹞子被一帮无赖小强盗在光天化日之下抢走,被李公安莫名其妙地没收,这口气他怎能咽得下去?那是他父亲的血汗啊!是父亲用肩、用手,走了无数里路、熬了无数个黄昏与夜晚,用心血做成的啊!多少块砖没了!
父亲给他算过账:卖出一只鹞子,刨去竹子、纸张、麻线、浆糊等等原材料本钱,不算功夫(农民种地所花费的力气和时间是从不计算成本的),只赚二分多钱。这是父亲的智慧、力气、熬夜的血汗换来的。而这二分多钱还买不到一块砖。一块砖要二分八厘,一只鹞子平均赚二分四到二分六厘,顶多只能买到大半快砖。娘说要盖四间砖瓦房,爹计算了一下,需要三万八千块砖。按鹞子的平均利润计算,这需要做出和卖出四万三千多只鹞子,需要花费三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坚持不懈地做下去才能攒够这笔钱。可是,今天,几十只鹞子就这样没了,不但没赚到一分钱,连父亲的本钱都被抢了,被没收了,等于是马上到手的几十块砖被人眼巴巴地从手里夺走了!造房的时间也往后推迟了。西邨怎能不忿恨?怎能不伤心?
西邨茫然地走着,心如刀割。
路边有个小池塘,在阳光的照射下,水面的冰已经化了。一群绍鸭唧唧嘎嘎、摇摇摆摆地跳进池塘里,拍打着翅膀,伸长了脖子,追逐着、嬉闹着,享受着快乐。
西邨想起了“诗盘子”上有句诗:“春江水暖鸭先知”。是啊,经历了一个寒冬,老鸭是最早也是最能体味春天池水冷暖的,它们已经预感到春天就要来了。可是,西邨的春天在何处?怎么刮来的依然是刺骨的寒风啊!
同时,另一个声音在他耳边响起:“吃够苦的孩子更想偿试甜,家贫出孝子!”
这是他父亲说过的。
他出生在贫穷的家里,命运注定他要比旁人吃更多更大的苦。穷人的孩子,尤其是长子,要多吃苦,要早当家。
'本书首发来自17k,第一时间看正版内容!'
;。。。 ; ;
第十一章
“有人偷东西啦!”
“抓贼骨头啊!”
“捉小偷啊!”
大路西北方向的树林子里有人大声呼喊。小孩子的喉咙。
树林郁郁苍苍。树林的旁边有几间低矮的砖瓦房和几间没有墙壁、用毛竹与木头支撑的简易茅草房,围成一个场院。环境十分幽静。几个孩子在树林边上放鹞子。鹞子在树林上空忽闪飘荡,样子悠然自得。
西邨循着呼喊朝前看去,场院的南面、紧靠大路边是被荒丘围起来的一圈菜地。菜地里果然有个身影弓着背、掬起屁股在挖地里的胡萝卜。她的身后放着装满鹞子的背篮。是丝丽姐!
听到呼喊声,房子里追出二个大人来,放鹞子的二个孩子牵着线也从树林子那边跑过来。“抓住她!”“是卖鹞子的!”“偷菜的贼骨头,别让她跑了!”
“叔叔阿姨,吾饿坏了,拔两根萝卜充充饥的,不是偷。”丝丽分辨说。
“不告而取就是偷!你饿就能偷别人的东西啊,强词夺理!”房子里跑出来的男子厉声责问道。男子看上去有五十开外,生得高大壮实,脸皮黝黑。
“哟,还是卖鹞子做生意的呢,偷东西的贼!”跑过来的中年妇女皮肤白净,说话的语气柔和中透出气愤。
“爹爹,我看见的,她在东青街上卖鹞子的,怎么跑到这里来偷东西啦?”一个看上去十二三岁的女孩牵着鹞子的麻线走过来。她就是抢着买写有“上青天”“飞马”寓意鹞子的小姑娘。
“不是的,叔叔阿姨,小哥哥小姐姐,吾是到东青来卖鹞子的,可是,东青人像强盗,幸亏吾跑得快,走到这里肚子实在饿得不行了,吾以为这地里的胡萝卜是天出的,就拔了几根,还没来得及吃。喏,泥巴还没揩干净呢。”丝丽狡辩说。
“什么‘天出’的?没有人种胡萝卜会从天上掉下来?真会狡辩!看你也有十六七岁了吧?一个大姑娘,偷东西都不知道脸红,不懂得羞耻!”妇女数落道。
另一个放鹞子的男孩一手牵着鹞子,走过来要去夺丝丽手里的胡萝卜,“还不拿来!”
丝丽以为男孩是来打她的,想往后退,却不料菜地里的积雪刚融化,脚下打滑,一个趔趄摔倒在地里。
“摔得好!让你偷!”放鹞子的男孩和女孩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