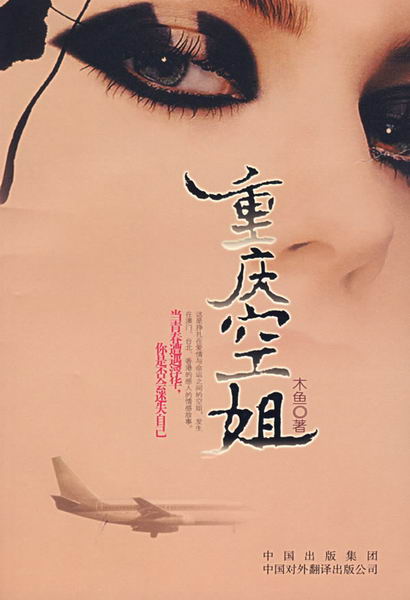重庆孤男寡女-第2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安生:我现在在海南。这些天发生了很多事,让我对人生有了更多的思考。绢子刚刚离开我们,在她妈妈的怀里,面向大海。这个小小的生命,在最后时刻十分顽强。在重庆的时候,她的病情已经恶化得很严重,医生也已经放弃了任何努力。当她对妈妈说,她最后的一个心愿是看看大海时,医生们都认为不可能,说她的身体不足以支撑到海南。但她竟然做到了,虽然路上几度在妈妈的怀里要睡着,但又顽强地醒过来——她怕一闭眼就永远不能睁开。
我和她妈妈一路轮流给她讲故事,以保持她的精力。因为心情悲伤,故事根本不可能讲得完整,但她还是认真地听着,我们讲错了,她还用微弱的声音补充。有一次我当着绢子哭出了声,绢子却反过来安慰我:'妖妖姐姐别哭,一哭就不漂亮了,就不是绢子心中的那个妖妖姐姐了。姐姐笑一笑,为绢子保留那漂亮的形象,好吗?'在这个坚强的小生命面前,一切都微不足道,一切又都弥足珍贵。绢子离去的瞬间,我泪如雨下,仿佛失去的不仅是绢子,而是生命中的全部。突然很想你,即使像从未见过面那样重新开始,也渴望能再见次到你。我一边流泪,一边拨打你的电话,可是你一直关机,我发疯似的在雨中奔跑,找到这间网吧,给你发来这封信。本来说过,这三个月中不和你联系,但我现在无法自持,还是想告诉你,请你一定遵守见一面的约定,不管结果如何,一定要见上一面。一定。
妖妖。“是今天刚刚发出的。也许此时妖妖就坐在海边的某个网吧,面向大海,默默不语,全世界的大雨在她面前纷纷而下。
我一遍又一遍地看着妖妖的信,直到所有的字迹在我的眼泪中模糊,然后点击硬盘格式化,消除一切痕迹。
出门以前,我看到门边有一张喜帖,我打开来看了看:恭请安生先生暨花妖小姐参加十月一日在万豪大酒店举办的婚宴,新郎熊伟、新娘余利。看到我的名字和妖妖的名字站在一起,我再次热泪盈眶。喜帖是特别印刷的,上面有熊伟和余利幸福的笑脸,我把他们轻轻地扔在沙发上。
在重庆森林大酒店,当电梯到来的时候,我看见丁树声搂着一个不认识的小妞走出来,看见我,有些尴尬,但还是站住了。
“安静……她还好吗?”我看着他身边那个穿着低胸T恤超短牛仔裤的妞,没有言语。
丁树声讪讪地放开楼着那妞的手,叫她先去前面等着,那妞看了我一眼,不情愿地在前厅的沙发上坐下,随手从报架上抽出一本画报翻看,眼睛不时往这边瞟着。
“安静最近身体怎么样?”“你们不是都离婚了吗?还关心她干嘛?”丁树声一听,瞪大了眼睛:“谁说我们离婚了?”“没有?”这下轮到我吃惊了。
“你真不知道?”看着我茫然的样子,丁树声说,“她怀孕了。”我愕然:“……是那次?”丁树声点点头。
“真能啊。”我不无嘲讽地说。他和小妹要了几年孩子也没要上,却在那种情况下怀上了孩子,这讽刺可真够辛辣的。
“法院也因为这个判了她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我跟法官说不告她,可是人家不听,说刑事案不能撤。”“干嘛,这时候假慈悲,早干什么去了?”“……大哥,你帮我劝劝你小妹,别拿掉肚子里的孩子,就是不离婚也行。”“你自己不会去跟她说?”“我去了,不让我进门,送的东西也给扔出来,大哥,求求你。”我看了看在那边不耐烦地坐着的妞,又一言不发地盯着丁树声,然后狠狠地说了句:“滚!”电梯到达,我走进去,丁树声在外面喊:“大哥……”电梯门关上,他的喊叫立刻被掐断,就像一只突然被人扭断了颈项的鸭子。
我在服务小姐的带领下,来到包房,两张大圆桌旁坐满了各式各样的人——这种各式各样是他们穿的风格迥异的服装带给我的感觉,在一堆西服、夹克中间,还有几个穿军装的人。其中一个穿军装的家伙端了一杯酒走过来,指着我大声说:“嗨,你这家伙,怎么今天才来参加我们的战友会,是没把战友们放在眼里吧?”我看着他,仔细辨认了一下,并不认识,这里没有一个我认识的人,但所有人都摆出和我十分亲切的样子。桌子边那帮人已经喝得面红耳赤,冲我喊:“还站着干什么?迟到了,入席三杯。服务员,换大杯子!”我看到里面有个家伙把茶杯里的水倒了,然后往里面倒五粮液:“没说的,这么多年不露面,先得把这个干了。”身后有人推着我不由自主地往桌边走,我在桌子边站定,才看清推我的人是沈汉。
“他们……”沈汉见我疑惑地看着他,于是向我解释:“这里的人没有你同期二连的,有些是其他连队,有些是咱们退伍后才进去的,所以你可能不认识。刚才我已经告诉他们有个战友要来。”边上一个家伙大着舌头喊:“别说了,先喝酒,喝完酒再交待革命历史!”原来这些家伙也不认识我,却做出亲热无比的模样,我差点以为他们属于我失去的记忆里的人。我端起茶杯,一饮而尽。
“好!”那帮家伙热烈鼓掌。
刚才倒酒的家伙又给倒上一杯:“哥们,够爽快,再来一杯!”我看着眼前这些热切期盼的脸,似乎他们此刻人生的全部意义就在看我喝酒上,于是不吭一声,端起茶杯又一饮而尽。
()
“好!”包房里再度爆发出一阵大吼。那家伙把第三杯递给我。沈汉在我身后问:“还行吗?要不,这杯我代了?”我端过茶杯,第三次喝了个底儿朝天。几个人上来,把我拥住,坐在椅子上,做出欢迎战友归队的姿态。
沈汉大声向大家介绍了我,隔壁桌一个穿西装的家伙端着酒杯站起来喊:“二连的兄弟是好样的,为二连干杯!”于是大家乱纷纷地站起来碰杯,喝酒。我挤过去,看着那个家伙:“你是二连的?”他夹了一大口菜在他胖乎乎的嘴里嚼着,含混不清地说:“不是,我是三连,九三年入的伍。”不是二连的为二连干什么杯!我问他:“你知道大傻吗?”他摇摇头:“不认识。”却随即站起来,端着酒杯喊:“为大傻干杯!”一帮人又乱哄哄地站起来碰杯。碰完杯,也没人问大傻是谁。
我在一片闹哄哄中站起来,大声问:“你们知道大傻吗?”这声喝问突如其来,让人无法把它和现场的场景联系起来。这帮家伙端着酒杯面面相觑,似乎我问了一个让他们不可思议的问题。
“他是我死去的一个战友,我想知道他怎么死的。”没有人回答,仿佛大家的意识依然停留在先前的状态。
“为死去的战友干杯!”不知道谁大喊了一声,大家如梦方醒,纷纷站起来举杯:“为死去的战友干杯!”干完,场面又恢复了热闹的气氛。
我没有再问有没有谁认识或听说过扁脑壳,回到自己的座位坐下来,也隔一会儿就稀里糊涂地站起来和大伙碰杯。这里根本不会有人认识什么大傻、扁脑壳,更不会有人费劲去追忆关于大傻和扁脑壳的事情,这帮人根本就是找个因由每月不管三七二十一的这么放纵一下。
喝到中间,一个很有派头满身名牌的家伙大声唱起了“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把营归……”旁边有人用筷子敲着节奏,然后不断有人应和进来,唱歌声和敲碗碟桌子的声音响成一片,唱完,又唱“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像太阳……”“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几乎所有部队的老歌都让他们唱了一遍。
沈汉搂着我的肩膀,在我耳边吐着酒气说:“怎么样?好玩吧?这里面有副县长、局长、师级军官,也有大公司老板,可一坐进来就他妈什么都放下了。”说实在的,我对部队生活并没有什么怀念,不管在哪里,不管干什么,不管是自己年轻和年老,本质上都一样,没有什么是值得特别留存的。这帮已经在各个行业很有成就的家伙,刚才对我提起的一个死去的战友完全无动于衷,这会儿却很投入地唱着这些老歌,甚至可以说是深情款款的样子,让我有些迷惑。他们究竟是在怀念那段时光,还是根本就把那段时光美化成一种精神寄托?
歌声渐歇,带头唱歌的家伙站起来,大声说:“同志们,我宣布,现在开始打靶!”“好!”一帮人乱成一片。
“打完靶有事的战友先走,没事的带着自己的姑娘,咱们在原地儿,接着喝!解散!”沈汉交给我一把房间钥匙卡,我立刻明白了打靶的意思。虽然很久已经没有接触过姑娘,但我似乎对此一点兴趣都没有。此刻因喝酒过多,头痛欲裂。反正去哪里都一样,哪里都不是归宿,我接过钥匙,踉踉跄跄地来到楼上房间,没有开灯,借着走廊的微光扑倒在床上。
我应该想起大傻和扁脑壳,而实际上,此刻我脑际浮现的是妖妖的脸。我始终还不清楚我对她的感情,我承认我对她产生了一些有别于其他姑娘的特殊的东西,甚至真的试图在她身上尝试一下爱的存在,究竟是她打动了我,唤起了我内心深处的某些东西,还是我因为这种孤男寡女的相处形式产生了错觉,不能确定。当她在我怀里的时候,我的确产生了一种类似于感念的东西,我和她的交欢,不是距离,而是归宿。那么妖妖呢?这个纯真的姑娘是什么感受呢?她清楚自己吗?或者她也是错觉呢?
房间的灯打开了。我的头埋在被子上,说:“不用了,你出去吧。”那个进来的小妞也许没有听清我的话,走过来,跪在地上替我脱鞋。我坐起来,想叫她出去,然而,看到她的脸,我怔住了。这是一张似乎很熟悉的脸,很自然的眉毛,挺拔的鼻子,瘦小的瓜子脸,特别是那眼睛,大大的,黑仁占据了大部分位置。这是个二十来岁的姑娘,没有KTV包房小姐的俗不可耐的浓妆,穿着也很清秀。
“你是哪里人?”“东北人……在重庆读大学。”姑娘一口东北话,当她说自己在重庆读大学的时候,有些难为情,却又为自己说出来感到轻松。
不是,不是我以为的人,我好像松了一口气。其实,我以为她是谁,连我自己也不胜了了。
“为什么出来做呢?”问长问短可不是我以前的风格。
“学费很贵。”“我不用,你出去吧。”姑娘微微有些失望,但并没有像其他小姐那样缠上来,点点头,准备离开。
“等一下。”她站住了,我掏出四百块钱,给她。她迟疑了一下,接住了,居然低头说了声谢谢,出去了。我倒头继续睡,却怎么也睡不着,一些纷乱的前后没有任何逻辑关系的场景在我的脑子里交替出现。一会儿是丛林,一会儿是城市,一会儿是老唐,一会儿是远处哨所的缅甸小伙,大傻,扁脑壳,古萍,妖妖,甚至是已经从我的生活里淡出的余利和阳阳……就在纷乱的场景中间,突然出现一个清晰的信息——我想起了我刚才差点以为那姑娘像谁,是啊,大傻的妹妹,那双眼睛,大大的,黑仁占据了大部分位置。
“哥,我长大了也能穿军装吗?”“不,他们不招收女兵。”“哥哥骗人,哥哥骗人,电影里就有女兵!”“咱们农村姑娘当不了女兵。”“为什么呀?为什么呀?安哥,我哥哥骗我,是吗?”那双黑眼睛看着我。
“是啊,他骗你呢,咱们玉茭长大了当女兵去。”“哦,我要当女兵咯,我要当女兵咯。”我想起来了,那个在重庆永川黄瓜山的乡村。探亲假,我没有回家,而是和大傻一起去了他在乡村的石屋。那个秋天,山上的茅草金黄。就在这个秋天,老爸在医院去世,部队辗转通知了我这个消息,我没有告诉大傻,第二天,和他一起踏上了回哨所的归程。
我打开房门,来到楼下包房,又有一帮家伙围在里面喝酒,沈汉也在,每人身边坐了一个妞。那个带头唱歌派头十足的家伙见我进来,冲我喊:“嘿,怎么样,那妞够爽吧?哥们以前上过,技术不错,所以介绍给你。她有没有跟你说她是大学生?”他见我茫然地看着他,得意地说:“把你骗过了吧?哈哈,老子没有上她的当,照样把她干得哇哇叫。”这家伙牙齿黑黄,边说边挥舞着拿着烟的右手,还在他身边的妞脸上拗了一下,满脸得意的神情。但随后他马上变得惊慌失措,因为我突然上前抓住了他的领子,把他的脸拉到自己跟前。
“你认识大傻吗?”他不知所措,完全不清楚我问他这句话的用意,结结巴巴地说:“不、不认识、怎么了?”我挥拳在他脸上狠狠地来了一下,把他打到地上。
“操你大爷,你干的是他妹妹。你们他妈的干的是你们自己的妹妹!”所有人都看着我,没有吭声,也没有人上来劝解,好像脑子已经停顿,不明所以。半晌,那家伙从地上爬起来,茫然地问沈汉:“他怎么了?”又看着我身后:“你有哥哥吗?”我回头,那个大眼睛姑娘在另一个战友怀里,刚刚走进来,她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小心地回答:“我没有哥哥,我爸妈就我一个。”“操!”我转身走出包房。
我不知道今晚我为什么要发火,我他妈以前不也这样乐此不疲地和各种款式的姑娘交欢吗?难道因为即将离开这个世界就有资格像个卫道士一样责骂别人?要不你就彻底堕落,要不你就永远清高,这副谁都排斥的模样简直让人恶心透顶,比那帮家伙更他妈让人恶心。
夜风中,我走过解放碑广场,人们一群一群,表情却各不相容,他们也只是孤男寡女,因为仅爱自己。四面高楼林立,解放碑像是一具不合比例的棒棒,可笑地萎缩在广场中间。这就是这座城市的根。
50、什么是归宿?
大巴从高速公路下来,停靠在永川市客运中心。候车室里南来北往的人歪七扭八地坐在玻璃钢椅子上,里面混合着香烟和汗味儿,还有谁包里浓烈的海产品干鲜味道。我仰着脖子,看了看显示屏上滚动着的客车时刻表,费劲地寻找去黄瓜山最近的车次,那是十分钟过后一辆到四川泸州的过境客车。
半个小时后,客车就颠簸在了黄瓜山山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