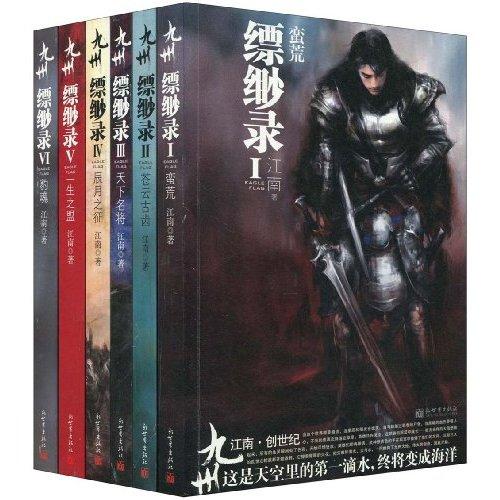九州·华胥引-第2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小心地看他一眼,伸出两只手放到他额头两侧,他愣道:“干什么?”
“不要气了,生气多容易老啊,来,我给你按一下,还疼不?”
“……”
——*——*——*——
不知莺哥此后何去何从,但无论她做什么样的选择,已不是我们所能左右。想到她来找我时眼中毫无光彩的颓然和那些决绝的话,心中就有些发沉。恰在此时,一只小小的灰鸽子扑进刚推开的木窗棂,直撞进我手心。
这是君师父的传信鸽。我愣了愣。想不到这么快又有生意。
展开素笺一看,忍不住对慕言扬了扬信纸:“你说容浔正遍天下寻找能救活锦雀的名医果然不错,这次居然找到了我师父。”
他正在收拾血迹斑斑的枫木琴,闻言抬头:“哦?华胥引竟还有这等功用,能生死人肉白骨?”
我踌躇道:“生死人肉白骨倒说不上,只是换换命罢了。”想想又补充道:“其他的人可救不活,只能救活因选择华胥幻境而在现实中失掉性命的人。前提是,还得有一个同她血脉相连的至亲之人愿意以命换命。”
他若有所思:“所以,你师父来信让你用莺哥姑娘的命去换锦雀姑娘的命?”
我将信笺收好,摇摇头:“师父他压根儿不知道锦雀还有个姐姐活在世上,只是让我去走个过场,说是郑王都找到他跟前来了,实在不好意思推脱。”
说完到处找笔墨:“得给他回个信,明天就要出发去找小黄和君玮了,哪里有时间。锦雀本就一心求死,救活了又怎样,既然强求无益,何必苦苦强求,救活的那个人也未必会感激他什么。”
说到这里正找到矮榻附近,擦过莺哥身体时蓦地被一把握住手。我惊讶垂头“你醒了?”
她闭着眼睛,没有放开我,半晌,道:“君姑娘若是能救舍妹,还请勉力一救。”
我看着她:“你发什么傻?除非用你的命去换她的命,否则根本没可能把她救活。倘若你果真想这样痛快就放弃性命,那不如把这条命给我,我来为你织一个幻境,让你和容垣在幻境中长相厮守。”
她终于睁开眼睛,眸子浓黑,却无半点神采,大约这就是所谓的哀莫大于心死,恍眼看上去倒比我更像个死人。
良久,她像是终于反应过来我的话,侧头疑惑地看着我,眼睛里一片空茫:“那又有什么用?都不是真的。”我才想起来,她这个人一向较真,宁愿明明白白痛苦,也不愿糊里糊涂幸福,这段故事里,活得最清醒的就是她了。
而我无言以对。
她转回头看着房梁,声音毫无起伏:“今年我二十六岁,觉得这一生很好、很长,没什么可留恋了。”顿了顿,又道:“只还有一个愿望,我死后,请让我和我夫君合葬。”
七月,蓼花红,木槿朝荣。
兜兜转转回到郑国。
施术之所定在四方城城东为举行祭礼而建的土台上。我想莺哥大约不愿见到容浔,以秘术一旦施行不能有任何生人打扰为名,将方圆五里清了场,只留慕言在土台下喝茶。
锦雀的棺椁在酉时初刻被抬上祭台。已近一月,寻常应是白骨的躯体却未有半点腐坏,只是脸色有点苍白,可看出容浔确实花了心思。酉时末,莺哥最后一个到场,纱帽揭开,看到及腰的发,毫无表情的一张脸。我将含了血珠的茶水递给她:“现在还可以反悔的。”她却一口就喝下去。我看了眼空空如也的茶杯,还是想要说服她:“这件事我真是没有把握。”将几案上竖列的两张瑶琴指给她看:“我得同时弹奏你们两人的华胥调,一个音也不能错,还得摧动鲛珠牵引你的精神游丝……”她打断我的话:“若失败了,会否对君姑娘造成什么反噬?”我摇摇头:“那倒不会,就是你多半活不了,你妹妹也救不活。”她瞥了眼棺中的锦雀,目光淡淡的:“这也没什么,君姑娘,开始罢。”
站在土台上,四方城东西南北十二条街道尽收眼底,夕阳掩映下,房屋鳞次栉比,似镀了层金光,偶有几户升起袅袅炊烟,平凡世上也有平凡幸福。
琴音泠泠,土台上骤起狂风,躺在石祭台上的莺哥缓缓闭了双眼,缀在长裙上的紫纱随风飘飞,像一棵瑰丽的树,越长越大,渐渐将她笼起来。再见了,十三月。我闭上限,正欲凝神催动鲛珠,破空声来,睁眼时枚古剑堪堪定上身前七弦琴。弦丝尽断,狂风立止。我怔了怔,抬眼塑向前方的石祭台,看到紫衣男子挺得笔直的背影,柳絮纷扬,慢悠悠落下来,似裁剪了鹅毛碎。我抱着断掉的琴几步急走过去。男子正俯身揭开笼在莺哥脸上的轻纱,修长手指颤抖地抚上她的眉,声音却低沉平静:“她是睡着了吗?”
我施了个礼,将紫纱重新盖好,边角都扎严实,又将袖子拉下来点,好盖住她冰凉的手:“两位夫人只能活一位,陛下想救月夫人,我便为陛下找来尚在人间的紫月夫人以命换命,紫月夫人不死,月夫人不能活。两位夫人到底保哪一位,陛下不妨再想想。”
我等着他回答,却未等到任何回答,因话毕时轻纱微动,莺哥已渐渐醒转,本以为她会再昏迷一些时候,那双杏子般的眼眸却缓缓睁开了。半晌,浓黑的眸子里突然升起千般华彩,她看着面前这个端整的紫衣男子,蓦然扑进他怀中,声音里带着小女孩的天真:“我们终于能在一起了。”他愣了一下,抬手将她紧紧搂住,她把自己更深地埋进他怀中:拔颐侵沼谀茉谝黄鹆耍菰!彼成布渖钒住?
一点一点将她拉离自己的环抱,他静静看着她:“我是谁?”
她眼角渐渐有些红,眼睛里也漫出一层水雾,目不转睛盯着他的脸,半晌,伸手搂住他的脖子,头埋进他肩膀,哽咽道:“他们都说你死了,我不相信,如果你死了,我该怎么办呢?”
容浔的手僵硬地垂在身体两侧,良久,沙哑道:“月娘……”
我淡淡道:“别在意,她这样多半是疯了。换命之术最忌中途打扰,怕正是因此……若陛下仍想救月夫人,紫月夫人她这样,也是无碍的,只是要劳烦陛下再送我一张七弦琴了。”
他却并未搭理我的话,半晌,苍白容色浮出一丝苦笑:“即便是疯了,终归,最后是我得到了她。”
我看着他:“若是她清醒,第一件事怕就是为景侯殉情。”
柳絮漫天,似在祭台上下一场轻软无终的雪,他将她抱在怀中,向石阶走去:“那就让她永远不要清醒。”她的纱帽落在地上,风卷过来,似一只断翼的蝶。
在土台上站了好一会儿,我有点混乱,不知怎样做才算是好,现在好像也不错,大家都求仁得仁。容垣想要的是莺哥活下去,她活下去了。容浔想要和莺哥在起,他们在一起了。莺哥想要容垣,在她的意识里,也确实得到了。就像是一场华胥幻境,美好虚妄,各有所得。
走下土台,看到慕言正一派悠闲地煮他的功夫茶,我生气遭:“刚才你为什么不拦住容浔啊?”
他好整以暇地看着我:“是我叫他来的,我为什么要拦住他?”
我瞪大眼睛。
他将煮好的茶递给我:“每个人都应该有选择的机会,你说对么,阿拂。”
我不知道对不对,只知道有多少入迷失在这虚妄的华胥幻境,自以为懂得爱的美好,要抓住这美好不容它错过,其实都是软弱。人最宝贵的是什么?不是爱,是为爱活下去的勇气。可我遇到的这些人,没有一个人懂得。
不几日,我们离开四方城,听说锦雀被厚葬,这一月的良辰吉日,莺哥将同容浔大婚。得知这消息时并没有什么特别感想。而在第九日早上,却听说大婚当夜莺哥失踪,容浔将整个四方城翻过来也没找到。慕言问我:“你觉得她应该是去哪儿了?”
其时我正在给君玮写信,确定他所处的最终方位,争取早日顺利找到他和小黄,听到慕言提问,三心二意回答:“可能是突然清醒,去完成她的最后一个愿望了吧。”
“我死后,请让我和我夫君合葬。”我记得那时她是这么说的,这是她最后一个愿望。
慕言沉默半晌,过来随手帮我磨了会儿墨。
当夜,一向风度翩翩的慕言难得模样颓唐地出现在我房中。夜风吹得窗棂格格作响,我一边伸手关窗户一边惊讶问他:“搞成这样,你去哪儿了?”
他从袖中取出一块紫纱,笑了笑,轻描淡写道:“在容垣的陵寝中捡到的。”
我顿住给他倒水的手,良久:“莺哥她,是在容垣的墓中?”
他从我手中取过茶壶,自己给自己倒了一杯:“更确切地说,是在容垣的棺椁中。”
我愣了愣,半晌,道:“怪不得他们都找不到她。”
他笑笑:“没有人敢去动景侯的陵寝,他们永远都不会找到她了。”顿了顿,又轻飘飘添了句:“除了我。”
我赞同地点头:“对,除了你。”指着他的袖子:“但你好像受了伤。”
他面不改色将手缩回去:“没有的事。”
我拉过他的手把袖子挽上去给他涂药,发现他僵了一下,抬头瞟他一眼,有点讪讪地:
“我有时候是不是,太任性了?”
他撑着额头看我,唇角含笑:“不,这样刚刚好。”
番外诀别曲
“寻寻觅觅半生,最好的东西却在寻找中遗失,谁会像我傻到这个境地。月娘,我用半生无知,为你谱这支诀别曲。”
他又听到她的声音,温软的决绝的,响在耳边:“杀了我,容浔。杀了我,我就自由了。”话尾处一声叹息,想冰凌中跳动的一簇火焰,不动声色灼伤人心。
他捂住胸口,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疼。同样的梦已做了无数次,却还是不能习惯。
有秘术士告诉他逃避噩梦的方法,但他没有用过,这是他知道的唯一再见她的方式。在一位她死去的那三年,他一次也没有梦到过她,而今她带着嫁衣失踪三月,在他坚信她还活在这世上的时日,她却夜夜入梦。
他其实已想到那个可能,只是拒绝相信。若她果真已不再人世,她的魂魄夜夜归来,就算是要折磨他,也是应该让他看到她的模样,而不是只给他一个虚无缥缈的声音。
每一个关于她的梦境,都不曾真正看到她的身影,那是他用来说服自己她还活着的唯一理由。说服自己相信这些不详的梦只是太想她,而不是真正有什么不详之事已经发生。
可今夜,却不同。
令人窒息的梦境中,他听到那个声音,本以为会像从前无数个夜晚,就那样被胸口的疼痛生生熬醒,但这一次不知为何,却并未醒来。
他看着自己的手,一条长长的刀痕,掌管命运的掌纹被拦腰斩断,姻缘线显出模糊的深痕。
一朵戎面花不知从何处飘来,落在他手心,云雾后谁唱起一支歌谣:“山上雪皑皑,云间月皎洁,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
他愕然抬头,看到雪白的戎面花从天而降,摇曳不休,似落在野地的一场荒雨。而坠落的花雨中,那个紫色的身影正缓步行来,臂弯处搭了条曳地的朱色罗纱,细长的眉,浓黑的眸子,绯红的唇。地上的戎面花自远方的远方,一朵朵变得朱砂般艳丽,转眼她就来到身边。
他知道这是梦境,却忍不住想要握住她,可她像没有看到,他的手穿过她的身体,他惊愕的回头,她的背影已那么
脚下的戎面花像是铺就一条红毯,雾色浓重的远处,她走过的地方,悬在半空的宫灯一盏一站点亮。他终于看到行道的尽头,昭宁殿三个鎏金大字在宫灯的暗色中发出一点幽幽的光,殿前两株樱树繁花满枝,开出火一般浓烈的色彩,朱色的大门徐徐开启,显出院中高挂的大红灯笼,和无处不在的大红喜字。
她想起来这一夜,应是她嫁给容垣。那时她的重要,他并不明白,拱手将她送到另一个男人怀中,那些类似疼痛的情绪,他以为只是不习惯。
对莺哥那样的情感太难描述,她是他亲手打造的一把刀,是最亲近的人。在没有谁像她那样,一切都是他所教导,一步一步,按照他的意愿长成她所期望的模样。
看着她褪去女子的情色女天真,一日日变成冷血无情的杀手,有时他会还念她从前单纯胆小的模样,但是若是非要二者选一,他宁愿看到她是容家最好的一把刀,自己最得意的作品。
她的情意他不是不明白,课他不能爱上她,枕边人可以有很多,但是容家最好的到只有一把,这锻造来得这样不易,他不能随意将她毁掉。
他已经开始打算,下一次,若下一次她扑进他环抱,他一定将她推开。他从未想过自己那样意志不坚的人,当她的手臂圈住他的脖子,那样甜蜜又清冷的月下香令他无从抗拒,总想着下一次,下一次一定……
锦雀就是在那样的时刻出现。和她一模一样的容貌,笑起来天真无害,就想十六岁前尚未成为杀手的她,瞪人的样子尤其地像。
第一眼看到锦雀,比起惊讶来他竟是为长久挣扎的情绪松了一口气。有些人可以爱上,有些人不能爱上,他看着紫阳花丛中皱着眉头的锦雀,告诉自己,这是一个安全的,可以爱上的女子。那时他没有想过,他见过那么多所谓天真安全的女子,为什么只有锦雀让他觉得可以爱上。
莺哥不明白,以为他是真的爱上锦雀,连他自己都那样以为。这是一场时间最彻底的移情,对莺哥的所有感情都尽数移植到锦雀身上,然后一次又一次告诉自己,眼前这个笑容天真的女孩子,才是自己真心想要珍惜。
但看到莺哥强装的半是真心半是假意的小,他却一日比一日烦乱,他总是能准确抓住她眼中一闪即逝的悲色。将一个女人自自己的感情世界尽数剔除,这会有多难?
他从来相信自己有一副硬心肠。他爱的人、要娶的人是锦雀,那是和她全然不同的女子,她的笑太假、性子太强、心肠太狠、手段太毒辣,强迫自己眼中一日日只看到她那些不好的、不过美的地方,这日复一日的心理暗示,让他果然越来越讨厌她执刀的模样。
直至那一日,他亲手将她送进郑宫,送到别的男人手中。他从前那样压抑自己的情感,是因为他珍惜她作为一把刀的价值,可时移事易,在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之后,深入局中举步维艰的他全然忘记,容家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