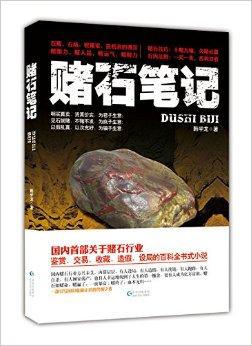情爱笔记-第2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冰的一句话:If you can dream——and not make dreams your master(如果你能做梦——又不做梦自己当家……——译注)
这是个及时的提醒。他还仍然是自己梦中的主人吗?或者是梦在主宰着他?就因为自从与卢克莱西娅分居后做梦太滥?
“从那次法国大使馆共进晚餐以后,我和她成了朋友。”他妻子继续在讲述。“她邀请我去她家做客,一起洗蒸汽浴。看来在阿拉伯国家这是个非常普遍的习惯。蒸汽浴。这和桑拿浴不是一回事,不是干洗。是在奥兰迪亚的住宅里,花园深处,让人建造起一间浴室来。”
堂利戈贝托继续茫然地翻阅着笔记本;但是注意力已经不完全在上面了;他也进入那个种满木曼陀罗、白花和紫花的月桂、盘绕在露台支柱上散发出浓香的藤忍冬的花园里了。他瞪大眼睛,监视着那两个女人——卢克莱西娅,身穿一件带花的春装,脚踏露出那滑石般光洁的双脚的凉鞋;阿尔及利亚大使夫人身穿一件颜色好看的长袍,在晨光下闪烁——,一面在长满红色天竺葵、绿色和黄|色的蓖麻的灌木丛和修剪整齐的草坪中穿过,目标是一座半遮掩在大榕树下的木结构房屋。“蒸汽浴,蒸汽治。”他自言自语地说道,感到心儿在跳。那两个女人背对着他,他惊叹二人体形的相似之处,肥大、稳定的臀部有节奏地扭动着,脊背高傲地挺立,走起来颤抖的大腿给衣裳画出皱格。二人手挽着手,极为亲密友好,手里拿着毛巾。“我也在那里,可以得福升天了;可我在自己的书房里,他想,如同胡安·马利亚·布劳森在他那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单元房里一样,扮演了利用女邻居盖卡的密探阿尔赛,又扮演成迪亚斯·戈莱依医生,逃脱出那个不存在的圣达马利亚。”可是,他从那两个女人身上开了小差,因为翻过一页笔记,看到了另外一段从《短暂的生命》炒来的语录:“您根据自己的了解任命了全权代表。”
“这是一个属于胸膛的夜晚。”他动情地想到。“我和布劳森难道只是一对精神分裂症患者不成?”他一点也不在乎。他早已经闭上眼睛,这时看到那两个女友毫不或犯作态地在脱下衣裳,动作熟练,仿佛在这个蒸汽浴室小小的木制前厅里曾经多次举行过这样的仪式。二人把衣裳挂在农钩上,围上宽大的浴巾,快活地谈论着利戈贝托不懂得、也不想懂得的事情。
随后,她俩推开一道无锁的小木门,走进充满蒸汽的小木屋。他感到一股股湿润的热气扑在脸上,弄湿了他的睡衣,钻进了他的脊背、胸膛和大腿。蒸汽从他的鼻孔、嘴巴、眼睛钻进了他的身体,带过去一股类似松香、檀香、薄荷的气味。他浑身颤抖起来,害怕会被两个女友发现。可是她俩丝毫没有理睬他,仿佛他不在那里,或者他是个无影之人。
“你不要以为人家给她用上了什么人工材料,什么聚硅酿之类的破烂玩艺儿。”卢克莱西娅向他澄清道。“绝对没有。人家是用她自己身上的皮肤和肌肉再造出来的。从腹部、臀部、大腿上各取下一小块。没有留下丝毫痕迹。结果妙极了,妙极了!我敢发誓。”
的确,他在证实这一点。她俩已经脱下浴巾,在一条背靠墙壁的木条板凳上坐下来,二人挨得很近,因为空间很小。堂利戈贝托透过蒸汽波浪状的运动欣赏着两具裸露的身体。这比安格尔的(土耳其浴室)要好多了,因为安格尔在画中把裸体堆集在一起,因而破坏了注意力的集中——他骂了一声:“该死的集体主义!”——而在这里,他的感觉可以集中起来,可以一眼就抓住了两个女友,可以盯住她俩,而不会错过任何微小的动作,可以把她俩控制在整个视力之下。此外,《土耳其浴室》里的身体是干燥的;而这里卢克莱西娅太太和大使夫人的皮肤上在短短几秒钟内已经挂上了晶莹的汗珠。他激动得心里想:“她俩可真漂亮。”
“二人在一起显得更漂亮,好像一个人的美启发了另外一个人的美。”
“一点伤疤的影子都没有。”卢克莱西娅坚持道。“无论腹部、臀部还是腿部,都没有痕迹。至于再造的Ru房就更不用说了。简直让人不可思议,亲爱的。”
堂利戈贝托信服得五体投地。怎么能不令人信服呢?这两个美人就在他眼前,近在咫尺,如果他敢伸出手去,那就可以摸到!(“哎呀呀!”他肾伶地叫起来。)他妻子的身体比较白皙;大使夫人的比较黝黑,好像是在野地里长大的一样;卢克莱西娅的头发直且黑;而她女友的则卷曲而且发红。但是,尽管有这许多不同,二人却在以下方面相同:都蔑视时髦的消瘦和针叶型的风格,都喜欢文艺复兴时代的华丽,都讲究充盈丰满的Ru房、大腿、臀部和双臂,都追求美妙的圆形——无需抚摸就可以知道——坚实、硬挺和绷紧,仿佛是那些看不见的|乳罩、束腹带、背心、袜带塑造压缩成型的。对此,他赞美道:“古典派模式,伟大的传统。”
“由于多次动手术,多次疗养,她吃了许多苦头。”卢克莱西娅太太同情地说。“但是,她的美丽、一定要成功的毅力、一定要战胜自然的决心、一定要延长美貌的愿望,都给了她很大帮助。终于,她打赢了这场战争。你不觉得她美极了吗?”
“你也美极了!”堂利戈贝托用祈祷的口气说道。
热气和汗水已经搅得她俩躁动不安。二人深深地呼吸,胸膛如同海浪一般缓慢而深长地起落。堂利戈贝托感到窘迫难耐。她俩在说什么?二人的眼睛里为什么会发出调皮的闪光?
他支起耳朵,努力去听:“简直无法相信这是真的。”卢克莱西娅太太注视着大使夫人的Ru房,夸大她的吃惊程度。“它们能让任何人喜欢得发狂。真是做得再自然不过了。”
“哦丈夫也是这么说的。”大使夫人笑起来,说着故意挺起胸膛,让Ru房烧烟生辉。她说话时吸嘴,有法国口音,但是发字母j和r时是阿拉伯人的方法。堂和戈贝托做出了判断:她父亲出生在奥兰,同阿尔贝·加缨一起玩过足球。他们做得比原来的还好,现在他更喜欢了。你别以为手术以后它们变得感觉迟钝了。根本不是这样的。“
她笑了,装出不好意思的样子;卢克莱西娅也笑了,在大使夫人的腿上轻轻拍了一下,这吓了利戈贝托一跳。
“希望你别误会,也别瞎想。”过了片刻,卢克莱西娅说道。“我能摸摸Ru房吗?你在乎吗?我特别想知道如果用手摸摸的话它们是不是像看上去那样真实。提这种要求,你是不是觉得我发疯了?你在意吗?”
“当然不在意了,卢克莱西娅。”大使夫人亲切地回答说。她吸嘴的程度更厉害了,笑着张大了嘴巴,真正骄傲地展示她那雪白的牙齿。“你来摸我的,我也摸你的。咱们比较一下。
朋友之间亲热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就是,就是。”卢克莱西娅高兴地叫起来。接着,她用眼角瞥了堂利戈贝托呆的地方。
“她从一开始就知道我呆在这里了。”他叹了一口气。我不知道你丈夫怎么样。可我丈夫非常喜欢这个。咱们来玩吧,来吧!“
她俩开始抚摸起来。起初小心翼翼,随后,胆子越来越大;现在已经互相抚摸|乳头了,没有半点伪装。二人越来越靠近,终于拥抱在一起,头发互相汇合成一堆了。堂利戈贝托几乎看不清二人。汗珠——也许是泪水——不断地刺激他的瞳孔,弄得他只好没完没了地眨动和闭上眼睛。“我很幸福,我很悲伤。”他心里想,同时很清楚自己思想的不一致。这可能吗?
为什么不可能呢?既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又在圣达马利亚;既在这个黎明、孤独、荒凉、堆满笔记本和图画的书房里,又在那个春天的花园里,在蒸汽的包围中,大汗淋漓。
()免费电子书下载
“开始时是一种游戏。‘卢克莱西娅给他解释说。”为的是开心,同时也是去毒。立刻,我就想起了你。想你会不会同意这种游戏。会不会让你激动,会不会让你觉得讨厌,如果我讲给你听,会不会让你跟我装腔作势。“
他信守自己这一诺言:整宿对妻子享有全权的Ru房顶礼膜拜,因此跪在地上,处于卢克莱西败分开的两腿中间,后者则坐在床沿上。怀着求爱的态度,他一手握着一个|乳头,极为小心在意,好像那是易碎的玻璃、有可能碰破。他吸着嘴唇,一厘米一厘米地亲吻着Ru房,认真耕耘每一块土地,绝不留下半个田埂。
“也就是说,她挑逗我去抚摸她,为的是让我知道摸上去那不是假造的。她是出于礼貌,为了不保持正经的样子,好像很懒散一样。当然,这可是玩火。”
“当然。”堂利戈贝托点点头,一面不知疲倦地追求对称,公平地从一个|乳头跳向另外一个|乳头。“是因为它们渐渐激动了吗?是因为从抚摸要转向亲吻了吗?转向嘬吮了吗?”
他说完就后悔了。因为他破坏了这样一条严格的规定:快感和说俗话,特别是动词(喝和吮),是重创一切幻想的,二者之间水火不容。
“我没有说‘吸|乳头’。”他辩白道,努力追溯往事并且加以修正。“咱们就说亲吻,行吧?
两人中是谁开始的?宝贝儿,是你吗?“
他听到了她那轻优的声音,可是已经来不及看到她的身影,因为她很快就消失不见了,仿佛镜子上的热气被擦掉,或者被一阵冷风吹掉了一样:“对,是我。不是你让我这么干的吗?
这不正是你希望的吗?“”不是。“利戈贝托心里想。”我希望把你留在这里,有血有肉地在我身旁,而不是个幽灵。因为,我爱你。“忧伤仿佛倾盆大雨一样浇在他身上,急风暴雨卷走了花园、住宅。檀香、松香、薄荷以及藤忍冬的气味、蒸汽浴室和那两个亲热的女友。还有那几分钟前尚在的湿热和他的梦。黎明时分的寒冷钻了他的骨髓。匀速的海浪愤怒地拍击着悬崖。
这时,他回想起在那部长篇小说里,——该死的奥内蒂!神圣的奥内蒂!——盖卡和胖姐两个女人躲着市劳森,那个假阿尔赛,亲吻和爱抚;他回想起那个妓女或者前妓女、那个女邻居、后来被人杀害的女人,以为她的房间里挤满了魔鬼、你儒、怪物。前来骚扰她可又不见影子的抽象野兽。“一边是盖卡和胖姐,”他想,“另一边是卢克莱西娅和大使夫人。”这是精神分裂症,与布劳森一个样。就是幽灵也已经拯救不了他,而是每天都把他理进更深的孤独中,让他的书房布满了凶猛的野兽,如同盖卡的房间一样。是不是应该烧掉这座房子?
也要连同他和阿尔丰索在内?
笔记本里闪烁着胡安·马利亚·布劳森的一场春梦(“他拿起保罗·德尔沃一些绘画,奥内蒂写作《短暂的生命》时还不知道德尔沃的作品,因为这位比利时的超现实主义的画家那时还没有画出这些大作呢。”一条加引号的注释这样说道。):“我懒散地靠在座位上,靠在那姑娘的肩膀上,想象着自己正在远离一座由妓院组成的小城市;远离一座隐秘的村庄,那里面有一对对裸体男女倘佯在小花园里、长满青苔的小路上,一遇到灯光,一遇到搞同性恋的男仆……情人们就张开手护住面孔。”他会像布劳森那样结束吗?是不是已经成了布劳森了?
一个如同天主教理想主义、社会福音改革者那样普通的失败者,一个如同后来主张恢复绝对自由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享乐主义的家伙,一个如同具有高度想象、高品味艺术趣味的私人语言的制造者,他身上的一切都崩溃了:他爱的女人、他养育的儿子、他企图插入现实的美梦,他日渐衰弱,躲在那个成功的保险公司经理讨厌的假面后面,变成一个奥内蒂那部长篇小说中讲的那个“纯粹绝望的人”,变成《短暂的生命》中那个悲观的Se情受虐狂患者的复制品。
布劳森在结尾时至少还设法逃离了布宜诺斯艾利斯,他乘上火车。汽车、轮船或者大公共汽车,终于来到了他发明的拉布拉他河租界地:圣达马利亚。堂利戈贝托至少还相当清醒地知道:他不能在虚构小说中自己贩卖自己。不能与梦生气。他还不是布劳森呢,还来得及做出反应,做点什么。可是做什么呢?什么呢?
无形的游戏我从烟囱里钻进你的家,虽然那里不是圣达卡罗斯。我一直飘浮到你的寝室里,然后贴着你的脸,我模仿蚊子的嗡嗡叫。你在梦中开始黑乎乎地舞动双手同那个不存在的可怜的蚊子搏斗。
当我玩厌了这个装蚊子的游戏时,我揭开你的被子露出你的双脚,吹出一阵阵冷风,让你的骨头麻木。你开始发抖,缩成一团,乱抓毛毯,牙齿打颤,用枕头盖住自己,直到打起喷嚏来,但不是那种你因为过敏才打的喷嚏。
于是,我变成一股皮乌拉的热气、亚马逊的热气,让你从头到脚大汗淋漓。你好像一只落汤鸡,把被子端在地上,脱掉衬衫和睡裤。直到你光着身子,出汗,出汗,一面像风箱一样地喘息。
然后,我变成一根羽毛,让你浑身痒痒:脚心、耳朵、胳肢窝。嘻、嘻,哈、哈,呵、呵,你在梦中笑起来,一面做着绝望的怪相,一面向左、向右地来回扭动,为的是制止大笑引起的痉挛。直到你终于醒来,一脸的惊慌,却没有看到我,可是感觉到有人在黑暗中走动。
在你起床后准备去书房的时候,去用那些图画开心的时候,我在你路上设下陷阶。我把桌椅、摆设从原地挪开,让你跌跌撞撞,发出“哎呀呀”的叫声,一面抚摸着小腿。我一会儿把你的晨在和便鞋藏起来,一会儿打翻你放在床头桌上准备醒来时用的水杯。当你醒来在黑暗中摸索水杯可是却发现它在地上一滩水里的时候,你是多么地生气啊!
我们女人就是用这种种方式跟自己的爱人做游戏的。
你的、你的、你的幽灵般的情人。
八、镜中的野兽
“昨天晚上,我去了。”卢克莱西娅太太脱口而出。她没有完全明白自己究竟说了什么,就听到阿尔丰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