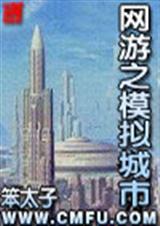城市-陌上桑-第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挣扎之中搏一活。
那是难的。
但是对他苦炭儿来说,却是可以做到的。
刚刚好,可以做到。
木轩感到苦炭儿要转身了,那种艰涩晦深的感觉,瞬间如同蚁穴溃堤,从丝发小孔般的颓势一崩千里。
苦炭儿确实是要转了。
只要转过身来,路,就活了。
就是这么个当口,就是这么个刹那。
两只手从木轩的侧后方倏忽而至,到得近前,一分为二,左削木轩,右斩苦炭儿。
被袭的两人都是手上功夫的好手,但这个时候,他们才算见到,这手上功夫,用到巅绝处,是个什么样子。
那对手出得太快。
那对手出得太绝。
绝到令那原本苦苦相峙的两人,都在一瞬之间,从心头涌出一个难以回绝的念头。
服了。
这一手击来,不挟风雷之势,只是带着一股子决意,一股子绝。一招之间,便见胜负。木轩伏地,苦炭儿遭擒。
这时候两人才得以看清来人的面目。
眉眼细长,双唇紧抿,这人是不识得的。或是,有些什么事情磨去了他原先容易被人识得的那一面?
哦,颜仲,手上“控缰”,脚下“伏枥”的颜仲。
苦炭儿和木轩相峙半晌,虽然有所互耗,但相对说来却亦形成犄角之势,两人之间,咫尺之距,可说固若金汤。
不过也正是缘于他二人斗得太深,才给了颜仲一击得手的机会。
这两人之间无论怎样,那所谓犄角之势,溃了。
一溃千里。
颜仲抄手拿起桌上那木盒子,万千瞩目,入手却不过尺寸厚薄。
不过那尺寸之中,确实还是有些沉的。
颜仲到的时候没从大门进来,但那“陌上桑”入手之后的一番跃动,却让他那脚下“伏枥”只想一纵如鹤,将这几年来的寞寞,快意一宣。
下一手,劈破栏杆,将那苦炭儿从三楼掷出。
俱散和顾融的交手,远远没有颜仲刚才在那与“请杀”之局相较的凶险。
他们打得很闷。
闷得就像这夏天午后的太阳,懒散,却又偏执。
这个胜负不是为了一决而决的。
对于俱散来说,这场胜负,在他心中,徘徊了快十年。
其实打滚道上,胜负本来就是常事,俱散本性潇洒,自然更不在意那些一招之间的胜败,只是当年的那一招,败得,实在是一塌糊涂。
“你还记得当年那一战吗?”俱散缓缓的递出一式,问道。
顾融却不忙回答,凝神接下那慢得无可再慢的一招,转身一肘撞出,矮小的身形在马路上几乎留不下长影,只有那一点一点的影斑,忽大忽小。
“你保镖,我劫镖,天经地义的事情罢了。”
俱散一笑。
“没错,各为其主。”俱散的笑逐渐化成一抹苦,这潇洒的男人,在这短坡之上,今天第二次显出些止不住的苦楚来。
当年他保的镖,是颜仲的女人。
那一次,颜仲正要替先生办一件大事,老城局面再起波澜,颜仲为免后旧城忧,托先生差人将自己的女人送到水乡一避。
先生差的是俱散,说起来,俱散作保镖,这一趟,应该十拿九稳的了。
可是“夙兴夜寐”的人不这么想,尤其当时新投到老爷子手下的一个人不这么想。
那个人,“枕戈”的人一向称其为,大公子。
那是沈先生的儿子。
可是,是投了老爷子一边的沈先生的儿子。
他谋的那劫镖一事,他请动的顾融,他随行,他动的手。
当时,那“跋荒原”上,只有俱散,和那颜仲的女人。
当时,俱散和顾融斗到酣畅处,竟已是生出些惺惺相惜。
不过,大公子猛然发难,改变了几个人,那以后十年的轨迹。俱散败了,因分神,而惜败,败给顾融一招。
只是一招,但那紧要处的一招,足教他不能再战。
若不是顾融手下留情,俱散今后的几年,艺业一道,已经不用再谈什么进境。
大公子抢了颜仲的女人,那是俱散当时就看到了的。
大公子强占了颜仲的女人,那是“枕戈”上下后来听说的。
之后就是颜仲出走社团。
“你知道我有多想再打这一场?”俱散道。
顾融阴沉的眼睛里竟难得的露出些暖意,“这一场,我也等你很久了,我只是担心,你的艺业是有进步,但这久违一场,你还能不能打得像那时一样好。”
九太岁在那矮房门口,不足十平的小院中,低着头,专心的享受着这下午最后一点温暖和惬意。
阿洛在他的身后,用一把小刀,细致的修剪着自己的手指甲。
“阿洛,你在想什么?”九太岁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没有说话,这一刻却像是忽然想到了什么似的,略略偏过头去,问道。
阿洛抬起了他那秀气的脸庞,他的脸颊清隽,白色的衬衣领口露出一截颈项,温白色的颈项,随着那一抬头,隐隐的动出一份锦来。
“锦绣阿洛”,这就是外人对这沈先生座下三弟子的赞誉。
“九哥,就算是仲哥他也不会想到这次我们齐聚栖凤,会与他西去‘浴海’,取那‘陌上桑’有关吧?”
“该当如此,不过,若那边局势明灭不定,环环之间渐趋险恶,以颜仲的本事,会想到我们要做的事情的。”
“我在想”,阿洛似乎这才想起九太岁刚才问他的问题,“我们这次来,有几分胜算。”
阿洛的字句,好像在谈论什么倒悬之事,但他的语气神情,却平淡非常,似乎这中间纵然波澜壮阔,也不会动了他那双眸之中的古井不波。
九太岁这回真的回过头来,不过,他那一侧身,一回头之间,也沉默了,这默,默的是阿洛的一问,诚如这山雨欲来的局势,胜算多少,他也不敢说了。
此番他们要应对的人,决然不会对“陌上桑”这样的事情松手,就算他已经隐没许久,但阖城尘烟再起,他还是会出而逐论两道的。
栖凤山,阖城市区中的一座小山包,南方城市,诸多山丘,这城中的山丘,正是市区一带怀巢区区府所在。
区府的护卫组织,称作“府卫”。
此时坐在区府门口小广场凉亭之上的卷儿,就是“府卫”新进的人。
卷儿很忐忑。
因为他感到那坐在凉亭之中,带他出来做事的胡姐姐也很忐忑。
胡姐姐是“府卫”的老人了,除了谈大当家,胡姐姐的艺业足可以领袖“府卫”,这些天胡姐姐带着卷儿自己,每天都在这凉亭上盯着那山势较低,不远处的几间矮房子,每看一天,胡姐姐的眉头就锁一天。
连她的眉头都锁住了,自己心中的郁郁如何能解?
不过似乎,胡姐姐担忧得有理。
那矮房中住的,都是老城那边过来的人吧。“枕戈”旧城自己资历再浅,在阖城长大,也不会是不知道那“卧榻老城,策对新都”的沈先生的。旧城们不是没有染指过这新城地面。
不过这次,不同以往。
“卷儿?”胡姐姐在下面叫了。
卷儿一回神,应了一声。
“今天还有新人来么?除了昨晚上来的那个?”
“没有了,而且昨晚上来的那个男人,今天也没有出现过。那两个最年轻的,今天出去,到现在也没有出现。”
“最年长的那个呢?”
卷儿愕了一下,这怎么答呢?
“他在晒太阳。”
凉亭中间没有声音了。
卷儿在这凉亭顶上,眺着这一区所辖的钢筋水泥。
原来是真的,那暴雨来前,真真是愈加的平静呢。
颜仲的身形顿住了,在距离“浴海”大门只有三米的地方,顿住了。
戛然而止。
因为一个头发白尽了的老头子正挡在他的面前。
这是海老王,颜仲心里知道,这“浴海”的地主,这“陌上桑”是他手下放着的。
“你是颜仲?”海老王问道,声音比他与甘笑儿说话时还要平静。
越是危险,越是平静。
所以这眼前的男人,比及刚才咄咄逼人的甘笑儿,是还要危险上几分的。
这个人身上带伤,眼中却也蕴得有刺,那一身的锋利,令海老王也不敢迫得太多,受伤的野兽,才最会攻击。
“我是颜仲。”
就像是都在等待这一声答应一样,全场在那最后一个字落地之时,竟然都不自禁的暗暗呼了一口气。
抑或是,偷偷的吸了一口气?
勾函的双眸抬了起来,这一抬,抬得他身边的左然都觉得一片粲然。
这就是声名吧!
一个传奇故事,不只能震慑场内,更引那后来之人一身热血。
勾函觉得自己的掌心,更加的暖了。
颜仲似乎感到这场中突如其来的那么一点共鸣,但他没有太多时间去细细的品味这点带这些倾慕的共鸣。
他的双眼略略的扫过众人,最后停在海老王的脸上。
“我要走了。”
海老王笑了,是真正的笑了。
不是觉得可笑,是有种像是开心的东西,在他那老谋深算的心底,发芽一般,冒出来了。
“拿了别人的东西,还是给个交代的好吧。”
那老迈的声音中间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声调,只是在这一语同时,那一边的二十多个人都围拢过来,把颜仲圈在了中间。
有人锁住了门,有人把厚厚的重帘放下来,挡住了一开始勾函劈开的地方。
夕阳要淹没在山巅云尽处了,“浴海”的大厅,提前暗了下来。
卷儿说得不对,那矮房之前,除了九太岁和阿洛之外,小隼和冬林也没有离开多远。
茂密的树丛之中,每天,他们两个都会就着犄角之势踞守。
尤其颜仲应先生之请,去了“浴海”之后,局势在某种局面上说,已经单纯了起来,他们的目的很简单了。
协着九太岁,一同阻着那个人下山。
一同阻着那个人入世。
沈先生说了,这锅水,不能搅得再浑了。
“胡姐姐,我们要看的到底是什么?”燕胡让卷儿从凉亭的顶上下来休息一会儿,卷儿却是没有疲累的样子,到地便问。
燕胡抬起头来,瞧着这新来的小弟弟,微微笑了一下。
她只有二十七八的样子,清秀脸庞,皮肤稍有些黝,眼睛很大,虽没有妇人的*体态,细薄嘴唇抿笑间却也难掩别样风采。
“我们要看着这些人,看他们弄出些什么阵仗来。”
卷儿有些不解,“我们只是看么?”
“只是看。”
“这已是我们‘府卫’的地头了,就算那个领头的真如姐姐所说是个一流角色,至多不过是请谈大当家他亲自来一趟好了吧。”
“问题不在这里”,燕胡轻声道,“这帮人走在哪里,都是要弄出些阵仗来的,只在于那阵仗是大是小。这些天看下来,他们到这里,所为的不过是另一个人,所以,我们只需要看看就好。”
“那就是小阵仗了?”
“阵仗大小,不能以人数多寡来算的。这次的际会,绝不会是个善罢的局面,我们只是看,也因为这些事情,已经不是太好管了。”
“可是谈大当家···”
燕胡一抬手,示意卷儿不用再说。这年轻的兄弟,对自家的领袖,倒真是崇敬非常呢。不过。
“九太岁是惹不得的,‘枕戈’是惹不得的,沈先生是惹不得的。那个他们将要对付的人,更是惹不得的。所以,我们不能动。”
卷儿真的吃惊了。
“黑道之中,居然有比沈先生更厉害的角色?”
燕胡沉吟了片刻,才道:“论艺业,黑道之中,怕是无出沈先生其右者了,但这个人令人忧,不只在艺业一道,他一旦要搅进这阖城局面,就是连沈先生也不想面对的。”
“这人是谁?”
燕胡却没有立刻回答他。
“卷儿,你可知道‘枕戈’为什么会叫个‘枕戈’?”
“这是暗合了沈先生的姓氏的”,卷儿答道,“那个‘枕’,就是沈先生的‘沈’字化来的。”
“不错”,燕胡颔首道,“不过人们一向以为,沈先生名字中化的‘枕’字一过,剩下的‘戈’字就纯是个搭配了,这就错了。”
“胡姐姐的意思是那‘枕戈’中的‘戈’字也是有来历的?”卷儿讶道。
燕胡的嘴角一翘,道:“那个‘戈’,就是此次九太岁一行,要对付的人了。”
俱散的气息有点乱。
很奇怪的乱,打滚道上,什么样的场面都是见识过的,但只是稍微一斗,这气息就乱的情形,却是没有出现过的。
俱散心里清楚,他与这顾融,也就是在伯仲之间,两相抗手,若是连这点气都运不匀,就失了先手了。
顾融那阴郁的脸上,挂着的是一种似笑非笑的谑意。
俱散的心头就这么一颤。
其实,他已经是失了先手了。
这个先手,失了,也已经有许多年了。
俱散知道,平心而论,顾融当年赢他,是赢得侥幸的,那胜败的一招,若以俱散全心来系,绝对不该是问题,可是,他败就败在,他难以会心一战。
若是只有顾融一人还好,谁想大公子也会在其中,而且,在那紧要关头,大公子还出了手。
俱散就败了。
这几年来,俱散一直在思索那一招的解法,其实那一招的解法在两相争斗时自然而然就续得上来。可是单单的这么一想,还真是没有半点法子。
那一役败得太惨,所以,这一个人、这一招在俱散的心头,已经不是单纯的技击拼斗那么简单了。
那已经是一个结。
若要把这个结解开,还需要这系上结的人。
而且,要在那拼斗之中,忘却那昔日败绩,忘却那败绩所附的惨,平平静静,自自然然的将那未尽一战续上。
待那一招过后,这个结才算是解得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