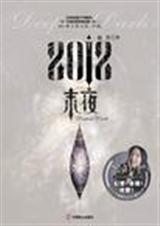流浪监牢20年-第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流浪监牢20年》(人渣录1…10)
一 高考之后
二00三年九月,我大约十七岁的时候,离开湖南到南京求学。一年半之后,我退学去了北京。如果说从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是流浪,那么这恰恰说明流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比如我从未离开过中国,——那么我从未流浪过。事实上,相对于我家那栋百来平米的房子,我一直在流浪,比如在网吧里,在酒店中,在从某地到某地奔走不停的道上。
大概从高考后,我开始较多饮酒。如此流浪是动态,而酒是常态。当时从高考结束到大学开学有三个月时间,在这三个月里,我和一帮有男有女的哥们作息时间如下:
下午5:00,吃早饭,三箱啤酒。
然后去上网,或在大街上瞎逛。
凌晨1到2点,在某个夜宵店吃午饭,啤酒不限。
上网、瞎逛至7、8点,回家睡觉,下午3点起来,做些活动比如押金花,然后去吃早饭。
三个月后,我们各自奔不同的道,往自己该去的地方去。我考入南京师大历史系,入住仙林校区,清一色的白房子,绿草地。早听说此处美女如云,——那没错,只不过云是动态的,变幻莫测的,或者红霞满天,或者乌云遍布。我独自拖着箱子在校园里游荡了四个小时,见到了无数乌云,正值满怀失望之际,在通往院办公室的电梯里遇见一个美女,漂亮且年轻。之后我发现此人是我们的辅导员,姓开名云。这是我今生第一次发现:世间还有“开”这个姓。后来我和大学时同级同院不同班的哥们小群用“开”组词,诸如此类:
开火,开包,开房,开妈,开炮
满是卑鄙猥亵之意。由此可见:我们是一帮卑鄙无耻下流的人渣。
二 圣诞
没念大学之前,我无所谓聪明,无所谓愚蠢,只是贪玩,比如踢足球,赌博,打电游,上课睡觉,和漂亮的女孩子瞎扯,等等,另外还有本能的厌恶与反感,或者说也有一些无知。入读大学历史系之后,我感觉并证明了有人想用瞎话把我灌傻。
到北京之后,我躺在地下室里念赵世民的《汉字·中国文化的基因》,其间《智·越喝越渴智慧海》中有一句:
“是做个快乐的猪,还是痛苦的智者?”
在南师大念书时,同学、室友、酒友、同乡(同为湖南人,我在怀化会同,他在益阳南县)老黄是我最好的哥们。我们第一次酩酊大醉是在O三年的圣诞节全班聚餐,我们几个湖南佬坐在一块。我和老黄空着肚子在一个小时内干了十三瓶,我七他六,期间各自有两瓶是一口气吹掉的。当时的场面有点痛快淋漓、惨无人道,据第二天在场观众的描述,老黄走出酒店之后便已神志不清,连连把脑袋往墙壁上撞,——他以为前面是路,而不是墙。观众们把他架到车上送回寝室门口,管理站的不让进,说是清醒了再说。结果老黄瘫倒在地开始口吐白沫。估计站长是怕出人命,赶忙打120把老黄送进医院。医生猛开了一通药,其中包括治淋病的,花了老黄两百六。——此事第二天老黄迷迷糊糊爬起来时才发现,——当时他浑浑噩噩下了床,拿起桌上一包药看了半天,猛然间醒悟过来,大叫:
他妈的老子正奇怪怎么花了两百六,老子只是喝醉了酒,他妈的连治淋病的药也给老子开了!
我说:你留着吧,以后用得着。
接下来该谈我酒后的表现:当时老黄已经被架出去了,我又摇摇晃晃一屁股坐到其他酒桌的席位上,——之所以选中此桌,原因是其间有一漂亮的姑娘。当时我又喝了几杯,——估计还说了几句难听的话,然后情不自禁唱起歌来,歌名为《同桌的你》,老狼的。我自以为很动情,唱得很投入很哀伤,但事后我估计同桌的人当时都有一股一刀把我杀了的冲动。随后有人说我喝多了,要把我送回去。在我“我还没醉”的瞎嚷声中,江苏盐城一哥们叫大东的架住我往外走,后面有人说大东辉辉就交给你啦。此时我突然挣脱大东,一溜烟跑了。事后有人说:你小子喝多了以后别乱跑,没人追得上你。我摇摇晃晃进了寝室,倒在床上大睡。然后突然直接在床上吐了起来,搞得一片狼籍。
同寝室的老李第二天对我说:昨晚大东忽然冲进来,红着脸粗着脖子喘着大气说:不好啦,你们寝室的辉辉,喝多了突然跑了,快去找!当他们匆匆忙忙往外跑,刚要出寝室楼管理站时,却见我摇摇晃晃一路走来。于是我开始琢磨一个问题:我挣脱大东后全速飞奔,按说该比大东早到寝室,怎么大东会赶在了前面?后来我终于想了明白:当时我钻进草丛里睡了一小会儿。
此事让我与老黄声名大噪,成为闻名一时的酒鬼。之后我们常在一块喝酒,至少一周一次。
三 老黄
在南师大的两年里,我的作息时间一般如下:8:00,去图书馆看书;6:00,回寝室找老黄喝酒,或找其他哥们比如小宝、小群,或者自己一个人单喝;11到12点,睡觉。
老黄这人比较清醒,不是*。这也便是我俩深交的原因之一。喝酒之际,我们经常说些反动的话,每一句都够我们给判上十年。地点多半是寝室楼旁边一小摊,羊肉串,十瓶啤酒。有时也喝白酒,一人半瓶,牌子多半是四块五的沱牌,或者二锅头之类,其他喝过的牌子已不记得。偶尔带上隔壁的小宝。此人念西方自由主义的东西比较多,为方便与之瞎扯,我也常找来看看。小宝理所当然是个反动分子,只不过隐藏在人民群众内部,而且胆子特小,每每说到反动处,便食指贴唇,“嘘——”,一副怯弱怕事没出息扶不起的阿斗模样。这点让我和老黄特不屑。尤其让我俩愤怒的是,此人喝酒特不爽快,一次最多喝一瓶。
大学时代我和老黄没谈过女朋友。我的原因是:沉迷于图书馆,没时间,且觉得没什么意思。最重要的是,一般来说,江苏的女的都非常小气,庸俗,虚伪,世故,装逼,没有大脑,令人恶心。老黄的原因则是:容貌凶恶,像土匪,给人的第一印象就不好,往往吓坏了人家女孩子。
来北京后,我和老黄在网上第一次聊天的记录大抵如下:
我:兄弟好啊。
老黄:兄弟好。
我:你他妈的还没做鸭啊?
老黄:操你妈你才做鸭呢。
我:你那副德行,不做鸭能行吗?对得起党和人民吗?
老黄:我操你妈!
四 小唐与大薇
来北京后的第三个月,我住在交大南门附近的一地下室里,一副穷困潦倒的模样。空气潮湿且闷热,怪味难闻。某日高三的两学生,大唐和大薇请我和一哥们喝酒。此哥们是我在*上认识的,ID名流浪狗,简称小狗。此前我和小狗已喝过一场,所以和那两姑娘没喝多少,就已有些神志不清。酒桌前,我大谈自己可怜的身世与际遇,估计博得了俩姑娘的同情。随后我趁着酒兴写了好几首打油诗,一首给小唐,一首给小薇,一首给小狗,一首给自己,一首给大家。然后我搂着小唐从交大西门逛到气象局,期间说了许多平时打死我也不会说的肉麻兮兮的话,之后大多已不记得,偶尔突然想起一句都恨不得把自己杀了。
当时我搂着小唐,小唐说:你别搂我,让我搂你好吧?我说行。于是她搂着我,我顺势挽其手,搂其腰,其状态*堕落有如八旗子弟。可以肯定我抒情的话说得特别多,因为我依稀记得小唐义正词严地说:我是写情诗的,这些我见得多了。
第二天我清醒过来后,在地下室认真地作出总结:没喝酒时,我从来不敢对女孩子动手动脚,不敢说一句肉麻的话,不敢牵任何女孩子的手,包括高中时代的两位女朋友。喝酒之后,我开始变得像西门庆,或者琼瑶笔下的男主角。五、六瓶之后,如果身边有女孩子,我很可能会牵住其中之一的手逛一整条街,此情形不下十次;如果身边没有女孩子,我多半会直奔电话厅,狂打电话,对象通常是爱过我或我爱过或彼此爱过的女孩子,说我爱你我其实一直没忘记你我一直很想你之类。这些话通常让对方感动万分,而我只记得不多的一部分。
其间有两件事尤其荒唐,每次回想都恨不得跳楼自杀,不过最终还是没有跳。一是在湖南会同时,我一最好的哥们,名叫鸭毛。某日酒后,我们找到鸭毛以前的女朋友,说去散散步。此女孩特单纯,便高高兴兴跟着去了。到了某个僻静无人之处,我一度大摸其乳房。正当我摸得兴奋之际,忽闻啪的一声,大约是挨了一耳光。我听见她说:
“算我看错人啦!”
后来我想:她这话说得挺有内涵。原本她以为我是一个好学生,翩翩才子,品格善良正直,心无二念,几乎是个太监,却没想到我是一个见色起意、无恶不作、调戏邻家少女的色狼。所以说她看错人了。我也觉得我错了。我也觉得我什么都好,就一点不行,色。这就像武侠小说中某高僧犯了*,便痛苦万分大彻大悟感慨万分地说:可惜,我这一辈子虔修苦练,却始终无法参透,一个“情”字。
作为回报,高考之后的那个暑假,我把以前的一位女朋友带到我家玩,让鸭毛与之“培养感情”。这类似于创办了一家论坛,给大伙一个交流的平台。谁知鸭毛将我房门一关,开始霸王硬上弓。此姑娘连呼我名字。我想:我成了人家的救命稻草,万不可辜负人家的希望。于是开门说:鸭毛,你在干嘛?
一年之后,我和鸭毛向俩姑娘道歉,和好如初。措辞是不好意思那时候我们年纪小不懂事并且喝多了之类。
五 地下室
二OO三年九月之前,我一直生活在湖南西陲的一个小镇,憧憬着大学里闲适而自由的生活。进入大学之后,我日渐发现:这不过是一种束缚转为另一种束缚,由一座监牢转向另一座监牢。后来我终于来到了北京。我在湖南憧憬南京,在南京怀念湖南,在北京追忆湖南和南京。
湖南的小镇山清水秀,小街直通南北,走一遍只需不到二十分钟。这为我省了不少车费钱。在南京,我住的大学城离市区坐车需半小时,我便懒得去,故而也省了不少车费钱。在北京,我居无定所,四处游荡,同样省了不少车费钱。车这种现代化的东西似乎与搞文学的气质上格格不入,骑马和坐车感觉完全不一样,至少马嘶给我的听觉冲击很好,而汽笛令人心烦。遗憾的是我没有马,只好步行。
我住地下室的时候,隔壁有个山西运城来打工的小伙子,叫阿祥。阿祥说他干过传菜生、网管之类,如今闲着没事干。他的梦想是四处流浪,体验一番,然后回家乡。当我说到我当时是靠写东西赚酒钱时,他说他也写东西,以前上学时还写过一两万字武侠。不过现在都混成住地下室了,写东西什么的,还是算了吧。我说我也住地下室。他便说他的确也想写个长点的小说,叫《混》,或者《跟我流浪》。于是我们要了点啤酒胡侃起来。当我说到人的种种权利时,他或黯然或苦笑或自嘲地说:我什么权利也没有,只有帮人家打工的权利。凌晨三两点时,我们都感觉得出去走走,于是离开那个活死人墓,光着上身在街上游荡。
此时街上冷冷清清,两边的大楼仅零零星星数家灯火,小店仅一家开着,除了躺在道上或天桥上露宿的人外,行人全无,除了我和阿祥。我们看到密密麻麻品牌不一的小车,除桑塔纳外,全不认识。我说,北京有两类人,一类有房有车有钱有女人,一类没房没车没钱没女人。阿祥对此深表赞同,说我们属于后一类。我说:我们曾经有过或终有一日会有车,比如自行车。此时一穿得很少的漂亮姑娘迎面而过。阿祥说:瞧,这不就是车么。
此后我们开始研究搞破坏的问题,比如在车轮下装几个钉子,一倒车就“嘭”一声爆胎,再也开不动。或者用玻璃刀把玻璃划破,再爬进去把车开走。此时我问:阿祥你会开车么?阿祥说:第一,光把玻璃划破了没用,得有钥匙才能开走。第二,开车他不会,让车开不了他会。后来他又说:瞧我们的脑袋里,成天都想着些啥哟。
三天后,他流浪去了郑州。此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他。
六 阿祥
关于阿祥,有几件事需要补充。首先是有关梦想。当时我大谈对未来的憧憬:回湖南农村养几只猪,几百只兔子,再买一匹马,天天骑了它去市集卖猪卖兔子。偶尔去县城中学摆一地摊,专门出售自己写的书。同时要请高中时的同学小马用毛笔写两块牌子,如下:
一,招魂,原名李建辉,1986年6月生,湖南会同人,在会同一中念中学,2003年9月考入南京师大历史系,05年4月退学去北京混。喜欢瞎逛,以阅读、写作、香烟、啤酒为生。
二,此地出售的书籍皆为本人所写,每本十元。以此为生,生人熟人一律不还价,还请见谅。
同时我衣冠不整或干脆光着上身歪坐在地,脚踏木屐,嘴叼软白沙,和一帮老朋友或刚认识的新朋友喝酒,并且一头长发。
阿祥的梦想捉摸不定,时而是流浪,时而是写本《跟我流浪》,其终极梦想则是:去内蒙古的大草原上牧马放羊。我为他补充了一点:带上一个漂亮的姑娘。之后他去了郑州,此梦想相对于在北京,不是更近,而是更远。
其次是地下室与漂亮的姑娘。由于我与阿祥住在地下室的最深处,每次回房都要经过地下室的所有房间,故而对地下室里住的所有漂亮姑娘一清二楚。阿祥甚至还告诉我:哪间房有三个漂亮姑娘,且睡觉从不关门。我说:此地的漂亮姑娘,只怕多半是性工作者。阿祥说:何以见得。我说:昼伏夜出,且一个个像是比赛谁的衣服穿得少。阿祥说:有道理。我说:上次去厕所,见一女的,几乎是在勾引我,——仅披一件薄纱,基本上属于100%透明,能清楚地看见其黑色的*,阿祥说:哇——你观察得真仔细。我这辈子还没见过女人的*。我说:那你真是吃亏了。干脆就在这找个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