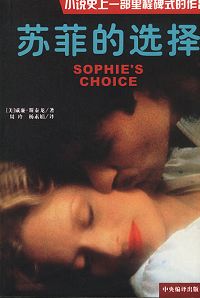苏菲的选择-第7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他出来干嘛,直到几百码远苏菲的窗口传出的“经典”音乐才将他唤醒。那乐声变得异常响亮,仿佛全是号角声。他想起了他的使命,苏菲还在等他呢。他赶紧一路小跑往回赶,在卡顿大街差点撞上一辆卡车。当他走近房子时,音乐声更大了。他想他或许可以尽量委婉地提醒她放低音量,但他又想,现在是白天,而且是星期六,别的房客又都不在,不会有什么妨碍的,让它去吧。
他敲了敲苏菲的门,没有反应;他又使劲敲了敲,还是无人应答。他把酒瓶放在门边的地板上,然后下楼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他在那儿欣赏自己收集的火花。莫里斯是个收藏迷;他的房间放满了各种各样的软饮料瓶盖。大约半小时后,他决定像往常那样小睡一会儿。等他醒来时,已经是下午四五点了,音乐声已经停止。他说他当时就有一种不祥的感觉;他的理解力似乎因闷热而变得有些迟钝,就像这即将沸腾的粉红宫在没有一丝风的空气中停滞不动。他热得浑身大汗。房子里突然变得异常安静。公园远处的天际线上,炽热的阳光迅速移动,西边传来沉闷的雷声。在静悄悄的开始变暗的房里,他又来到楼上,那瓶威士忌还在门口放着。莫里斯又敲了一阵门。年久失修的门扇轻轻动了一下,露出一条缝,但门是从里面闩上的;透过门缝可以看见插得死死的门闩,于是他知道苏菲没有离开房间。他叫了两三声她的名字,仍然没人答应,四周一片寂静,他的困惑渐渐变成焦虑。他朝里窥视着,发现房间里没有亮灯,这时天已全黑了。于是他决定给劳瑞打个电话。医生在一个小时内赶到了,他们一起把门撞开……
与此同时,我在华盛顿的另一间小房间里热得发昏。我做出一个对事态的发展不可能产生任何影响的决定。苏菲先于我六小时离开了华盛顿;即使这样,如果我不耽误时间马上尾随而去,或许能够及时赶回布鲁克林,扭转事态的发展方向。但我恼怒,痛苦,出于某些我至今仍不完全明白的原因,我决定独自一人回南安普顿。我想我的决定里一定有“恼羞成怒”的成份:为她的背信变节而气恼,同时被嫉妒刺痛得发狂,以至我得出一个痛苦的结论,她只会照料那个傻瓜——内森,那个疯子!我已尽了全力。让她回到她那个犹太疯子情人,那个狗杂种身边去吧。于是我清点了一下已大大缩水的钱包(很具讽刺意味的是,我仍然依赖内森的馈赠维持生活),带着强烈的反犹情绪从旅馆结账退房,冒着酷热,步履艰难地走了好几个街区来到汽车站,买了一张去弗吉尼亚弗兰克林的长途汽车票。我决心忘掉苏菲。
这时已是下午一点。我没有意识到这点,深深地陷入危机之中。恶毒的背叛,巨大的失望,深深地刺痛了我,使我的身体像患了跳舞症似的,手脚颤栗不已;还有,宿醉像酷刑似的袭遍全身。当汽车轰鸣着驶过拥塞的阿林顿大街时,我浑身剧烈颤抖,心情十分沉重,这多半与苏菲给我灌下的威士忌有关。我从没见过自己的手指无法控制地剧烈颤抖,以致连烟都点不着。再加上那噩梦般的一幕,我沮丧到了极点。阴沉的郊外,高墙环围的监狱,流淌着粘乎乎污水的宽阔的波托马克河。我小的时候(离现在并不太久),华盛顿特区的南郊还是一片田园风光。我的上帝,看看现在!我忘了我的家乡已经历了一场磨难,被战利品充斥得满满当当的,费尔伐克斯县污秽肮脏的城市形象像脑中的幻觉一样一闪而过,钢筋混凝土到处都是。仅仅在一天前,我还以为我永远不会再看见它们。这一切都是北方佬蔓延到我亲爱的家乡的恶性肿瘤吗?往南方走肯定会好一些;但此时我却不得不把头轻轻靠在椅背上,在疲惫、恐惧和痛苦中备受煎熬。以前我从未体验过这种感觉。
司机高叫一声:“亚历山大。”我知道我必须下车了。我心里琢磨着,如果这些地方医院里的实习医生看见一个皮包骨头,穿着皱巴巴的条纹西服,神情恍惚的幽灵要求穿上紧身衣,会怎么想?(难道就是在那时,心里有个声音告诉我,我不可能生活在南方?我想是的,但迄今为止我仍无法确定。)
但我总算控制住了自己,把脑子里的妖魔鬼怪统统赶跑了。在搭乘了一连串的交通工具(包括一次出租车,这差点让我经济崩溃)之后,我终于及时赶回联邦火车站,乘上三点钟开到纽约的火车。直到我坐在闷热的车厢里,我才让自己想苏菲。仁慈的上帝啊,我倾慕的波兰姑娘正在奔向死亡!我突然发现,我之所以在未能完成的弗吉尼亚之行中将苏菲从脑子中完全赶跑,只是因为潜意识阻止我预见或接受这一预感:可怕的事即将发生在苏菲和内森身上,而我迫不及待地赶回布鲁克林也无法挽回他们的命运。并非因为我有先见之明,而是我故意视而不见,或是装傻,或两者都有。她最后的字条没有流露出什么吗?上面再明白不过了,六岁的孩子也能体会它的含义。是我的疏忽吗?我为什么不紧随她而去,而是乘上那辆愚蠢的公共汽车去穿越波托马克河。我痛苦得无法言喻。我对她的内疚一如她对她孩子的内疚。我本可以不让她走上死亡之路的,可我却没有这样做,这与内森亲手杀死她有什么不同?我痛苦不堪,内疚万分。我对自己说:上帝啊,电话在哪儿?我要抢先警告莫里斯·芬克或劳瑞。但这时,火车启动了,我明白我无法再与谁联系,一直得等到……
于是我陷入一种短暂却相当强烈的稀奇古怪的宗教情感中。《圣经》早已成了我许多年来四处巡游的一部分行装,我把它与《时代》杂志还有《华盛顿邮报》一起随身携带着。当然,它还得充当恩特维斯特尔牧师的必备之物。我从来不是一个信神的人,《圣经》对我的意义主要在文学方面。它提供想象,隐喻,为我小说中的人物提供大量画龙点睛的引语。我自诩为一个不可知论者,不信神,不受宗教的束缚,即使在遭受巨大痛苦时,也敢于质疑诸如神和上帝之类虚无缥缈的脊椎动物。但我坐在列车上,孤独,无以形容、无法排遣的虚弱和恐惧,我的精神支柱一下子垮了,《时代》和《邮报》也不能为我排解苦闷。一个奶油色肌肤高大肥胖的女人挤在我身边的座位上,一下子把这地方弄得满是香味。我们正朝北驶去,刚离开哥伦比亚特区。我转头看看她,因为我感觉她正盯着我。她用那双柔和,充满关切的圆圆的棕色眼睛打量着我,微笑着,喘了口气,神色间充满我渴望已久的母爱的慈祥。“孩子,”她说,充满信任和鼓舞,“这是惟一的好书。就是你手上拿的这本。”彼此的信任就这样建立起来。这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从旅行袋中拿出她自己的《圣经》,坐在座位上愉快地看了起来,湿润的嘴唇不时发出咂咂声。“相信他的话!”她提醒我说,“你就会得到拯救——这就是圣书和主的真理。阿门。”
我回答说:“阿门。”我打开《圣经》,一页不差地翻到最中间的一页。少年时代在教会学校的课本中学过的那首《赞美诗》就印在这一页上。“阿门。”我又说了一遍。“像糜鹿渴望清泉,我的灵魂向往着您,啊上帝……”突然我觉得我必须躲开所有人的眼睛。我歪歪倒倒地走进盥洗间,锁上门,坐在马桶上,飞快地在笔记本上划下一些有如天启般的语句。这些语句涌出我混乱的意识时我并不真正明白:这是一个即将消逝在这世界上最遥远最恐怖的孤岛的罪人的最后忏悔,他匆忙写就放进瓶中,任其在黑暗的永恒的海底飘浮。“你为什么哭了,孩子?”当我回到那妇人身边时,她问,“是谁伤害了你?”我无言以答。但她马上提了一个建议,于是不久后,我便和她一起朗读起来。我们把声音提得很高,协调而悲伤的挽歌压过了火车的哐当声。“《赞美诗》第八十八,”我建议道。她回答说:“一首很不错的赞美诗!”“啊上帝我的救主,我日日夜夜呼唤着你,让我的灵魂来到您身边……”我们高声读着。读完了威名顿,切斯特,翻到了基督和以塞亚。过了一会儿,我们试着读《登山训众》,但它对我一点不起作用;希伯来老奶奶的悲歌更加深了我的悲哀,于是我们又回到《约伯纪》。最后,我抬眼看看窗外,天已黑了下来,我已喜欢上(如果不能算爱的话)的这位黝黑的女布道者在纽阿克下了车。“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她预言道。
从外面看上去,那天晚上的粉红宫就像我看了不下一百遍的粗制滥造的侦探片的外景地。直到今天,我仍能清楚地记得我从人行道上走过去时的那种认命的感觉——我不愿感到惊讶。一切都如我的预料:救护车,消防车,闪着红灯的警车,等等——一大堆车聚集在那里,仿佛这所破旧不堪的房屋遭遇了一场大屠杀,而不仅仅是两个年轻人自愿而严肃地在此了却一生,永远睡去。一盏雪亮的探照灯把这里照得如同白昼,周围用路障围了起来,竖起“禁止穿越”的警示牌。到处是嚼口香糖的警察。我和其中一名警察,一个丑陋暴躁的爱尔兰人吵了起来,告诉他我应该获准进入。但如果不是劳瑞,我可能要在外面呆上好几个钟头。他看见了我,对那一脸肥肉的家伙说了几句什么,我才得以进去,穿过过道,经过我自己的房间。我房间的门半开着,耶塔·齐墨尔曼正半躺半坐地蜷在一张椅子上,神色恍惚地用依地语咕哝着什么;那张幽默亲切的宽脸此时没有一点血色,显然惊吓过度。一个护士在她身边摆弄着注射器。劳瑞一言不发地把我带到楼上,经过一群满脸肃穆的警察、记者和两三个随着准备对任何一个活动物体举起闪光灯的摄影记者。整栋房屋弥漫着浓烈的烟雾,有一瞬间我还错以为这里失火了。在苏菲的房间门口,莫里斯·芬克正用发抖的声音向一名侦探模样的人诉说着什么,他的脸色甚至比耶塔还要苍白。我等了很久才和莫里斯说上话。他把那天下午的一些事,还有音乐的事告诉我。最后我终于来到苏菲的房间。在那扇被撞破的门后,一片温馨的珊瑚红色出现在眼前。
我在昏暗的光线中眨着眼睛,然后慢慢看清苏菲和内森躺在铺着鲜艳的杏黄|色床单的床上。他们身穿很久之前我第一次碰见他俩的那个周日的衣着——她穿着那套活泼的旧式服装,他则穿着那件宽条纹,艳丽俗气,有着时代错误的灰色法兰绒衣服,看起来像一个赢了大钱的赌徒。虽然衣着如此,可他们躺在彼此的怀里,拥在一起,显得异常安宁,就像两个相亲相爱的人穿戴整齐后,正在像以往那样去午后散步,但突然一时冲动决定躺下休息,或者亲吻,Zuo爱,或仅仅是说说悄悄话,便一下子僵住了,将这温柔的拥抱永远延续下去。
“如果我是你,就不去看他们的脸。”劳瑞说道。他顿了顿,又说:“不过,他们并不痛苦,服的是氰化物,只须几秒种。”
我感到膝盖发软,差点跌倒,劳瑞一把抓住我。我赶紧站好,想走进门去。
“医生,他是谁?”一个警察问,一边走过来拦住我的去路。
“家庭成员。”劳瑞说,他说的是真话,“让他进去。”
房间里没任何变化,没少什么也没多什么,只有他俩躺在床上。我不忍心去看他们。我的眼光尽量避开他们,朝那台留声机走去。它已经关上,我看见那天下午苏菲和内森放过的那摞唱片,蒲塞尔的《小号琴》,海顿的大提琴协奏曲,《田园交响曲》,格鲁克《奥菲欧》中的悲悼欧里狄塞——这些是我从唱机上取下来的十多张唱片中的几张,其中两首乐曲的标题对我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我知道它们对苏菲和内森也有着同样的意义。一张是莫扎特的钢琴协奏曲——他的最后一首曲子。我和苏菲在一起时,她曾无数次地放这首曲子,每次她都躺在床上,一只手掩住眼睛,听着那缓慢、甜美而忧伤的旋律弥漫整个房间。莫扎特写这首曲子时已不久于人世;这是否就是(我记得她也曾十分困惑)这首乐曲充满近乎快乐的认命和解脱的原因?她说,如果她有幸成为一名钢琴家的话,这将是她要牢记在心的第一首曲子,她将感受这“永恒”的声音的每一个细微之处。那时我一点不了解苏菲的过去,也不懂她说的这些。当时她停了一下,又说:每当听到这乐声,她总会想些在黄昏中玩耍的孩子们,落日的余晖将草坪笼罩在一片阴影之中。
另一支是苏菲和内森整个夏天都在听的曲子。我不想过多谈及它,因为苏菲和内森都已不在了。这张唱片正好放在唱盘的上面。我取下它,忍不住想,在他们最后的极度痛苦或极乐,或无论什么类似的词儿吧,总之在他们临终之前,他们听到的最后声音是耶稣,是人类追求快乐的旋律。
这时,两个身着制服的殡葬人员拿着塑料袋走了进来……
我想,这最后的内容,可以称为“征服悲伤的研究”。
我们把苏菲和内森葬在一起,让他们并排永远躺在拿骚县的公墓中。这事办得比想象的更容易一些。因为我们曾担心过,这毕竟是一个犹太人和一个天主教徒的“自杀契约”(《每日新闻》第三版的报导是这样说的),一对未婚的恋人,悲剧的男主角精神异常,等等。这在1947年是十恶不赦之罪。你可以想象把他们合葬会招致多大的压力。但葬礼得以顺利进行(劳瑞安排了一切),因为必须遵从的宗教禁令并没有多少。内森和劳瑞的父母是正统的犹太人,但母亲已经去世,而父亲也八十高龄,早已老朽昏庸,再加上(为什么我们不能正视这一点呢?)除了内森,苏菲没有比内森更亲近的人。考虑到这些理由,劳瑞决定在第二天(也就是周一)举行葬礼。劳瑞和内森都已好多年没有进过犹太教堂。当劳瑞询问我的意见时,我认为苏菲不会想要牧师或其他神职人员来为她行宗教仪式。也许这是渎神的假设,会导致苏菲下地狱的,但我当时相信(现在仍然如此)我是对的。在来世,苏菲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