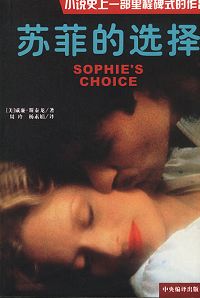苏菲的选择-第6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更接近他。我以一种浪漫主义的态度对待内森的重新出现,并完全接受了他,只是对他今后是否会复发感到轻微的忧心忡忡。显而易见的是,苏菲和我都是容易被打动的人。他重新回到我们的生活,把他那高昂的情绪,慷慨,生气勃勃,迷人,快活以及爱,又重新带给我们。这就足够了。我们曾以为这一切永远成为了过去。而事实却是,他又回到了粉红宫,重新在楼上筑起爱巢,似乎一切自然而然,以至于我到现在仍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将那些家俱、衣服、随身物品搬回来的,就像它们从未离开过粉红宫。
一切恢复了原样,仿佛什么也没发生,我们的友情和幸福仿佛从未被他的疯狂破坏过。时间已进入九月,夏日的暑热仍盘旋在大街小巷的上空。每天早上,苏菲和内森都在教堂大街的BMT车站搭乘不同的地铁上班——他到普费泽的实验室,而她则到布鲁克林商业区的布莱克斯托克诊所。我呢,幸福地回到那张小小的橡木桌前。我不再让自己迷恋苏菲,心甘情愿地再次将她放回到她本该属于且正属于的那个男人身边,心里再次承认自己对她的爱是微不足道的。没有了这些胡思乱想,我又怀着满腔热情回到被打断的小说创作中。当然,完全投入也是做不到的。苏菲的过去偶尔会钻进我的脑子里,但总的来说,我可以将她的故事从脑子中赶跑。生活仍在继续。我突然热血沸腾,强烈地感受着属于我的悲剧故事,这足以把我的时间排得满满的。此外,内森的经济援助也鼓舞着我,它无疑是一个艺术家能收到的最令人振奋的礼物。我开始以极快的速度工作起来,并不停地修改、润色,写秃了一支又一支维纳斯牌铅笔,黄|色稿纸在桌上堆起一大摞。
内森重又成为支撑一切的兄长般的支持者(除了钱以外),一个提建设性意见的友好的批评家。我崇拜的这个人又开始读我的作品了。每当我写完二三十页,他便把手稿带到楼上阅读,几小时后再还给我,几乎每次都把我最渴望的东西——赞美——带给我。虽然他会不时提出一些尖锐的批评(此时他通常表现得很为难),但我敢肯定,他被我书中那些阴郁的潮汐镇传说,用真情写就的场景和气氛,以及那些正穿行在弗吉尼亚低地送葬途上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完全迷住了。更确切地讲,我在书中竭力构筑的新的南方形象最终打动了他(尽管他已察觉到福克纳对我的影响,而我也欣然承认)。用他的话说,“像触电一般”。我暗自陶醉于自己那精妙的艺术炼丹术,觉得自己逐渐改变了内森对南方的偏见,他开始接受和理解了。我发现他不再对我使用那些令人生厌的字眼,如兔唇、金钱癣、私刑、乡巴佬等等。这一影响在他身上明显地表现出来,而且因为我对他的崇敬,他的这种反应特别令我感动。
“那种乡村的氛围真令人称奇。”他对我说。那是一个周六的下午,我们坐在我的房间里。“那位母亲和黑人女仆的对话——我不知道,好像觉得蛮像回事。还有南方夏日的感觉。我不知道你是如何写出来的。”
我心里一阵得意,口里咕哝着一些感谢的话,吞下一口啤酒。“这次进展相当顺利,”我说,心里意识到这句话蕴藏着的矜持。“我很高兴你喜欢它,真的。”
“或许我应该到南方去,”他说,“看看它什么样。你的东西刺激了我。你来当向导,那肯定很合适,怎么样老伙计?我们来一个南方之旅。”
我一下子兴趣盎然。“上帝,当然了!”我说,“那真是太妙了!我们可以从华盛顿启程。我有个老同学在弗雷德利克斯堡,他曾参加过南北战争。我们可以和他呆上一阵儿,参观所有的北弗吉尼亚战场遗址,曼纳萨司,弗雷德利克斯堡,荒野地战场,西尔维尼亚战场——所有的战时工事。然后我们乘车去里奇蒙德,参观彼德斯堡,再去南安普顿我父亲的农场,马上就到收花生的季节了……”
内森显然被我的计划所打动。我滔滔不绝地述说着我们的旅行计划,他则一个劲儿地点着头。我设计了一个严肃,富有教育意义,同时又不乏趣味性的漫长缓慢的旅行:经弗吉尼亚到达北卡罗来纳的海滨地带——那是我亲爱的老爸生长的地方,然后是查尔斯顿,无树平原,亚特兰大,和穿越南部中心地带,亚拉巴马,密西西比,最后在新奥尔良结束行程。新奥尔良的牡蛎又大又新鲜,每一个才两分钱,美妙的大杂烩,长在树上的喇咕。“这是多美的一次旅行啊!”我叫道,又打开一听啤酒,“南方的烹调,炸鸡,哈希小狗,花生加熏猪肉,克里特威士忌,科纳得青菜,乡村火腿加威士忌肉卤。内森,你这个美食家会幸福得发疯的。”
啤酒使我情绪高涨。那天天气异常炎热,但公园那边有一丝微风吹来,窗帘微微飘拂。我听见楼上传来贝多芬的乐曲声。这当然是苏菲所为,周六她只上半天班。她总是在冲凉时将留声机的声音放得大大的。我意识到我正像一个地地道道的南方人一样,浓墨重彩地描绘着南方的美景。其实我对他们的观点厌恶之极,对南方怀着与那些自由主义的纽约人几乎相同的憎恶感。这曾令我无比痛苦,但现在已经无所谓了;在整整一上午卓有成效的工作之后,那块魔力无穷的土地令我兴奋异常,描述它(我曾忠实而痛苦地记录下它的音容笑貌)带给了我一阵微小的狂喜和巨大的心痛。当然,我常常经受这种快乐与痛苦交织在一起的情感冲击(最近的一次便是我在莱斯丽身上的失败),但此刻,我似乎特别脆弱,仿佛随时都可能潸然泪下。第四交响乐柔和亲切的慢板从楼上飘下来,像脉搏一样坚强有力地跳动着,与我激动的情绪交织在一起。
“我必须去看看南方,老伙计。”我听见坐在我身后椅子上的内森说,“你知道,现在是我看南方的时候了。今年夏天你讲的那些事,仿佛已过去很久。你说的那些南方的事,或者应该说是北方与南方的关系触动了我。我们在争论我们常常争论的那些话题时,我记得你当时说了一些很有道理的话。你说,至少南方人已冒险来到北方,见到了北方的真相,而真正想了解南方的北方人却微乎其微。我记得你说,北方人在自己的无知中沾沾自喜,你说这是一种思想上的傲慢。这是你当时用的词儿,它们曾狠狠地刺痛了我,可后来我又仔细想过,开始明白你可能是对的!”他停了一会儿,接着真挚地说:“我承认那是无知。我怎么能仇恨我从见过和不了解的地方呢?你说得对,我们去旅行!”
“谢谢你,内森。”我回答说,心里充满感动与莱因戈德啤酒激起的真情。
我手里拿着啤酒瓶,走进浴室去小便。我比我意识到的醉得更凶一些,尿撒得到处都是。透过尿溅在池中的声音,我听见内森在说话:“十月中旬时我可以休假,到那时你的书也写得差不多了,大概也需要休息一下。我们为什么不那时去呢?苏菲也从来没有请过假,所以她也可以休假一二周。我可以借我哥哥的车,是一辆敞篷车。他又买了辆新车,所以不会再开它了。我们开车去华盛顿……”他说这话的时候,我的目光一直盯着药箱:被盗之前它一直是个很隐密的储藏所。既然莫里斯·芬克排除了嫌疑,那么谁是罪犯呢?我心里思忖着。附近总有一些贼在游荡。不过这事儿也无所谓了。我意识到,我先前的气愤与懊恼此时被一种奇怪复杂的不安情绪所替代,毕竟那被偷去的是一个人的卖身钱。阿提斯特!祖母的奴仆,我的资助人。这个黑奴男孩的肉体为我提供了足够的保障,使我得以在布鲁克林逗留了整个夏天,并完成小说的前面部分。或许神是公平的,阿提斯特不再纠缠于我,我的生存无须再与一桩罪恶相连。我为自己摆脱了它,摆脱了奴隶制而感到欣慰。
然而我怎么可能摆脱奴隶制呢?我心中一阵犯堵,低声地说出了这个词,“奴隶制”!我一直有种冲动,想写写奴隶制,将它从深埋之处挖掘出来。与它相关的任何事情每次都激起我的冲动。实际上我此时写的,正是那个制度的继承者们在四十年代,在弗吉尼亚的潮汐镇的疯狂挣扎,在我那亲切而令人痛苦的布尔乔亚新南方家乡的一举一动;此时我才意识到,那儿所有的一切都是从奴役中产生的。我们大家,无论白人黑人,在某种意义上不都是奴隶吗?我明白在我心灵深处某个最不平静的角落,只要我还是一位作家,就会受到奴隶制的束缚。突然间,通过一阵令人愉快的、懒洋洋的、略微有点醉意的精神漫游,我从阿提斯特想到了在麦卡阿尔宾酒店大声打鼾的父亲,又从父亲想到了那个穿白色长袍的黑人——在詹姆斯河泥泞的河水中接受浸礼的那特·特纳,强烈的思乡之情突然向我袭来,一阵痛楚像长矛似的刺穿了我的心。我从浴室中出来,脚步蹒跚,嘴里念念有词,声音很大,把内森吓了一跳。
“那特·特纳!”我说。
“那特·特纳?”内森迷惑不解地问,“谁是那特·特纳?”
“那特·特纳,”我说,“一个黑人。在1831年的暴动中,他大约杀了六十个白人——没一个犹太人。他住在离我家不远的詹姆斯河边。我父亲的农场正好在他领导那次血腥起义的那片土地的中间。”我开始向内森讲述我所了解的这个黑人令人吃惊的故事,以及他那些早已被人遗忘的神秘生活与举止。我正在讲述的时候,苏菲走了进来,她刚洗完澡,浑身清爽,煞是迷人,那张脸看上去非常甜美。她坐在内森椅子的扶手上,一边专心听着,一边用手不经意地抚摸着他的肩膀。但我很快便结束了,因为我发现我对这人了解甚少,没有多少东西可讲;他神秘地出现在一段历史中,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后,便如同来时一样不可思议地消失了,没有留下任何东西,没有身份,没有形象,只留下一个姓名。他应该被重新发掘出来。那天下午,当我借着酒兴试图向苏菲和内森讲述他的故事时,我第一次意识到我应该将他写出来,把他变成我书中的人物,为世界重塑他的形象。
“太妙了!”我听见自己带着醉意兴奋地大叫,“你知道吗,内森,我现在才明白,我应该用那奴隶的题材写一本书。我们的旅行正是时候。现在这本小说已写得差不多了,可以稍微停一下。我可以做一个全盘计划。因此当我们到南安普顿时,我们可以开车游遍那特·特纳的故乡,和人们交谈,参观所有的古老房屋。我可以感受那里的气氛,做很多笔记,收集资料。这将是我的下一本书,一本关于特纳的书,同时,你,还有苏菲,也可以为自己增加许多有价值的知识。这将成为此次旅行中最奇妙的部分……”
内森用手抱住苏菲使劲搂了一下。“斯汀戈,”他说,“我简直等不及了。十月份,我们就往南方进发。”他瞟了一眼苏菲的脸。他们交换着爱的目光——先是相遇,继而强烈地交织在一起,以至我感到很窘迫,赶紧把目光躲开。“告诉他吗?”他问苏菲。
“为什么不呢?”她回答说,“斯汀戈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不是吗?”
“也是我们最好的人。我们将在十月结婚!”他高兴地说,“所以这次旅行也将是我们的蜜月旅行。”
“上帝,天哪!”我欢叫起来,“恭喜你们!”我大步跨到椅子前,吻了他俩——吻在苏菲的耳旁,那股栀子花的芳香像针似的刺着我的心;吻在内森那高贵的鼻子上。“真是太妙了,”我喃喃地说。我确实是这样想的,早已忘记在刚刚过去的日子里,这样的狂喜往往伴随灾难同时降临。
大约十天或十天后的一天,也就是九月的最后一个星期里,我接到了内森的哥哥劳瑞打来的电话。那天早上,当莫里斯·芬克指着过道里那台油腻的付费电话叫我接听时,我大吃一惊——接电话本身已令我吃惊,尤其是这电话是我常听说但从未谋面的一个人打来的。那声音十分温和,可亲,和内森几乎一模一样,带着明显的布鲁克林口音,刚开始时很随便,然后渐渐严肃起来。他问我能否安排一次与他的会面,越快越好。他说最好不要让他到齐墨尔曼的公寓来,而是我到他在森林山的家里去一趟。他又说,我必须知道这事与内森有关,而且很紧急。我不假思索地答应了,于是我们约定在下午晚些时候在他那儿见面。
我在迷宫般的地铁站里完全昏了头,像无头苍蝇似的乱窜一气,结果乘错了车。当我到达时,已比预定时间晚了一个多小时。劳瑞十分友好地接待了我。在一片相当阔绰的住宅区里,的站在一套宽大舒适的住宅门前迎接我。还为有一个人能像他这样一见面就让我着迷。他比内森略矮一些,比内森更敦实,年龄当然也大一些。他俩长得很像,但差别也相当明显:内森神经质,易激动,不可捉摸;劳瑞平和,说话柔声细气,令人宽慰,这可能与他的职业有关,但我觉得更多地来自他那沉稳、刚直的性格。我正想解释迟到的原因,他却很快使我放松下来。他递给我一瓶加拿大裸麦酒,对我说:“内森告诉我说,你是一个麦芽酒的行家。”我们在一扇巨大的落地窗前的椅子上落座,可以看见外面掩映在常青藤下的建筑物。而他的话则让我产生如遇旧识之感。
“我想我不必告诉你内森对你评价极高,”劳瑞说,“真的,这也是我请你来这儿的部分原因。事实上,我想你们相识的时间并不长,但我相信,你或许知道他已经把你当成了最好的朋友。他对我讲起你的工作。他认为你是个很不错的作家。有一阵子,你知道——我猜他一定告诉过你——他也曾想过写写自己。只要有适当的环境,内森几乎可以成为任何一种人。我想你一定知道,他有很高的文学鉴赏力。我想你也一定知道,他认为你正在写的小说十分了不起,而且你的南方世界很打动人。”
我点着头,心里充满喜悦。上帝,我多么渴望得到这样的赞誉!但我对这次会面的目的还是摸不着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