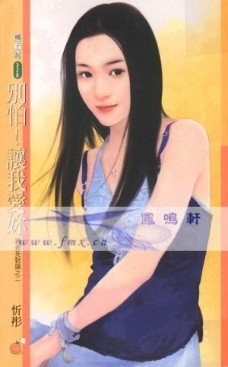永失我爱-王朔-第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本站所有资源部分转载自互联网!请支持正版,版权归作者所有!
按:王朔早期作品吧,婉约派的活儿。也算告诉他们不是只有琼瑶能感动初二女孩
儿。全篇虽多少有点大男子主义,不过有些场面也能看出渗着血。你爱过你才会懂,你经
过你才能感受
青山癫生
那天,报纸电视都预报是风力二三级的晴天,但当我们聚集到建筑工地的空场上时,天
瞬时阴了下来,并伴有不间断的狂风,工地上的水泥浮灰被吹得漫天飞扬,沙石打在一字排
开的载重卡车车帮上铿然作响。
我迷了眼睛,进了一嘴砂子灰了脸。空场旁插着的彩旗也在刹那间黯淡了。
似乎有无数的炸弹纷纷落在若大的工地上……
接着,成吨的雨水倾泄而下,灰飞烟灭,未建成的庞大厂房、恐龙般的吊车轮廓依稀呈
现,笼罩在一遍水雾弥漫之中。
人们抱头鼠窜,石静横穿混乱的人群向我们跑来,头发湿漉漉地贴在额上颊边,雨水流
进她大张的嘴,白色的牙齿一晃一晃,喧嚣的雨声使我一点也听不清她在喊什么。我们分头
爬上了各自的卡车。驾驶楼内十分闷热,并混杂着柴油味,不断流倘的水波使四处景、物、
人变得朦朦胧胧。我开动前挡风窗的雨刷,水被一层层刮去,前景忽而清晰,忽而模糊,两
旁的卡车都隆隆发动起来,石静在车下变成一团只具轮廓的人形,周围人影纷乱。我摇下边
窗,只见她已掉头一步步往回走,脑后的湿淋淋的头发散乱着象一团胡乱缠的黑毛线。
工会的小刘头带桔黄色的塑料安全帽,象名在敌前火力封锁下敏捷穿行的侦察兵一样,
弯腰冲刺出现在车前,一手拿着只哨子含在嘴里鼓足腮帮子吹了一下,一手擎着的小红旗猛
地往下一挥,撒腿就跑。
旁边的两辆车猛地冲出,待我反应过来,那未出现的哨音已淹没在哗哗雨声中,慢了半
拍。董延平的车已跑到了我前面并挡住了我的视线,铲状的车尾在我面前跳抖着,冒出股股
黑烟。
发动机的吼声盖过了雨声,方向盘象通了电似的震得人手发麻,车身大幅度颠簸着我,
象骑在马上。左右是一辆辆同样急驰的卡车和车与车间隙内一片片闪过的工友们的枯黄头
盔。我数次接近那同样桔黄色的车尾,又眼睁睁地看着它拉开距离--董延平有意遮住我的
路线,我向右打把他也向右打把。董延平的车尾蓦然增大,向我扑来,我向左打把,眼前蓦
地又出现小齐的车尾,近在咫尺,我只得紧踩煞车,他二人的车瞬时远去,与此同时,老吴
的车从我眼前呼啸而去,一排沉重的泥点訇然作响,横拍在我的前挡风窗上。
待我重新发动车辆,驶向终点时,董延平他们已稳稳地停在终点,大笑着从驾驶室里爬
下来,站在那儿冲我吹口哨。
我风驰电掣地冲他们驶去,开到跟前,一踩前闸,车身一下横了过来,高速旋转的后轮
刨起泥浆糊了他们一头一脸。
“报复是不是?”
董延平和齐永生冲上来,拉开门把我揪出来。
我被他们扭着,叫着挣扎说:“报复你们,怎么着吧?”
“灌你丫的。”
接着,我就被他们按进了一个泥水坑。
我被他们拉起,啐着泥水说:“有什么呀,不就是泥水浴么?”
“还嘴硬?”董延平又按我头。
这时,头儿们和石静打着伞笑吟吟地走过来。小齐嚷着:“领奖领奖,前三名毛毯,其
余的一人一个暖瓶。”
董延平对石静说:“这要在过去,说老实话,就得把你奖给我。”
“奖你一大嘴巴。”石静笑着说,“没你那样的,骑着人开,按少数民族脾气早给你下
油锅了。”
“透着是一家子。”董延平笑着乜我一眼,又对石静,“我怎么就不如他了?人家皇上
的闺女还知道搞点选拔赛什么的,你也给我一次机会。”
“就是,”小齐插话说,“挺好一滩牛屎你插回试试。”
“抽你啦?”董延平恫吓小齐。
“你没戏。”我诚恳地对董延平说,“别没事就下蛆,哥哥这儿所有的缝儿都抹死了,
混凝土浇铸。用样板戏的话说就是:风吹雨打全不怕--是不是石静?”
“没错,”石静笑着说,“全都玩去。”
“真粗野。”董延平摇头叹道,“没劲,真让我伤心,看来这老百姓家的丫头是不
行。”
“对这种人咱们一般怎么处理来着?”我指着董延平问小齐。
“看瓜呀。”小齐一声喊,一帮人蜂拥而上,把董延平七手八脚按在地上。
“蹭上蹭上!”董延平躺在地上大叫,“我昨儿穿的裤子还没换呢。”
“左眼跳是财来着还是灾?”
“灾。”
“是财跑不了,是灾躲不过。”我开了自行车锁,推着往外走,外面雨下如注。
“等雨小点再走吧。”石静打着伞推着车望着我。
“你知道什么叫沐浴么?这就叫沐浴。”我片腿上车骑入雨中。
街下的树木在风雨中飘摇,两边的建着物窗户紧闭亮闪闪地反着光,楼房泄水管哗哗流
着水=*头绿地的草坪浸泡在白哗哗的水中,马路、车辆、路灯、楼厦都被雨水冲刷得十分
洁净。滔滔不绝的水从各个路口四面八方涌来,夹着树叶残花打着旋沿着拱行的马路向两边
分流泄淌。家家商店的屋檐下站满一排排躲雨的人和自行车,人们看着雨出神。
“多幸福的事,”我对赶上来与我并肩骑行的石静说,“大庭广众之下洗着鸳鸯澡,回
头再潮得乎地对上道梅花枪,抽根儿夺命烟,喝上二两追魂酒。”
“别不要脸。”石静话音未落,手里的花伞被风吹得“呼”地脚尖朝上,旋即脱手而
去,在风中飞飞停停,颠来倒去,顷刻间成为远处水中一盏飘飘荡荡的莲花灯。路边避雨的
人群中暴发出一阵狂热的掌声,人人喜笑颜开。我挥手向人群致意,顿成落汤鸡的石静一脸
哭相。
“让你欲盖弥彰。”我笑她。
“这人怎么都这么坏?”石静气咻咻地说,“看见谁倒楣就幸灾乐祸。”
我们拐入另一条街,只听路边闲人齐声欢呼,一股洪水席卷了路边的一个瓜摊,浩荡水
中飘游着一个个翠皮大西瓜,滚磕碰撞肥头大耳络绎而来。
“什么叫堤外损失堤内补?抱两个吧!”
“你这祸国殃民之心何时能死?”
石静咬牙切齿,在滔滔水中东倒西歪为西瓜簇拥。
“这叫欲进不能,欲退不得。”
我翻身下车,溯流而下,弯腰趁势抱起两个大西瓜,未及夸耀,早有一个赤膊短裤小子
趟水而来,接过西瓜,口称:谢谢。
“占什么便宜了?”石静下车立于水中笑我。
我们搬车到路边,站在树下看苦主儿奋勇扑捞瓜果,每捕住一个,便大拍巴掌叫好。
“你无聊不无聊?”石静看我兴高采烈喜不自禁的样儿嗔问。
“我操,兴奋一下多不容易。”
这时背后“光啷”一声,街边楼上的一扇窗户玻璃被打碎,落英缤纷,滚滚黑烟冒出,
一颗姑娘头探于窗外大声疾呼:“救命呵!着火啦!”随即消逝不见。
黑烟滚沸出户,风吹雨打立即稀薄澄澈,无影无踪。街上行人都仰头卖呆,迷惑不解,
面面相觑。
“不能吧,这也不是着火的天呵。”
“喀嚓!”又一扇窗户被打破,伸出一颗髦毛焦黄的爷们儿头,同样粗腔大嗓地吼了
声:“救命呵!
着火啦!”随之缩了回去。
又一扇窗户被打破,伸出一颗娘们儿头,同样声嘶力竭地喊救命,并不再缩回,伏于窗
上高一声低一声。黑烟不时将该头笼罩吞没,彼时便断了呐喊,咳嗽剧烈,俟黑烟散去,喊
声复起,其高亢嘹亮不减分毫。其情可哀,其状可悲。楼下闲人只得连连顿足,迭声呼叫:
“跳呵!跳呵!”
“恐怕也只有我挺身而出了。”
石静一把没拉着,我已弃车子弹般射入楼内。
一楼太平无事,职员官员们庸庸碌碌地在挂着牌子的各科室进进出出,抱着文件端着茶
杯。
一个一脸无知却带着副眼镜的看门老头儿,从门房冲出,横眉厉目拦住我:“楼内没厕
所。”
“二楼着火了。”我趁老头儿一愣,分开他窜上楼去。
一群知识分子沿走廊狼狈溃逃出来,其中之一抓住我,指着走廊顶头一间烟冒得最粗的
房间说
“那里有重要材料,快去抢救。”说完匆匆下楼而去。
走廊里不见火光,只见股股浓烟从对称的房间内接连涌出。我闯进第一个房间、抄起把
椅子,向那一扇扇宽大的窗户排头砸去,砸完第一间砸第二间。各间办公室既不见人影也不
见火光,只有浓烟透过似毫无缝隙的墙壁弥漫四散。窗户玻璃砸碎后,雨斜射进来,窗帘迎
风飞舞,烟便也散去。在最后一间办公室我才看到火光和昏在窗上的那个老娘们儿。
火舌沿着地板和墙上的油漆层飞快地窜行着,象水中涟漪一样疏散开来,几道火苗窜到
我脚下便带着烧糊塑料的臭味躲闪开向四处蔓延。我抄起办公桌上的茶杯用力摔在地板上,
迸碎时产生的冲击波和溅出的茶水使弹着处的火苗瞬间熄弱,随即又跳跃着越过水渍更欢快
地奔向它处。我兜着圈子舞蹈着走到窗前,试图扛起一滩泥似的老娘们儿,楼下看热闹的人
一片欢呼。
“扛不动。”我放下架在脖子上的老娘们儿胳膊,拍着老娘们儿肥厚的肩膀冲下说,
“二百多斤呐。”
“扔下来,扔下来!”
几个小伙子跑来,大张着胳膊做接面口袋状。
“别来这套。”我笑着对楼下的人说,“我扔下去你们就躲了,我还不知道这个。”
楼下的人笑:“保证不躲,你扔吧。”
我捧起老娘们儿耷拉着的头,狠狠弹了俩钵儿,又拧着脸迎着急速打来的雨水浇了一
通:“醒醒醒醒,这会儿先别睡。”
楼下的人笑着指着我骂:“孙子,你手轻点。”
老娘们儿一下惊醒,搂着我脖子就哭。
“别介呀,”我红着脸掰开她,“别瞎哭,睁眼瞧瞧是不是亲人。”
我可知道人抓兹命稻草是什么手劲儿了。
幸亏一股火苗蛇似的窜来,燎得我们踩电门似的忙不迭分开。
一点不瞎说,再瞪大眼儿找就找不着人了,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没影儿的。
这时屋里的几张写字台已经烧得非常好看了。火苗从所有抽屉往外冒,不时“乒”的一
声响从桌面四壁迸出。一会儿工夫便烧得透明了,若大写字台的框架门剔透鲜明,最后便
“哗”的一声塌下,火势减弱随之又高高窜起直逼屋顶。我出了房间,在走廊墙上摘了一架
泡沫灭火机,倒举着一路扫射冲出走廊,扔了灭火机下了楼。
一楼人都跑光了,扔了一地形形色色的鞋。我听到救火车自远而近呼啸而来,带头盔的
消防队员在门外晃动。我刚出楼门,被高压水枪射出一束水柱砸了个满脸花,脚下一滑便坐
地上了。
“过瘾了?”石静迎着,乜着眼抖着腿问。
“什么话!”我愤愤地说。“对英雄怎么这口气。我不说什么鲜花拥抱之类的吧,起码
也得敬佩地看上我两眼。”
石静看着我笑,“行啦,承认你是救火不是趁火打劫就够宽大的了。”
“你把我当什么人了?”我笑:“让人寒心呐。”
“你的胳膊怎么啦?”石静突然拉着我的右臂惊叫起来。
“嚷什么?”我甩开她的手,抬起右肘看了一眼,只见右肘外侧划了一道大口子,很长
但不算太深,因为渗流出的血已结痂。
“你得去医院上药。”
“别那么大惊小怪。”我说石静,“去什么医院,你没看血已经不流了?回头洗洗,自
己上点药就行了。”
我拉着石静走出人群,此时雨已经小多了,接近于淅淅沥沥的程度。我们扶起倒在路边
的自行车,骑上蹬走。一路上,石静总是忧心忡忡地瞅我的胳膊。
夜里,我们在空荡荡的新居内刷房子。说是新居,其实是人家住过的旧房子,墙壁斑驳
剥落污浊不堪。石静在用水泥抹墙壁上的洼点。我举着胳膊在给自己擦红药水。
“你擦什么药呢?”石静头也不回地边抹边说。“别乱上药。”
“怎么叫乱上药?正经的你减三十--二百二。”我扔掉棉签,上前接过石静的灰板和
瓦刀,搅着黏稠水泥一刀刀抹着玩,对石静说,“你去和大白吧。”
四面墙尽管颜色深浅不一,但已平平展展,放倒任何一面墙都可以打克郎棋了。
石静拎着和好的白灰桶放在我脚下,用自己的手绢四角扎结罩在我头上。我踩上一张板
凳,用排刷沾着灰水在墙上上下平刷。
灰水一道道笔直淌下去,长短不一,却毫无例外地在筋疲力尽时坠出一个沉甸甸的终
点。薄薄透明的灰水似遮掩不住墙壁的瑕疵,然而在乾涸凝结后就一片洁白耀眼了。
石静在墙的另一端刷着,她头带护士帽,衬衣束在腰里,一手叉腰,一手挥动排刷,动
作轻柔富于韵律,安祥耐心,并不抬头便知道我在看她:
“好好干活,别东张西望,这可是给自个干。”
“我发现你刷墙的姿式比较好看。”我索性停下来,笑嘻嘻地对她说。
她迅速地瞟我一眼,迷人一笑,又低头认真地刷墙低声说:“什么意思?”
“没什么,不过是比较一般的讨好。”
“不是想让我一人把墙全刷了吧?”
“你这人怎么那么没劲呵。”我笑着从板凳上溜下来,坐着、荡着腿,“你把我这一腔
柔情都给弄没了。”
“累了么?”她偏过头来看着我问。
“没累,这点活算什么?咱不是给自个干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