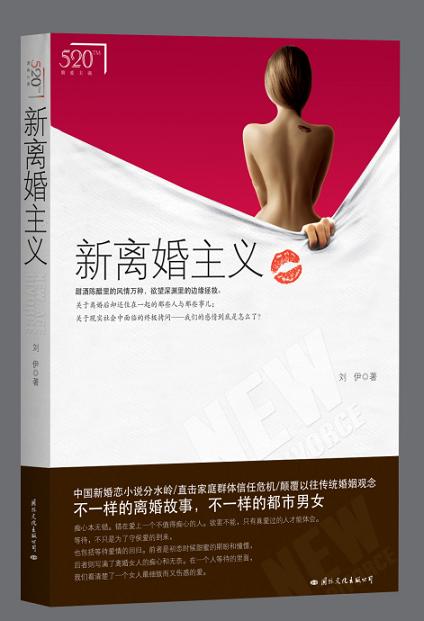����Ժ�-��11����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ȷ����ζ����
�������ó����ۣ�������ʵ������һ����ʵ��֪�ι�ȡ�����Լ�ԭ������ʵ�����۴�����Ǩ������ʵ��������˭���Լ���������ģ���֮�ұ�������������ڡ��������һ���¶����ڵĻҝ��������췿����ѵ��Լ����Դ��������⣿���±����ͽ�����ʲô������ʩһ���ĵط����������Dz����ܡ��ӳ�ʶ������������˭���Դ�����ס��ҽԺ���أ��ο��ⷿ�俴�����Dz�����Ҳ�����η���������ǵġ��������������ͨͨ�Ŀշ�����ѡ�
�����������ϴ������ָ����ޱ���������ͷ��������������Ȼ���ޱ���������Ȼ����ͷ���ȷ��������ַǹ����ʵ�ı������ʵ����ͷ�����Dz������κ�������������ָ���������Լ������ӣ�����˯�°�˫�ַ����Լ����鷿���棬ȷ������һ���������Լ������������ӣ���״�ÿ����鷿���ұ�������һ����飬һ���ʲ��������ޱʵ��������Ȼ�������á��Լ������Լ�����һ���ò�ȷ��������
������ѣ��ʧ����ҡ�����ڼ������о����ƺ�֧���Լ�����Ľ��ּ����ڱ�һһ�����������ڲ�ʧȥ��Ҫ����������ɳ��Ŀն�������Ϊֹʹ������Ϊ�������١��о���Ѫ��ͼ��䣬��ij��֮�������ذ���һ�ա�������Լ����ʲôҲ���ǣ�������Ϊ����Ϊ�ⲿ�����ͨ���ṩ����Ĵ��ڡ�һ����ȫ����Ƥ�������ӿ�Ĺ����г���Ϯ�������������С��Ҳ����������ӣ�Ȼ��������������������У��Ӻ����������ȴֻ��С�ü�����������������
���������������������˯�ߡ�����Ӻ�˯������ʱ�ܹ������Լ�ԭ�е���ʵ���Ǹ��ж�����������°��������뵽��Ωһ�����������İ취�����Եļ�ֵ�ܸ��еġ�������������˯��������������Ϊ���ոմ�˯��������������˯����ô�á���ô�������ð�ԭ������ʵ��������ʲô�ط���
��������ʰ�����ɫǦ��Ю��ָ���������ת��ģģ�������ڴ�������о��ܹ�������ij�ּ��䡣������ָ��о�����ֻ����ֹ���ݵ��ĵļ��ʡ������ɵý�Ǧ�ʶ������ϣ��ϴ�������ѣ������۾���
����˭Ҳ����������������롣����Һ������˭Ҳ�������������
��������֪���������������ʸ���롣
�������Ǵ��Ϸ����������ڴ��ϵ����ˡ��̶�����Ϊ�ӵ������������ȥ�������컨�壬���ٺ��ˣ�����ֹ�غ��ˡ�dz��������֮���α�С�����һ��С�㣬������ʧ�����Ǽӿ��ٶȣ��ʹ˺����Ŵ�Խͬ�²㡣�����С�������ʧ����������������У�����ʹ�ӵ�����ֹ�غ��ˣ����������ƺ��˵Ľ��̡�
������ʶ��ʱ�������ѷ���dz�������ķ��䡣���Ͽտ����ˡ����ӻ�������ˣ�������ӳ����ֻ��ɳ�����������������Ĵ̶������������������ĵؿ���һ���ɳ������
��������Խ��Խ��������Ѹ����ʧ��ɳ����Ҳ������Ӱ������ȫ�ĺڰ������ˡ�����Ժ�
11
3��42
�����������Ų����ڹ������ϡ�λ�ڶ������е������ε�С�����оɹ���סլ��һ����Ϊ��ͯ�������ֳ�������ǧ�������ΰ����ˮ̨��ˮ�������λε��������ܡ����q�q����ľ��ͷ��������չ������Ҳ�й�ľ�ԡ���Ҷ�����������棬����ȥ��������֨֨�������������졣�賿��ʱ�Ĺ����������������Ӱ������İ����������ĵ��߹��ڿ��С�������һֻС��è����ϥͷ����������ֽ�����Ŵ����������Ρ�Сè������ζ�س��š������ḧ��Сè�ı������⼸ֻè�����뿪Щ�ĵط�������һ���Ρ�
�������ڡ��������ǡ���ʱ����Ϣʱ�䳣��ʳ����������è��������˵��������һ����ס�ڹ�Ԣ�ﲻ����è���ܻ�����è���ָС���
�������ڼ�ʱ��è���������ʡ�
��������Ϊû���ֵܽ��ã�è��ȡ����֮�ˡ���
��������ϲ��������
��������Ҳϲ�������˼�������������è���ã���Ϊ������Ȥ��˵����
����������è�Ҷ�û������������˵�����ҽ��Զ����ë��������ס�ش����硣��
���������𡣡�
�����������˴�С�ͶԺö�öණ��������ɼ��������������ݢ��������Ϻ����Ϳ�����������ȵȵȵȡ���
��������Ϳ���������������üͷ������ô��������û��˵������
��������������������ʵ��Ҳ��֢״���֡���
������ʲô֢״����
��������ݡ����������ѣ�֧�����������������Ķ����������ȥҽԺ���ɡ���
������ÿ�δӸ�Ϳ������ǰ�߹�����������
������Ҳ����ÿ�Σ�ʱ��ʱ�ء���
������ʱ��ʱ��Ҳ���ܵģ���
��������ĬĬ����è��
��������ô���أ��������ʡ�
��������������
�������š���
����������������һ��û�С�������˵������û�ù����������ԣ��ڼ����������еİ�ѩ����������׳׳ʵʵ�ķ�ɽ��Ĺ����
��������ѩ����һ�Ҳ���Ҫ��������
����������ͷ��
��������˵����������������������ﲻ������ý���ʲô��Ϳ��Ϳ�����ᡣ��
��������Ŀ�Ӹ��ţ�������û��ô����
���������鵱Ȼû��ô��������˵������������������˵�����ﲻ�䣿��
���������䣬���¡���
���������־���һ���ǹ�������θ�Сè��Сè�����Ӷ����ˣ��Ե�����רע��
��������һʱ�ò��������Dz��Ǹ������Ǽ��£������վ���˵������˵ʵ������һ�Ρ�������һ�Ρ����Ҹ����㵥��̸�ú����롣��
��������������������ʲôʱ����£���
�������������¼�ɡ�������Ҫ�Ҷ�����·��Tower��Records�ڣ�����ǰ��ͻȻ����dz����������һ���ˣ���Ҳһ���ˡ�����ͨ��վ������һ�������Ҫ˵�Ļ�̫�࣬�ͽ��˸���һ�ҿ��ȹݡ�����ĵĶ��Dz��̲������ճ��л����Ǹ���ͬѧ����þ���·�������ĵ���Щ����˭˭��ô��ô���������Ϻ����������ȥ�ܺȾƵĵط���˵�����൱����ĸ��˻��⡣��ô˵�أ��������кܶ��˵����
����������ĸ��˻��⣿��
�������ǵġ���
���������Գ�ʮ�ַѽ����ɫ��������ô�����˵���ֻ��أ�ӡ������ͬ����������ô���ܡ�����
������������ҵ�Ȼ���ر����ܡ�����ǰ����һ��ȥ������Ӿ��ʱ�ŵ�һ�������ؽ�̸���������������Ƿ�֪���ҵ�ȫ������
��������Ĭ����������������ϥ�ϵ�è��
��������˵������������ʱ���϶����˭˵�����š��������ֻ����ö�Ҫ�õ�Ů��˵���ǣ����������û���ܹ������ø���Ů�ѣ����Բ�ѡ�����ң���š����ɰ��ˣ�˭������ν�ġ���
����������Ϊʲôѡ�����أ�������֪����Ӧ��һ��ȱ�����ѵġ���
�������϶���ȱ����
��������ƫƫ����·�ϲ��ڶ������㣬Ҳ����˵�Բ���ô���ܵ���˵�˸������ﻰ������Ϊʲô�أ���
�������ǰ����������žʹ��Լ�˼������������Ϊ�ҿ���ȥûʲô�����ɣ���
������û��������
����������˵��ʹһʱ����Ҳ��������в����
�������������װ�����
����������˵�����������������Ƶ��������£���˵����֣���ʱ��������Ϊ��ͬ�����ߣ���·��ʱ���в���ʶ���������Ҵ��к��������ҡ���
��������ʵ��Ȼ����
�����������Ҵ�Ų��ǡ�����������������ȥ����������˵���ﻰ��������Ů����ʹ����ôҪ�á������ز���ʶ���˶����ҹ��������ͬһ������ܡ���ô�����أ��ֲ�����������Щ�¡���
�����������Դ�������Ļ���Ȼ��˵��������֮����������˵�����ﻰ�ˣ���
�������š����ﻰ�����߲���˵�Ǹ��˻��⡣��
�������ȷ�ʲô���������ʡ�
�������ȷ��������ˣ�������˵��¡���
���������˵��£���
�������ȷ�˵��������˵��
�����������Ҳ������ඣ���
�������ǰ�����
����������˵������
��������Լ�Կ�����һ�¸���ô˵�������硭����������Ҫ��Щ����
����������Ҹ�Ҫ��Щ����
���������������������������־��룬�Դӹ���ij��������������
�������������������£Сè�������㴫�ݵ������ϡ�
���������ǣ���ʹ�����ʵ����룬�����˲�Ҳ����Ҫ�õ�ô��������˵��
��������Ȼ��������˵�����ǵ�Ȼ���������������Ƕ���ij������˵���ʵ��ľ��룬������һ������δ��������������������Ҳ���еġ���
����һֻ��ɫ�Ĵ�è��֪����������������Ž��ϲ��Դ�������������è�����´����ͳ�����ɽ�����˺�����ϰ�װ����һ�������è�����ζ�س���������
�������Ǿ��ǰ������еĸ������⣿�������ʣ�������˵��û�취�����ý�һ��Ҫ�ã���
�������������������������һ������ֹ�������
��������ĬȻ��
�������ż�������������˵����ʱ���dz�������������������ҩ���ִ���ȫ��ҩ��һ�ߺȷ���֭���ؼ�һ����Ի�����һ��һ��һ���س�ҩ���ҵ�Ȼ��Ϊ�ǺϷ�ҩƷ��������������������
��������������ҩ���ԣ���ȥ��������Խ��Խ���ء���
������Ӧ������Ȱ�衣��
��������ҡͷ����ҩ�����ԣ����ʡ���������˵��˭ҲȰ�費�ˡ���
��������ί���˵���Dz��������ר��ҽ�����������羫���Ʒ�ר�һ����ҽ���������ƺ���ȫû��ǰȥ��ҽ����ͷ�����߲���˵ѹ������û������Լ����Ϸ�����ʲô����ˣ���ô˵�أ���Ϊ��Ҳ�൱���IJ��¡���dz������������ô�����أ���
����������¶��ɫ���������£���绰ֱ���ʱ��˲��͵��ˣ�������������İ����Ļ�����
����������̾һ��������ͻص�����һ��ʼ��˵���ˡ��������ǼҴ�绰��dz�������������治֪��������ô˵��˵ʲô�á���
���������˵�ʱ���Ǻ��ž����ܵ�˵����ô��ʱ���𣿶���˵��������ĸ��˻��⣡��
�����������ǵ��������ġ���������˵��˵�ˣ���ʵ��������ʱ����û���ڣ�����������һ����˵����ֻ�Ǻߺ߹��������š����ң��Ҿ�����ʵ������Ϊ�����ģ������Ǻܶࡣ����˵�������ڸ��������и��˽���������
��������Ϊ���ֲ������뵽�Ǹ��ز�����
������Ī��˵�������������������ġ���˵�ţ���������ȥɦè�Ķ�������Ӧ��˵û�Ǹ��ʸ�
������ֱ���˵�˵�����������������Ǹ��̶ȵĹ��ģ���
�����������ô˵��dz����������Ҳ����˵������ȹ��ġ��ղ�Ҳ˵�ˣ���ֻ�����Ҹ���˵����������˵���Ҳ�����һ���ܹ��ʵ��߹�����ġ������е�����ζ����ǽ�ڰ��ˡ���
���������Ҳ�˵������ڰ����л���û����ȹ��ģ�Yes����No����
�������Ų�֪�����Ƶ����˫�֡�������⡣��λش�dz����ѡ�
������Yes�������Ҷ�dz���������й��ġ���Ľ��ӵ�м�����Ȼ��Ȼ������Ķ�������������Ķ��������������������ġ����磬�����������ž����н�̸��ʱ�����Ҷ��۶����ؿ��ţ�����������룬�ǰ���ò��Ů��Ϊʲô����������ò�����������һ���أ���
���������ǡ�����
���������ǣ���
�������ú����뿴��������˵���������㡮���ڰ����л���û����ȹ��ġ�����ش𡮻��й��ġ�������©���ˡ���ȡ�һ�ʣ����˾�����ʲô����֮�߸�
�����������óϷ��������湻ϸ�ĵİ�����
��������ĬȻ�ȴ��Է����ġ�
���������е������֪��λش𡣡������������ˣ�����������泤ʱ��ؽ�̸�ţ�����������һ�ֲ���˼������顣���û��ʶ����ô����˼�飬������ʱ������ƣ����ָо���ʼ����ײ���ؿڡ���ô˵�أ����ƺ����Լ���������������ĸо���������������ǰ��ȴ�����ü������
����������Ȼһ�Բ�������ҧ�촽�ȴ�������˵��ȥ�����Ż�ʱ��Ѱ�Һ��ʴʾ䡣
������һ�仰��������˵ʲô�����ִ�������ʶ���Һ�dz������֮�����һ���������ĺ���ز�Ķ������ҳ��ڵĻ�����ͨ�������ʱ������������������֡������������ϣ���û������˵ʲô��˵��֮�䣬�ҿ�������㡣��һ���������ڵĻ���Ҳ������Եִ�������ˡ����Ƿdz�����ĸо�����
��������ǹ�������β�������֮��СèһŤ���Ӵ�����ϥͷ�������棬��Ҳ�Ƶ��ܵ���ֲ������ȥ�ˡ���������������ε�ֽ�������������ȥ����մ�����м��
��������ע����������������˵�ģ�������ף���
������˵����Ҳ�á�����������һͣ�٣����ղ�����˵�ģ�˵�����ܽӽ���һֱ�������еĸо����������⼸��ĸо�����
���������ﲻ���ִ���������ӵģ���
�������ǵġ���
�������Ű�ʣ�µ�����ɽ����Ը�����ǰ������һֻè��è�������������ζ������ϲ����ʤ�ش�ڴ�ڳ���������
�������ȣ���������⣬����ʵ�ش𣿡�
�������ܡ���
����������һ��ȥ���������ǡ����Ǹ�Ů����Ī�����ҽ�㣿��
�������ž��ȵ���������������������ע��С����ˮ���ϵ����IJ��ơ�
������Ϊʲô��ô�룿�������ʡ�
���������ɵá���Ϊֱ�������ԣ���
���������ԣ�����dz���������DZ��Ů������
��������ģ���
��������ġ���
��������˼��Ƭ�̡�
����������һ���ɺã���
��������Ȼ����
�������ٶ�����ҽ��һ����Ǽ��ù���������Ϊһ���ٶ�����
��������Ϊһ���ٶ�����
��������Ϊһ���ٶ�����һ���ٶ����ʡ�����ҽ��һ����Ǽ��ù�������ô������Ϊ�ٶ�����
��������Ϊ�ٶ�����
��������ô��������ʵ�ش�Yesô����
�������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