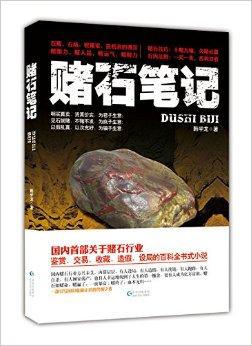狱中笔记-第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故人昨是今非。
“从你的自陈来看,情势不容乐观。”我的朋友比大学时更能克制情绪,只有前倾的上身透露出他的关注。在这个故事里,我没有在本科毕业后参军,而是读完博士,以我的进度应该是在1939年。当时很多一流的工程师因为血统或政见而离开德国,我在法本研发高分子新材料,因为前述原因而平步青云。次年,法兰西战役打响,能源紧缺使合成燃料成为科研的重点,老一辈很难改变研究领域,开发新热点就落在我这一辈人的肩上。战争时期,德军几乎所有的润滑油和炸药都来自法本,如果不是合成燃料的成功投产,二战在1944年就结束了。
“法本和帝国化工协会都被认为是纳粹化的组织,它们直接支持了德国的侵略,身为其中一员你难辞其咎。”我的朋友把自白书在手里收拢,陷入椅子的后部。我因为纳粹党员的身份而失去工作,又因为曾是法本能源部的高级工程师而身负战争罪责,“但也有另一条路,美国希望引渡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在那里你将获得自由、从事科研的机会以及相应待遇。”
“我拒绝。”我看着他,我说这句话的眼神一定是太硬了,乃至他笑了起来,“这真像你的做法,但我是在猜到你会这样说的前提下,决定来见你的——我在当时就应该劝动你出国。”
当时是1934年,纳粹上台后开始清算犹太人、共产主义者和魏玛分子,即使在舆论宽松的海德堡也有一些教授被迫离职,因为发现阴极射线而获得诺贝尔奖的勒纳德教授操纵了这里,把校园舆论导向种族主义,很多城市爆发焚烧非日耳曼书籍的运动,在学校,犹太学生遭受排挤乃至殴打。“这个国家已经疯了,”那时他念大二,大学生活刚刚走上正轨,“来论证一下,于公于私我们都不该留在这里。”
那时开始,德国走向极权的深渊,军国路线和克虏伯的军工业,妖魔化的犹太形象,作为少数族裔的犹太人执掌德国金融界的事实,沉重的经济危机和失业的狂热分子,大量涌入的东欧群氓,孤悬国外的东普鲁士,纳粹以疯狂的方式让几个势力咬合在一起形成了第三帝国,先天的罪恶变成累累罪行。
我们都是一流大学的佼佼者,理当在学术上有所追求。但那时学者离散四方或臣服于政党,战争造成的紧迫局面也必然限制科研的方向,学术根底因之溃烂。“我们留在这里,就是背叛良知、理想,和真正的祖国。”我的朋友敲着桌子大声说道。
“但是,我们应该去哪,”我看向他焦灼的眼睛,“总得选择一个国籍,你在法国或英国也能找到卓越的人文学者,但是最顶尖的化学系、半数以上的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在德国,我正在接受的是世界一流的化学教育。”
在这个故事里,我们不像真实经历里那样争执得面红耳赤。后来我的朋友凭借斯特拉斯堡的交换机会踏上德法交界的土地,由此前往巴黎,而我留在德国,按部就班成为博士,然后进入法本的科研所。每个科研所都有纳粹分子,但德国毕竟收复了莱茵河西岸和萨尔,进入但泽,将东普鲁士的飞地连成一片。
我该去哪里,几年后轰炸不停的黑夜里,这个问题又摆在我面前。我生在德意志,无论第二帝国、魏玛共和国还是第三帝国,乃至更早的德意志邦联,西边的国家都觊觎这片土地的衰亡。我研发的是合成燃料,当盟军的高爆弹把威斯特法伦或萨克森连片的城市化为灰烬,怎能不希望德国的飞机能有足够的燃油起飞。
于是到了战争末期,故事回到路德维希港。这里是供给燃油的重镇,法本的一家大厂日夜吞云吐雾,合成汽油是钢铁机械的化学食粮。作为工程师而不是帝国的反谍人员,我在这里逡巡。两年以来,路德维希港遭受的空袭不下六百次,工厂使用集中营的关押者作为劳工,当泛着火光的蒸馏塔倾倒时,工厂里血肉横飞。我该选择哪一方,在前线过早死去的日耳曼少年,还是集中营的囚徒?前者也是无罪的,而设计更高效的人造汽油生产流程是我的职守。
于是,那位化学工程师因为支持战争,现在被软禁在这栋小楼里。无论我选择哪条路,结果都无不同。我的朋友前往法国的不久后德军也开到那里,他的学业同样无法维继,直到战争结束,他以抵抗者的身份重归大学。
我们该去哪呢,五年以来,最好的年华消耗在战火里。
于是那位化学家扬起脸:“我遗漏了一段:德军所有的甲醇和润滑油、大部分炸药和合成燃油都来自法本,在纳粹上台前,它就为希特勒提供了十分之一的竞选经费。这是我后来知道的,但看在德意志支离破碎的土地的份上,时间先后并不影响我的选择。”我对他说了最后的话,我的挚友的身影变得模糊,我所设想的对话方开始缄默。
故事讲完了。在真实的世界里,我在1936年取得本科文凭,放弃深造而成为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的一员。操纵海德堡的那位勒纳德教授引荐了我,他是希特勒的物理学顾问。那时,我对扩军的真实目的或旧普鲁士贵族的虚荣一无所知,自认能以优秀学生毕业,就能成为优秀的军人。
我在二十出头的年纪度过一段充实的大学时光,海德堡的开明氛围允许我崇慕各种主义,我选择了唯一的意志。当我离开实验室,把结项报告交到导师手里时,他惋惜的话语没有说完,我的挚友摆出一副要对我大动手术的外科医师的架势。人生有多种可能,现在三十岁的我身披死囚的红马甲,在战犯监狱里想象另一番故事,仍然殊途同归。
“我是在猜到你会这样说的前提下,决定来见你的。”故事里我的挚友如是说,故事以外,他成为党卫队的御用学者,但德国没有别的历史学,某天我惊悉他的犹太血统,而他在布痕瓦尔德死里求生。
现在我想知道,如果他仍然能够坐在我面前,会摆出怎样的道理,来训斥我这个囚牢中人。
1946年7月23—25日
【编者注】
加兰先生早年学习化学,其后在军队或情报机构工作。三十岁后他第一次用文字写下内心所想,比较于他的知识背景,这篇文章显现出罕见的流畅。或许这故事已在他脑际盘亘多时,只当契机到来落笔成篇。
“如果按照优秀学生的人生套路,在学术领域走到尽头。”他以全知视角回顾人生,重新选择,但是1945年坐在施潘道小屋里的化学家仍然逃不脱被审讯的命运。直到篇末,作者仍在设想那位故友会拿出怎样的理由,说服他本该走上另一条无罪的道路,但人生和历史一样不容假设。
值得补充的是,战后盟军起初想把法本化工彻底解散,不久后美苏对峙却让德国成为双方的砝码。五十年代,法本化工在拆分成几个子厂之后重新融合,战争中被炸毁的厂房掩盖了其下珍贵的机器,德国化工迅速崛起。在真实的世界里,那位虚构的化学工程师不久后就会回归本职,在战后重建中度过余生吧。
、鲜花战争
【编者注】
本篇和紧随其后的《帝国安全》是1938年3月德奥合并时作者的经历。当时加兰先生是警卫旗侦察部队的排长,他参加了这场不懂一刀一枪的“战争”的全过程。在他笔下,德奥合并在军队进驻中顺利完成,人们走上街头,欢迎这些讲着同一种语言的外国军人。
质疑者声称这是纳粹的谰言,鲜花战争只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政治阴谋。很奇怪,这些人却无偿相信着美利坚东部十三州西进运动的合理性,罔顾西部一度是印第安语和西班牙语的世界。
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流逝,会有真正的思考者来洞悉这段历史,从而发现德意志兰的真正边界。但是对于这篇文章,仍要指出作者是和一切身在历史当中的人一样,并未写下全部的事实。
片面的真相都不足以成为后人的导引,但人们已经一再触犯这种无心的错误,远至对《日耳曼尼亚志》的理解,近至两次世界大战前后盛极一时的君王们所造的历史。鲜花战争是真正的民心所向,还是彻底的政治宣传?这些两极分化的问题并无助于确立公正的立场,无非能揭发双方各自规避的真相。
那么以下是一位跟随军队进入奥地利的纳粹党人所见的事实。跟随美军到来的人看到了另一些事实,但然而成王和败寇,不过是两位最引人注目的说唱家。奥地利人拥有另外的事实。为了不使编者高于作者,我将在《帝国安全》(它与本篇在时间和逻辑上都衔系紧密)的末尾对这些林林总总的事实进行综述。愿人们在获得尽量多的真相之前,不要自行陷入“我还能相信谁”一类的虚无论中。
【原文】
1938年3月10日深夜,一声紧急集合号响彻利希特菲尔德军营。我从床上爬起来,扯出早已放在枕边的背包,汇入冲往阅兵广场的大军。这是我进入警卫旗后的第一次大型军事行动,也是德军自挺进莱茵、萨尔回归之后,第一次在境外活动。不过那里很快也是帝国的领土了。德国与奥地利在一次世界大战中并肩前进,战后分隔两方,现在德国要用军事占领的方式,与奥地利合并。
我把瓦尔特P38式手枪在腰间别好,站在排前清点人数。二十出头的列兵身型挺拔,飘着冰沫的夜里,原野灰制服的银帽徽闪闪发光。担任仪仗和警备工作的旗队如今身负国家扩张之责,成为帝国的尖兵。
“我们将告别施普雷河,在一天内穿过萨克森的密林,越过巴伐利亚的群山,在马达声中飞速前进,在第二天清晨就来到奥地利——我们自己的领土上。”迪特里希进行了简短的训话,旋即宣誓声响起,“我的荣誉是忠诚”。没有哪种语言比德语更适合发布军令,更适合军人的誓言。
这次的主力是国防军第二装甲师,从维尔茨堡出发。警卫旗以摩托化步兵团的配置紧随其后,从柏林长驱420英里,与之会师于德奥边境的帕绍。轻型卡车从利希特菲尔德开出,车的两面装饰着旗帜,铮亮的武器在士兵们手中握紧,让这场出征更像是凯旋。残冬的雪水把军用卡车的篷布濡湿,车声震撼了勃兰登堡的荒地,两旁是不见五指的漆黑。车灯犹如火炬般照亮前路,人们的眼睛也被车灯照亮,个个睁得铜铃般大。
我领着侦察排开动了摩托车,施令时声音有点抖,嵌着三颗星钮的领章勒着脖子,仿佛在发烫。
由于统帅部确定这次军事行动不会开枪,因此侦察连只需要夹在队伍当中前进。我坐在三轮摩托的斗车里,不时摸摸手里的望远镜、新发的地图、仅仅在射击场上用过的枪,激动的心情和其他的新兵蛋无异。
从柏林到帕绍一直是急行军,二十多小时不间歇地行进,在第一个晨曦初露进入莱比锡,第一个落日越过雷根斯堡。3月12日凌晨,我们来到边境。步兵团的很多人由于兴奋而整整一天没合眼,而全部配备摩托车的侦察连,根本没有合眼的机会。到帕绍时,整个排的人艰难地翻下车,恨不得给自己的关节上机油。
帕绍是一座安宁的小城,多瑙河在这里最后一次眷顾德意志兰,奔向奥地利。天色很黑,景色无缘得见。睡意潦草地安抚了我们,风尘仆仆的军容和疲惫的黑眼圈未及休整,我们在清晨又跨上摩托车,冒着飞雪和横风继续向前。
一进入奥地利,市民马上包围了我们。参加过一战的男人向我们敬礼,女人则拿出食物,我的斗车立刻装满了各种面包。本来是不允许收受市民的东西的,但是拒绝这样热忱的馈赠就太矫情了,我们只好拖着面包向前开去。
在维也纳,照样受到了盛大的礼遇。人们在欢庆中涌向军队,撕扯他们的扣子。我不得不让士兵们把子弹卸下来以防走火或丢失。两挺冲锋枪的保险栓不太严实,干脆就把枪托拆了。余下的几天里,高级军官与奥地利上层互相访问,普通士兵徜徉于维也纳的名胜。3月15日,警卫旗作为帝国最优秀的仪仗部队参加了大阅兵,希特勒在阅兵台上演讲,“同一种语言,同一个帝国”。这的确是一句政治口号,但谁能造出另一句口号,来驱散这油然而生的心愿?
几天欢庆下来,我几乎忘记了这本该是一次军事行动。合并过程十分顺利,警卫旗抵达维也纳后一直待命,除了阅兵就没有什么任务了。那天我们列队走过多瑙城的笔直道路,欢呼声缭绕耳边。我在柏林的外交场合或纽伦堡的党代会上已参加过几次阅兵,仪仗靴又紧又硬,但只要拔高腰杆就能让动作流畅,这个诀窍是仪仗连教给我的。
不过由于奥地利警署正在交接,侦察连收到了旨在防止潜在的破坏活动的巡察令。我所在的排被分配到利奥波德城。
这是犹太区,在多瑙河的另一面。大量的流动人口和非德意志裔使之历来是犯罪多发地,为跨国的间谍活动提供了掩体。在德奥合并的时局下,肯定有大量的反对派和境外势力蠢蠢欲动。但这时奥地利已经是德国的一部分,国内安保工作本不该由军方出面,连长再三交代不要贸然行动,开枪更是严令禁止的。
利奥波德城拥挤的街道两边黑压压地林立着各色商铺。东欧式的混乱当中,连空气都弥漫着犹太小食店特有的味道,清戒派犹太男信徒穿着黑色长袍穿街过巷,蔚为奇观。我们分成三队逡巡在杂乱狭窄的街道上。人们对一支德国军队的到来感到好奇,满面髭须的东欧人干脆停在路上,用油腻的眼睛打量我们。
“避开他们的目光,这样他们也不会老是盯着你看。”我示意部下只去注意街头巷尾可能存在的可疑人物。
过了一会儿,“排长……他们还在看。”
“别管他们,我们的主要是来排查潜在的敌对活动的。”
士兵们没有多说,低着头走过一道道街巷。
这简直像中世纪的罪犯游街。我们的一举一动都被犹太人看在眼里,他们在我们身后交头接耳,快步跑开或奇怪地停下。我的故乡法兰克福也有犹太人,多半从事金融或教育行业,从口音和举止很难将之与德意志人区分开。但是利奥波德城的这些人顶着黑黢黢的毡帽,留着络腮胡子,油污满脸,讲一种听不懂的语言。
我们行经城区中心的一座犹太教堂。明显的土耳其风格将它与其他房屋区分开(该教堂实为摩尔复兴式建筑,是维也纳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