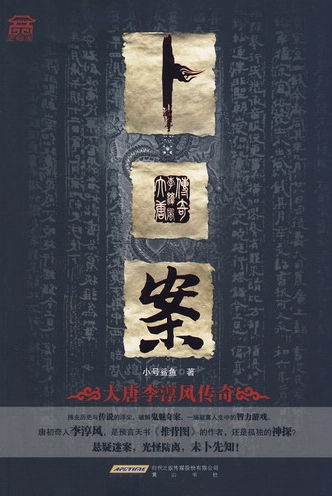大唐后妃传之珍珠传奇-第3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安庆绪内力浑厚,两人一时相持不下,默延啜弃鞭拨刀,如鹰隼凌空展翅,直扑安庆绪。安庆绪来不及拨剑,携沈珍珠连连后退,两侧骑士此际方反应过来,顿时弓弩朝天齐放,默延啜半空中挥刀砍箭,应接不睱,断箭之声“扑扑”不绝,却听“哧”的两下,肩臂、背心剧痛无比,已知中箭。
沈珍珠大惊失色,喝道:“还不快走,要死在此处,让我绝了被救之望吗?”
默延啜面色铁灰,已知事不可为,负痛跃身回马,喝道:“珍珠,我定会回来救你!”说话间,又斩断几枚来箭,那马臀部已中数箭,裂叫一声,驮着默延啜狂奔而去,一路听见他嗥叫悲凉,宛若荒野中的孤狼。
“晋王,可要追击?”一名领头骑士问道。
安庆绪摇头。掉头看身后的沈珍珠,道:“这样你可满意?”
沈珍珠强力支撑到现在,抬头,眸中静寂如水,问道:“为何要这样?”胸中的疼痛,脑中的昏眩漫天席地卷来,她不愿晕倒,她要清楚明白即将发生的,然而她还是幽幽的陷入下去……
念此翻覆复何道
瑟瑟寒风拍打窗棂;隔窗望去,几处破损房宇,枯草萋萋,有一缕风由窗隙挤压入室,一片雪花飘落在窗棂外,如琉璃般晶莹剔透。沈珍珠看着微微一笑,伸手去顾那片雪花,然窗棂的格子是由外朝内钉死的,她黯然的收回手。
“只要你愿意,不止可以走出这间房屋,这大好河山,万千黎民,都是你的。”安庆绪不知何时已走进来,在她身后说道。
沈珍珠不理他,走过几步,坐到几案旁,抬头问道:“这到底是什么地方,你到底想怎样?”
“你还不死心?”安庆绪在她对面坐下,道:“这世上除了我,再也无人知道你在这里。就算让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也毫无用处。”沈珍珠心中微凉,那日她自苏醒便已身在此房中,也不知究竟昏迷多久,此是何处。两名侍婢垂手侍立在门前,连眼角也不往安庆绪和沈珍珠身上扫略,宛若两个无声无息的死人——只当是死人罢,她们早被安庆绪毒哑,每日除了例行逼她喝药吃饭,侍奉穿衣洗浴,连眼神都是直的,木的,没有生机的。
房间特别暖和,地上铺的毡罽似乎都是热的,一应起居设备都是极好极全的,然沈珍珠只觉窒息无法透气,身体虽是渐渐康复,那心上的压迫之感却愈来愈沉。
“世上多是大好女子,我早已结缡他人,我不明白你何以依然如此偏执。”沈珍珠望向窗外那慢慢纷扬洒下的雪花,说道。
“可惜这天下之大,沈珍珠却只有一个。”安庆绪顺手拿起桌上酒盅,自酌自饮。他每日必至此房中,不管沈珍珠劝说喝骂,自饮自乐自醉。
“你真以为能关我锁住一生一世?”今日沈珍珠一改常态,竟夺过安庆绪手中酒盅,满斟一杯,说话间送至自己唇边。
安庆绪神色稍变,迅捷出手扼住她手腕:“你伤病未愈,不可喝酒!”
沈珍珠执拗的将手一送,启唇将酒全咽入口中,喝得太急呛住,连连咳嗽,牵住胸部伤痛,面上自现痛楚之色。
安庆绪冷冷看着她,启口说道:“你何苦跟自己身体过不去。我就如此不堪,昔日你宁死于我剑下,今天你视我如无物?”
沈珍珠咳嗽两声,道:“你既已知道,我心匪席;不可卷也。你若不肯放我,不如给我个干净痛快。这般的折腾我,又有何益!”
安庆绪面色乍变,扬首将杯中酒一饮而尽,手掌微微一捏,听到“哧”的脆响,酒杯粉碎,安庆绪扬手随意往后一掷,正正击中身后一名侍婢的面部,碎片划过处,那侍婢鲜血流淌,却不敢去拭,跪地“呀呀”的叫唤着,不住的磕头。
安庆绪只作无事发生,抚案而起,对沈珍珠道:“你休想再逃离我的掌控。我的忍耐有限,就算要不了你的心,也要定了你的人!你莫要逼我用强,莫要逼我毁了你!”说话中,似是无意朝那侍婢望一眼,拂袖而去。
沈珍珠呆立当场,半晌无法动弹。
他是安庆绪,再不是当年的安二哥。早在归还那枚珍珠当日,他心中仅存的那抹暖色已全部褪去。是她逼他的,为着自己的名节清白,逼着他一剑斩下,从此心如钢铁,视万物为草芥,摒弃所有情义。
她无法预料他还会做出什么事来。
他虽摒弃所有情义,惟有对她,因着亲下杀手,因着乍然失去,方知决不可舍,竟立意不惜一切夺回。大婚那日,他与她近在咫尺,终失之交臂,却更激起他之欲望。婚礼未成,或者在他心中,却早已将她当作天定的妻子。
他一步步退让,甚至顺着她的心意,有意放走默延啜等人,竟是下定决心要留住她的心。
他日日来视,当她卧床不起时,甚至亲侍汤药,让她身体日渐起色。
或许,他一直是在等,等她回心转意,等她重识眼前之人,是否方是可托终生之人?
若有一日,当他发觉,无论如何,她已不能将心留在他之身畔,他会怎样?
他如今对她,到底是爱,还是不甘?是想挽住在这世上唯一深心眷恋,还是想挽住过往年少的美好年华。是对她如眷如恋,难分难舍,还是不甘她情着别处,一心逆转?
她现今已经求死不成,他还会怎样?
“就算要不了你的心,也要定了你的人!”
脚底阵阵寒意泛起,她一个踉跄,早有一名侍婢抢上前冷冷的扶住她。她定住身形,对她们狂呼道:“滚!你们滚出去!”
那两名侍婢只若无闻,只谨慎又谨慎,防备又防备的盯住她,防她有任何异常动作。
沈珍珠颓然坐到床塌上。
安庆绪一连数日未来。
这日天色已晚,沈珍珠正欲歇息,安庆绪推门而入,她勃然变色,正欲逐客。却见安庆绪从怀中掏出一物,放于桌上道:“今日是你生辰,总算找到此物,也算是贺礼罢。”
沈珍珠呆了呆,问道:“已是十二月十九?”
安庆绪一改往日清冷孤寂表情,居然笑着点头,展开那卷物什,阵阵馥香扑鼻而来。沈珍珠缓步上前一看,原来竟是一包罗汉豆,应是辅以茴香、桂皮、食盐煮成,那香味确是诱人之至。
安庆绪说道:“我总记得你当初最爱这东西,那年你过八岁生日,宴席上满桌的鱼肉不过稍动筷子做个样,一退席,便缠着我偷偷出府买罗汉豆吃。”
“可惜时间太晚,你赶到店铺时,早已关门打烊。最后还是空手而归……”沈珍珠随手拈起一块,放入口中咀嚼。
少年时喜爱的,往往是这般简单直捷的吃食,及至嫁与李俶,吃不完的山珍海味,还会常常忆及那一小撮罗汉豆,香味萦绕梦境,绵绵不断的少年回忆,青涩甜美的憧憬。就连那时的愁,那时的忧,真真是无事上层楼,满目河山强说愁,哪似年长之后,每每欲说还休。然而,今日真的尝到这思慕已久的东西,却发觉物是人非,香与脆,总与记忆中相差一截,原以为入口绵连,难舍难弃,却不过如此。原来一路成长而来,口味混杂,恋恋不舍的只是那朦胧如诗的美好感觉。最美好的只该留在记忆深入,不被打破,永葆缄默。
安庆绪显然心情甚好,还在兴致勃勃的述说如何凑巧得到这一包罗汉豆。
沈珍珠唤了一声:“安庆绪,……”
安庆绪停下话语,警觉起来,“你不喜欢么?”
沈珍珠开口欲言,却听房门轻扣,安庆绪不耐的说道:“能有什么事?”说话间,走了出去。
这一去,安庆绪又是十来日再未来此。
此时已近年节,沈珍珠细听四周,竟毫无喜庆之乐,无人员喧杂之闹,左思右想,总猜不透现在何处。惟从天气温湿判断,此处似乎并不是长安,长安地势南高北低,故才有水自南而来,注为曲江池,冬日雨雪多,十分寒冷。而此地较之长安显然气候暖和许多,自入冬以来,不过在十余日前下了一场中雪。
门“呯”的被推开,抢步走进一名侍卫装扮的。两名哑婢见他,唯唯恭身后退,显是安庆绪身旁亲信侍从,哑婢对之敬畏交加。沈珍珠和衣未睡,立即翻身而起,那侍卫上前两步,沉声道:“奉晋王之命,请小姐去一个地方。”
沈珍珠疑惑的望着他,凝然不动,道:“已是深夜,恕我不能成行。”
那侍卫一把拿住她手腕,道:“晋王之令,小姐非去不可。”说着,已强拖着沈珍珠往外走,两名哑婢连连后退,不作丝毫阻拦。
乍出房门,一阵寒风扑面而来,沈珍珠不由打个哆嗦,那侍卫回首对哑婢微皱眉头,一名哑婢忙取了件铁红大裘披至沈珍珠身上。
沈珍珠只觉今日景况大为不妙,又说不出不妙在何处。若安庆绪真意图对自己有非份之想,何必多此一举,带自己离开此房间;若无非份之想,此时已是深夜,为何着人带走自己?
却总算多日以来,头一回能踏出这牢笼之门。沈珍珠张口欲呼,喉间一凝,已被那侍卫点了哑穴。沈珍珠怒视面前之人,那人却毫不理睬,只狠狠拖住她往前走。
跌撞着随他走去,廖阔天空半点星月也无,四周黑漆漆,模糊可望近处、远处稀稀落落几处房屋,衰微破败,无灯无烛,分外孤清,脚下不时有杂石碎草绊住,隐有哭咽之声幽幽传来,似是鬼魅人间,沈珍珠遍体生寒。
兜兜转转,极长极长的一段路,眼前豁然开朗。
沈珍珠不由自主止住脚步,双眸漾动点点光灿,简直不信眼前所见。
飞檐斗拱的殿宇,一眼看不到尽头,在华灯照耀下如玉宇仙宫,巨大的红色宫灯,排列齐整的路灯,内侍宫女手持的彩灯,映照出五彩的天地。
沈珍珠已然大悟,调头回望刚刚走出的拱门,昏昏暗暗,上书两个篆体大字——“掖庭”。
若没料错,此处竟是东都洛阳皇宫大内!
王公贵胄常往来于长安与洛阳之间,唯沈珍珠婚后多发事端,兼李俶事务繁忙,无睱□,从未陪她来过洛阳。虽然如此,洛阳皇宫殿宇与长安炯然不同,沈珍珠稍一对照,便知此处应是洛阳。心中惊异,没想到安庆绪竟将自己拘于宫城掖庭之内,度一路行来所见,拘禁之所,或者是掖庭内最偏僻罕有人至处,难怪他这般胸有成竹,谁会注意小小掖庭中的一座破旧屋宇?更何况,他也会加派人手,暗中守护不让人靠近。
只是,今日他之所为,究竟是何用意?
来不及多作思索,那侍卫已拖着她朝最近的一所殿宇走去。
殿宇外、宫阙口,数名带刀侍卫把守肃立,内侍宫娥各守其所,见了那侍卫和沈珍珠两人,只若未见,直直的放二人进入殿内。
沈珍珠骇异莫名,这座殿宇规模宏大,绝非仅为晋王的安庆绪份所当居,多半是帝后寝殿。数月以来,她只忖度安庆绪已逐渐全盘掌控叛军兵权,但未料已嚣张到这般地步,目之所及的所有侍卫宫人,俨然全听命于他。此时此际,只怕连其父安禄山——“大燕”的皇帝,怕也不被他放在眼中。
踏入殿宇,刺耳的鼾声由内殿传来,零星侧立的内侍宫女面无表情。那侍卫一挥手,殿内所有内侍宫女均退出殿宇。
沈珍珠方望一眼那侍卫,却觉全身一麻,已被点中穴道,动弹不得。那侍卫一把将她横抱起,朝内殿走去。
沈珍珠心中的害怕已到极处,实不知这侍卫要拿自己怎样,这内殿中之人到底是谁。
那侍卫蹑足轻声走入内殿,沈珍珠双眼平视而去,见殿中巨大透明薄纱帷帐居中,以明黄流苏为幔,巨烛高照,状如白昼。帐中一人壮硕肚子高高挺立,遮住面庞,鼾声扑天盖地,有一种怪臭熏人而来。
听到极轻的开柜之声,身子一松,被那侍卫送入一衣橱之中,这衣橱高过一人,内中容量甚大,那侍卫扶正她的身子,正可靠壁端坐其中。接着眼前又是一黑,那侍卫已将衣橱之门关闭。
虽然关闭,但那衣橱之门制作时并非用木材整块密闭,而是稀稀疏疏的有一条条横断缝隙,沈珍珠这般坐立,正可由缝隙中看到外间,虽不能一窥全豹,大致亦能瞧得清楚。她心中微有所动,安庆绪刻意要她在此,究竟是要她看什么?
她朝外看去,这衣橱正对那大床而立,床上之人,兀自酣睡未醒。
等了半晌,听见似有脚步声入内,隐约看见一身着青色锦袍,脚踏皮靴之人走近床帷,只是她坐势较低,只可见其颈部以下,无法看见此人面貌,却可确定并非方才侍卫。
那人站于床旁伫立良久,也不说话。
过了许久,那人终于开口沉声唤道:“父皇。”
正是安庆绪的声音。
他既称床上之人为“父皇”。那床上之人,定是安禄山无疑。
明月初沉勘契时
安庆绪连唤数声,安禄山似乎才醒转过来,开口道:“你来了?这么晚,还有什么事!”话中殊无欢喜慈爱之情,显得十分不耐和粗暴。
“孩儿想问父皇一事。”安庆绪的声音也无半分恭敬,话气生冷冰硬。
听到被盖悉萃之音,安禄山由床上坐起,堪堪让沈珍珠直面将他相貌看个清楚明白。安禄山以往虽常来长安拜谒玄宗贵妃,但自从天宝十三载杨国忠向玄宗进言安禄山必定会谋反,让玄宗多次试探后,再也不敢入长安。故沈珍珠从未见过安禄山。
此时隔着薄薄纱帐,见安禄山面庞青黑,长相甚为粗鄙凶狠,身量粗短,最为惊人的还是那硕大的肚子,圆如转盘,拖沓至床。
他半覤着眼,冲安庆绪道:“什么事,快说!”安禄山入秋以来,视力陡然下降,看甚么东西都渐渐模糊不清,本就性情狂燥,愈发无法自控,动辄鞭打、处死亲近侍奉之人和臣下,众人人人自危,日益离心。
安庆绪道:“听说父皇已拟诏册立庆恩为太子?”
安禄山毫不迟疑,粗声答道:“是又怎样!”
安庆绪朝床塌逼近一步,腰间长剑咄咄作响:“母亲因你而死,庆宗为你而死,你竟要将这大好江山,拱手送与那贱人之子?”沈珍珠听着心惊不已,安庆绪对安禄山已不再称为“父皇”,僭越之心昭然。安禄山共有子十一人,唯长子庆宗与庆绪系原配卢氏所生,安庆绪口中的“庆恩”乃是第三子,乃安禄山现今所立“皇后”段氏所出,封为平王,年纪尚幼,颇受安禄山宠爱。
安禄山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