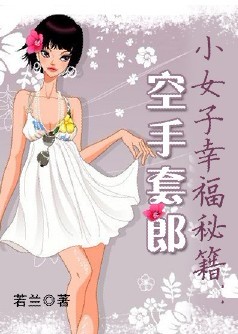女子无殇1,2完结,番外晋江新完结高分文[1].绝对好看-第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雍和四年,宠妃瑭姻以叛国之名获罪,累及满门。
(空,待补。)
雍和十八年,正式册封皇长子浞飏为太子,赐太子府。封皇四子浞陉为朔王,皇六子浞炯为单王,皇七子浞荇为佑王,膝下两女浞萧然、浞徽然分别为凝因、凝思公主。
雍和十八年,北方外族犯境,十八岁的少将修涯随父出征,战功卓越。
雍和十九年,册封修殄之孙女修溦为太子妃。同年纳太子太傅之女凤连城之女凤婞红为凤妃。
雍和二十年六月,大旱,西北蛮夷入侵,一时间竟然所向披靡。不足两月吞并西北近六座重镇,八月,传奇少年昊殇一战成名,全歼敌方先锋骑兵。十月,率一千精兵深入西北,痛击蛮夷。
雍和二十一年三月,偏安南方的晋安、叶同等小国因不满每年缴纳的岁贡,频频越境滋事,更有海盗袭击商船杀人夺货。三月末,太子浞飏率亲兵玄士军十万南下迎击诸国号称三十万的联兵。双方于榆城相遇,交战两天两夜,玄士军铁骑铠甲重创敌军,敌军主将阵亡损失过半退缩榆城,等待援军,不敢贸然出战。浞飏并不急于强攻,围困榆城近半月。与此同时,判官昊殇率两千水师顺恒河水路而下,快袭海盗船队,全歼贼寇。四月,昊殇带领水师频袭诸国海域。如此一来,各国皆腹背受敌,顾此失彼。于是求和。岁贡增至黄金两千,白银三千,丝绸布帛千匹……五月,太子回朝,娶大学士宁运兮之女宁清为妃。
雍和二十二年,即北方外族新君赫赤朗登基第二年,复又来犯,将军修涯带军出征,双方大小战役无数,却依然呈僵持之势。直至今日。
雍和二十三年,太子浞飏二十二岁手持玄铁,成为监国。
放下书简,仰面合目,头微微有些阵痛,尚不及理清这些支离的片断,便听见卿书慌忙跑来的脚步声。
人未到声已至:“姑娘,不好了,不好了,太子……”
我惊起,险些跌下椅来,忙问:“你说,太子怎么了?”
见我如此,卿书反倒扑嗤一声笑了出来:“先前还以为姑娘真是神仙般的人物没有喜怒的呢,这会才明白什么叫情深方许,关心则乱。”
我正色道:“太子到底怎么了?”
“哎呀,奴婢该死,忘了正事。上面传下话来,说是王上震怒太子私下凡间,还,还……”
“该死的丫头,你快说呀。”
“还因色误事,带回一凡间女子,败坏朝纲。”
“那如何处置太子?”
“圣旨还没下,具体的情况还不知道。这不,太子妃请您到前厅去,大概就是为了此事。”
太子府正堂前厅。
我迈过朱漆的门槛,膝下一软跪倒在地。
周围有低低的抽气声。修溦大声道:“你这是做什么,有什么事起来好好说。”
大理石的地面微微冰冷,坚硬的硌得膝盖发疼。我面含委屈之色,眼眶带泪,满眼凄切:
“泫汶万死,累及太子。”
一双暖暖的手带着不容置疑的力气把我扶起。我缓缓抬头,对上修溦清宁的眸子,她笑:
“准是卿书这丫头胡乱生事了。放心,别看王上王后刚正无私的,其实都是很疼爱太子的,说是惩处,不过是罚罚闭门思过之类的,没有大碍的。”
“真的吗?”我握着她的手,泪眼婆娑地问道。一幅柔弱小女子的无助模样。后来,修溦同样眼泪凄凄无助而迷茫的问过我同样的话,我告诉她,是真的,只是是我故意安排的。
她拉着我的手一同坐下,“真的。方才太子差人传话来了,让我们不必担心,过会便能回府。我叫你来原是想我们一起在此等候,却害妹妹忧心了。”
尚不及回话,凤婞红便风风火火的跑了进来,依旧是一身红衣,颜色偏于娇嫩,容颜也是粉嫩嫩的红。
她说,声音有些激动,内里是掩不住的兴奋:“爷回来了吗?”
修溦责备道:“怎么这么没有分寸。爷这不还没回来嘛。”语气却是宠溺的味道。
清妃一袭水蓝色的长衣窄裙缓缓而来,青丝未束,素面朝天,面目清冷,不见半分欣喜。与
众人寒暄几句后便是长久的沉默。一双原应钟灵清秀的美目了无生气。
浞飏怎会娶她,她对他应是无爱,那他对她呢?
时至正午,阳光明亮得炫目。浞飏就在这样丝绸般流淌泻地的金色光亮中出现。身着淡紫色的朝服,胸前金龙腾云盘旋,金冠束发,剑眉斜飞,嘴角凌厉微抿,面上没有一丝情绪,却依然英气摄人,王者睥睨天下的霸气与高贵已似天成。
一屋子人霎时仆仆跪倒行跪拜之礼。
“都起来。”
浞飏目光淡淡的扫过众人,道:“修溦随我来,其他人退了吧。”
凤婞红似乎在抱怨。
我只是低头作揖,转身离去。安静的姿态似乎我从未出场。
十多日离别之后的再见,我与浞飏没有说过一句话,甚至没有眼神上的交流。一切仿佛透着陌生疏离。
别来几向梦中看,梦醒尚心寒(
别来几向梦中看,梦醒尚心寒(一)
夜色已深,不见星月,唯窗前一弯碧水清澈,粼粼波光映在窗棱之上。
长夜深寒,对于女子来说永远是寂寞的等待。遥望漆黑穹庐,似在广寒宫中也有一位孤独的女子,百年寂寞的等待,我想那或许是中救赎,为她曾经抛弃的爱人。
点了一支熏香,淡淡的青草味道。再抬头就见未阖的门外倚着一黑衣男子,玉立长身,嘴角含着一抹漫不经心的浅笑。
我便也笑了。
二人相对一时无言,只是清然浅笑。一个风骨傲然,一个绝色清丽,都不是善于言语表达情感的人,于是似乎谁也不愿意打破此刻情意绵绵的纠缠,甜言蜜语在这样的气氛中黯然失色。
许久,许是累了,二人缓缓收回目光。
“伤好了吗?”却是一同问出的。于是又笑了。
浞飏笑着走进屋内,站在我面前,挺拔的身姿遮了我所有的视线。那绝美的俊脸上挂着一丝浅笑,似乎透着牵挂的气息。
他的手抬起我的下巴,那双黑漆漆的眼睛里映着略显娇羞的我自己,他说:“看来你是知道我会来,小妖精。”
“嗯。”
他恨恨的道:“你是不是在我身上下什么蛊了?”
我一脸无辜,愤愤道:“你还敢说,我才怀疑你给我下蛊了呢,害我白白忧心。”
“我,我白天那样……”浞飏说的很艰难,解释对他来说是件分外生疏的事。
我掩上他的嘴,轻轻说:“我都知道,我知道你是为了保护我。”疏离有时候也是源于爱护,现在只怕全国都得知太子浞飏带回了一位凡间女子,这种时候,浞飏对我的爱只会平添他人妒忌,使我成为众矢之的,所以白天时他才会有意的冷落我。
他把我抱进怀里,下巴抵着我的头。
我伸手反抱住他,我们的胸膛紧紧相依,静谧的夜里彼此的心跳清晰可见。
浞飏的头低下来,坚毅而桀傲的唇吻上我的,我愣愣的直视他深亮的黑眸,浞飏责备的瞪我,手掌轻轻合上我的眼睛。一时情动,我闭上眼睛回吻他。唇齿绞缠便有了情欲的味道。他忽的把我拦腰抱起向床边走去。一只手解我的裙带。
我惊惶的挣扎,浞飏死死箍着我,动弹不得。
我惊叫:“我们还没成亲,这……这样不行。”
说话间他已经把我放到床上,反手一挥,衣衫尽解。古铜色的肌肤上偶有伤痕,却掩不住精壮健硕,那双一贯清明的眼睛渐渐迷离,有激情燃烧的火焰。
锦帐雪帛,织锦缎被。青丝散落如瀑摊开,我手足无措的反抗,眼泪盈了满眼,顷然流落,无声的滴在枕边。
浞飏突然停止,茫然的神情一闪而逝,眼中燃烧的红热略有止歇,手怜惜的拭去我的泪。
“别哭,我还没与你说,父王虽是恼怒,但已经默许了你我,等过几日母后见过你,我们便可成亲。”浞飏温柔的说,拉过锦被盖在身上没,转身欲走:“你别哭了,是我急躁了。”
母后要见我!这几个字在我脑中炸开,顷刻之间决定。
我拉住浞飏的手,羞涩的看着他:“不是我不信你,只是吓到了,对不起。”
浞飏定睛凝视我片刻,俯身压了下来,吻上我的锁骨。反手挥落帘帐,织锦红帐轻纱烟罗流泻而下,掩住了一室桃色旖旎风情。
成了浞飏的女人,无疑为我与王后的见面多了一份筹码。二十年前心思缜密,地位显赫的善妒女子,二十年后重遇故敌,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的妖媚女子,该是怎样一番情景。
我没有必然存活的把握,而手中紧攥的只有浞飏,却也是她心底的爱,她最疼爱的儿子。
是的,害我至此的仇人便是今日母仪天下的王后修莛。那高高在上,妖艳狠毒的女子。
别来几向梦中看,梦醒尚心寒(
别来几向梦中看,梦醒尚心寒(二)
一夜迷情方转醒,万缕情丝心间荡。
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醒的,又或者是未曾睡着。夜色渐渐淡去,于是天边泛白,清清明明的映亮了屋子。
清晨沾染露水的空气总是清新好闻的,偶有鸟儿轻啼,唱得也是婉转清脆的歌儿,晨光怡人而美好,让人舍不得发出声来破坏这样和谐的大自然的声音。
身旁的男子睡得沉稳,嘴角似乎挂着浅笑。我狠狠地闭了下眼睛,复又睁开,可浞飏绝世的俊脸上依然微微荡着笑容,虽然浅浅的,却眩目的刺得眼睛生疼。自我认识他以来,这冷峻狠戾的男子不是没有展露过笑颜,只是那种微笑毫无意义,漫不经心地只是公式化的表情而已。然而,眼下呼吸均匀睡相酣然的浞飏,却在睡梦之中笑得这样真诚满足。
情不自禁的手就拂上了浞飏的脸,他长长的睫毛动了动,一双漆黑如暮的眼睛缓缓睁开。对我一笑,那是极其温情的笑容,暖暖的融进我的心里,却跌在狰狞屹立的冰川寒气之间,没了踪影。
我不由叹气,我这幽暗冰冷的心,谁人也无法救赎的了。
浞飏转身面向我,长臂一伸把我揽进怀里,赤膊相对彼此温热的体温在身体间流淌。“大清早的你叹什么气,怪我昨夜没有满足你?”
我怒目瞪他,这说得可就不真了,昨夜欲求不满的人似乎不是我吧。这话我自然是说不出口的,只能把一腔愤恨化作眼中两把利刃,生生的向他飞射。
浞飏嘿嘿的笑,搂紧我,把我的头埋进他的胸膛:“算我错了,你这模样怕是要把我生吃了,美人在怀我还舍不得呢。”说着手又不安分起来。
我身上痒痒的,赶忙按住他的手:“不要闹了,都什么时辰了,被人撞见多不好。”用力把他往外推,“快去穿衣服。”
浞飏在我的额头上印上一吻,起身下床,利落的穿好衣服。
门吱嘎一声从外面推开,卿书端着脸盆愣在门边,一脸惊恐,忽的一声盆摔在地上,人也踉跄的跪下,颤颤巍巍地说:“奴婢该死,奴婢该死。”
澄净的阳光穿过门窗照进室内,浞飏一身黑色长袍英挺的立在床边,神情一如继往的冷然,迫人的气势丝毫不减。我衣衫凌乱,蓬头素面,斜倚在床上,半边锦被遮身。这番场景怎么看都像是我色诱浞飏,手段魅惑,几尽风骚。
浞飏说:“你是哪屋的奴才,如此不懂规矩,门也不知道敲吗?”
卿书整个人簌簌的发抖,不停的磕头,“奴婢该死,奴婢原是太子妃房里的,奴婢该死,求太子饶命。”
浞飏皱了皱眉,负手而立。
脑中忽的闪过些东西,我不禁莞尔,这女人间的战争明里暗里的真是机关算尽呀。
拉了下浞飏的手,柔声道:“这不怪她,是我不懂规矩,与她随意惯了。再说也是太子妃一片好心照顾我,她也没什么大错,就饶了她吧,不然我怎么和太子妃交待。”
浞飏冷声道:“记住,今天的事要是走漏半点,便是死罪。”
方才浞飏眼中分明是凛然的杀机。他生性桀骜,不会在意别人的看法,我知道他是怕别人背后的风言风语伤到我,毕竟我们还没有成亲,现下关于我的流言已经够多了。
浞飏深深的看着我,“晚些时候再过来。”转身从卿书身旁出门。
待脚步声渐行渐远,卿书瘫倒在地,呼呼的喘着粗气,眼泪鼻涕的糊了一脸。
卿书说感觉就像是在死亡边上走了一趟,浞飏那看似淡如清风的眼神其实凌厉锐利,如冷刀割过皮肤,是死都不能如愿的折磨。
我递了杯水给她,她冲我重重的磕头:“谢姑娘救命。”
掏出手绢擦去她脸上的污渍,柔声道:“以后咱们都要注意点了,这规矩始终大于人命啊。”
卿书动容的看着我,热泪盈眶,说些感激的话。
可我的心依然在冷笑。女人总是自以为很聪明,以为假手于人便能安然躲在幕后脱去干系,却不曾想着世上本就没有可以完全信任的人。有些时候,我们连自己走未必尽信,又如何说服自己去相信他人。
晚饭的时候修溦遣人来叫,说一家人总算齐了,吃个团圆饭。
我略微思索了下对着镜子坐下,把头发松松的挽了个髻,单带一支紫玉簪。浅浅的上了个淡妆,穿一身淡紫色的家常套裙。
一张桤木圆桌。浞飏黑衣束发坐在正席,面无表情。修溦身着水青色的宫装,头戴凤凰八宝攒珠,安静地微笑坐在浞飏右手边。
行毕礼,我落座于在稍偏的位置。凤婞红依然是风风火火的闯进来,坐在浞飏左手边。
修溦笑道:“咱们开席吧,宁清身体不爽,便不来了。”
除去杯箸交错的响动,一室安静。
一黑衣侍卫匆匆进厅,屈膝跪地:“禀太子,王后凤驾已到街口。”
众人皆是一愣。浞飏起身道:“这会应该进府了,先去接驾。”
巍峨的石牌坊屹立街边,街口处十二个壮汉抬着一金色荷花宝座銮驾缓缓而来。隔着薄纱幕帐依稀可见,正中端坐的女子仪态之雍容。那身形即便是隔着百年的时空,依然是午夜萦绕的梦魇。
我在一干女眷中缓缓垂